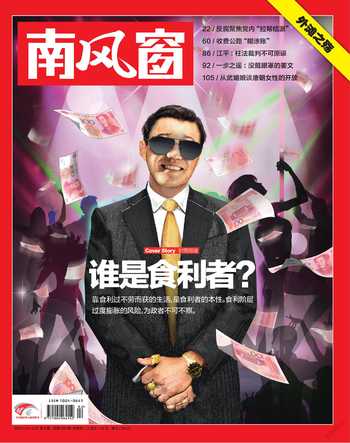評刊
楊軼清 浙商研究會執(zhí)行會長
創(chuàng)業(yè)者與草根從來都走得很近,如果特指第一代的創(chuàng)業(yè)者,那更加是形影相隨。歷數(shù)晉商徽商浙商第一代的大佬們,無論是已經(jīng)歸于塵土的歷史人物,還是風(fēng)頭正勁的當(dāng)紅明星,都有著草根的“影子”。他們的區(qū)別在于,“草根”是大多數(shù)第一代早期創(chuàng)業(yè)者的“身份”—他們多數(shù)出身寒微白手起家;而現(xiàn)在新時(shí)代新經(jīng)濟(jì)的創(chuàng)業(yè)者,“草根”主要的不是出身或身份,更多代表一種精神。這二者的共同點(diǎn)是:有夢想,相信市場,不迷信特權(quán),而且相信小草和大樹只是身材的區(qū)別,并非品種和基因的差異。
我在十余年前曾經(jīng)寫過一本書《浙商制造—草根版MBA》:如果要給浙商群體設(shè)計(jì)一個(gè)LOGO,基本元素就是“草根”。中國迄今唯一一位三度登頂中國大陸富豪榜榜首的企業(yè)家宗慶后,43歲那年蹬著一輛人力三輪車給小學(xué)生送貨開始創(chuàng)業(yè)。在成為校辦企業(yè)經(jīng)銷部“經(jīng)理”之前,宗慶后已經(jīng)在街道小廠蹉跎了七八年,干過多種雜活。再往前,初中畢業(yè)即下鄉(xiāng)的宗慶后,在紹興種過茶在舟山曬過鹽,在農(nóng)村苦行整整15年。直到他的母親提前退休,他才有機(jī)會“頂職回城”,回到杭州。
無獨(dú)有偶,與宗慶后一樣踩過三輪車送貨的,還有今年的新科首富馬云。1964年出生的馬云比宗慶后年輕將近20歲,應(yīng)屆高考落榜后,馬云替出版社踩著三輪車將成捆的雜志從印刷廠送到火車站托運(yùn),這樣的活兒干過一年多。
我們翻開風(fēng)云浙商的履歷,不難發(fā)現(xiàn),新老首富宗慶后和馬云的草根經(jīng)歷完全不屬于另類:
萬向集團(tuán)創(chuàng)始人魯冠球,初中畢業(yè)打過鐵修過自行車;吉利汽車創(chuàng)始人李書福,做過野照相(背著相機(jī)走街串巷給人拍照片);萬豐奧特董事長陳愛蓮,當(dāng)過農(nóng)村拖拉機(jī)手;美特斯邦威董事長周成建,做裁縫出身擺過服裝攤;奧康集團(tuán)董事長王振滔,做過木匠;唯一全品種民營車企青年汽車董事長龐青年,年少時(shí)以養(yǎng)牛販牛為業(yè)。
如果不厭其煩,這份名單可以開列得很長。但隨著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換代和創(chuàng)業(yè)者的年輕化,新時(shí)期創(chuàng)業(yè)者來自于社會底層的比例逐漸減少。但草根色彩,或者說草根內(nèi)涵依然濃郁。
馬云打造了全球最大的電子商務(wù)網(wǎng)站集群,但在同樣全球最大的實(shí)體商品交易市場義烏,近些年悄悄崛起了一批“電商村”。其中的青巖劉村因?yàn)椴痪们袄羁藦?qiáng)總理的到訪而聲名鵲起。阿里巴巴和義烏,或者說青巖劉村和一路之隔的義烏商貿(mào)城,從內(nèi)涵上說,二者并沒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以耕地種田的吃苦精神做生意,造就了傳統(tǒng)義烏奇跡;同樣,以擺攤做生意的務(wù)實(shí)精神做電商,造就了青巖劉村神話。按照馬云自己的解釋,阿里巴巴成功,就是草根力量匯聚的結(jié)果。
宗慶后人到中年蹬著三輪車白手起家,現(xiàn)在的年輕人懷揣夢想從零開始,只是行業(yè)和時(shí)代背景的不同。不變的依然是:平等的機(jī)會、進(jìn)入門檻不高、不依賴特定資源、不相信特權(quán)和壟斷、都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需要夢想、敏銳的眼光和一定的冒險(xiǎn)的魄力。“草根”什么時(shí)候都不會凋零,因?yàn)樗坝懈薄?/p>
我是一名“80后”的女大學(xué)生,畢業(yè)后在一家公司呆了6年,覺得該出來了,就自己出來創(chuàng)業(yè)了。我沒有得到資本和政府的什么幫助;跟大企業(yè)競爭,有時(shí)可能連敲門的機(jī)會也沒有,但我對自己不定大目標(biāo),就是很隨性地在做,所以既不悲壯,也不辛酸艱苦,基本要求就是一年一年往上走。我既不是創(chuàng)業(yè)家,也不是事業(yè)家,就是個(gè)小女人,做著一份小而美的事業(yè),兼顧家庭。我覺得草根創(chuàng)業(yè),拼的就是心態(tài),是對自己的定位,是堅(jiān)持走下去的心理素質(zhì)。
—杜勵(lì)(讀第1期《回歸常識:新一代創(chuàng)業(yè)者的價(jià)值觀》)
筆者身邊也有放棄穩(wěn)定工作加入電商大軍的年輕人,基本還在獲取收益與降低成本的博弈斗爭中掙扎。隨著人工、物流、房租成本的日益提高,期待再從這個(gè)行業(yè)中分一杯羹的后來者將面臨比前輩們更嚴(yán)峻的形勢。日益壯大的電商大軍,不僅需要國家層面的重視、關(guān)注,也需要能從制度、稅收、貸款、補(bǔ)貼等方面給予更多照顧,讓更多懷有創(chuàng)業(yè)夢想的年輕人能更輕松、更專注地發(fā)展。
—天天天藍(lán)(讀第1期《義烏“淘寶第一村”調(diào)查》)
縱觀歷史,我們的文明是不斷發(fā)展的。文明發(fā)展有賴于人與人的接觸。而事實(shí)就是,接觸總會產(chǎn)生沖突,只不過人群密集度加大,接觸更頻繁,沖突的概率更大而已。所以生存空間的缺乏會導(dǎo)致沖突事件相對更多。暴力事件的增多是副作用,如果就因?yàn)檫@樣便畏縮不前,不去正面看待生存空間問題,那就太悲哀了。
—?jiǎng)㈨y韜(讀第1期《公共空間的暴力沖突》)
文章中的看法只是眾多人視野變化的一個(gè)縮影而已,這些年,內(nèi)地在改革開放中發(fā)展了起來,同時(shí)也深刻影響了一代人的價(jià)值觀。當(dāng)然,有主流的,也有令人失望的。比如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浪潮激發(fā)出了唯利是圖的價(jià)值觀,金錢就是一切。現(xiàn)實(shí)證明,類似金錢就是一切的思維仍大行其道。當(dāng)我們談得越多,它就越盛行,現(xiàn)在很少有人再談了。當(dāng)這種社會意識不再有人談起的時(shí)候,或許說明,其已被我們無意識地接受了。這是我們被經(jīng)濟(jì)浪潮沖擊后妥協(xié)的結(jié)果。
—馬舉廣(讀第1期《金錢不是價(jià)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