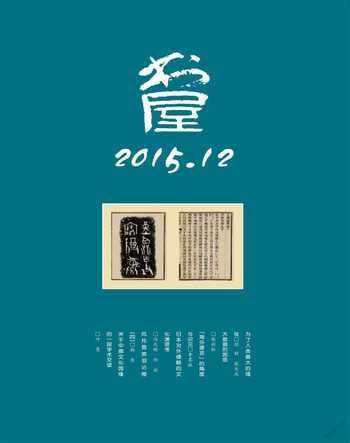道苦真無極
古遠清
研究世界華文文學,最迫切需要的是入門書,入門書又莫過于工具書,而工具書中的“年鑒”,大陸沒有,臺、港、澳沒有,在海外同樣打著燈籠也找不到。
關于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年鑒的編撰,我在多次會議上呼吁過,可一直杳如黃鶴。汕頭大學華文文學研究中心委托我編撰《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年鑒》,這是一個創舉,是一項攸關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建設的大事,在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史上也算得上是空谷足音。
作為一門學科,理應愈來愈重視史料和文獻的整理。編輯和出版了《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年鑒·2013》,就是希望能為“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建設盡一份力量。這本書通過“綜述”、“刊物”、“目錄”、“爭鳴”、“訪談”、“悼念”、“書評”、“資料”、“機構”、“會議”等欄目,反映“世界華文文學”這門學科2013年的基本狀況和重要成果,并匯集有關重要信息,以讓廣大讀者了解這門學科的最新動向,為世界各地學者研究時參考和使用。
在編撰工作開始之后,本書便發生如何界定“世界華文文學”問題。這里按約定俗成的辦法:除中國大陸地區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華文文學,都是本書收集和研究的范圍。但這兩者有時很難截然分割,故在“刊物”和“機構”等項仍保留有中國大陸的內容。關于這本“年鑒”的資料選擇,本人力求客觀持平,使讀者讀了這本書后能回到2013年華文文學批評現場,但不等于說是有聞必錄。由于世界華文文學年鑒的編撰尚屬首次,故本書在以2013年為主軸的同時,適當地將時間往前伸,如《華文文學刊物簡史》和《華文文學工具書一瞥》等項,就是這樣做的。把范圍擴大,可使此書既有年鑒的功能,又有辭典的作用。
《2013年中國大陸高校開設華文文學課程概況》一文是莊園女士給我布置的“作業”,應視為本書的重點文章。為寫此文,在春節期間本人多次打電話或發電郵給近六十所的高校老師,所得極有限。畢竟是人微言輕,手中既沒有掌握學術大權又缺乏行政資源,故個別人對我的資料征集不屑一顧,催了多次均不回復,也就只好作罷。但就從這些掛一漏萬的開課統計中,可看到“世界華文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建設還有遙遠的距離,且不說全國每所有中文系的文科大學都沒有像開“中國現當代文學”課那樣普遍講授“世界華文文學”,就是許多重點高校對這門課也是相當陌生,即使集中開課的南方高校,其課程名稱也是五花八門,用“世界華文文學”作課名的寥寥無幾。更使人不解的是,還有人死抱住“一流的搞古典,二流的搞現代,三流的搞當代,四流的搞臺港”的偏見,視華文文學研究者為“弱智”的一群,對空間無限遼闊且名稱繁多的“世界華文文學”的學科始終保持警惕。
但必須鄭重說明的是,汕頭大學委托我編此書,我不敢怠慢,力圖將它編成既符合年鑒體例同時又有個人風格的工具書。所謂個人風格,是指不僅把年鑒看成是年度資料匯編,同時也把它視為研究者心靈史的記錄。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包括“年鑒”的編撰,長期以來研究者的個性被遮蔽、被扭曲、被壓抑、被埋沒,這是不正常的。本書特設的“備忘”欄目,不僅是為兩岸文學交流的艱難以及研究者勇闖禁區的精神作見證,為百年來的華文文學研究留下雪泥鴻爪,也是為了建構一個更加豐富多彩的個性化文學年鑒形態,推進有個人鋒芒和學術風格的研究做出貢獻。也許有人不贊成我的觀點和立場,但這些都無關緊要,因為“年鑒”的編撰本身是一種理性的冒險,同時也是審美乃至靈魂的冒險。
這是一個躲避崇高、失卻信仰的時代。在拜金主義影響下,傳統信仰被解構,造成學術界一些人不堅守學術信仰而參與制造“學術泡沫”行列。對以學術為業的我來說,始終堅持學術進步的信仰,追求學術的創新,但“年鑒”畢竟有約定俗成的體例,很難出新。如果說2014年年鑒和2013年的有什么不同的話,除增加了論文摘編外,就是這本“年鑒”把“爭鳴”放在首位。這是有鑒于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爭鳴空氣不濃,可探討的理論空間很有限,這類文章也較難找,因而選用了少量并非當年發表,但系當年出版的論文集中的文章。所選者皆依原文排印,但頭篇王鼎鈞的文章在《羊城晚報》發表時,所用的題目是《起來,不愿被包圍的作家!》,后來鼎公來信說:“‘起來’作題目,易生歧義,用于年鑒,也稍欠莊重。仍用原來的題目吧。”這原來的題目即《海外華文文學的突圍》。
這位大名鼎鼎的王鼎鈞,曾在臺灣出版過《文學江湖》。借用他的話來說,世界華文文學文壇已成一座深不可測的江湖。是華文文學的創作與研究,構成了這個江湖的存在。比起中國大陸文學、臺灣文學及港澳文學,還有東南亞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這個江湖之大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的。這個“江湖”的發展趨勢和作家的走向如何,他們的作品如何經典化?本書收入的有關文章,初步回答了這個問題。
“百年身世千秋業,莫負相逢人海間”(葉嘉瑩語)。年復一年,季復一季,每本“年鑒”均是我徜徉在世界華文文學“人海間”理性冒險的履印與靈魂冒險的足音。我在密密的書林中享受著生命的安靜,在一本又一本的“年鑒”中尋回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