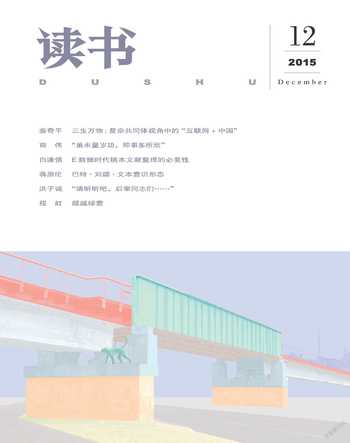“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
商偉
袁行霈教授是我的碩士導師,我是袁先生的第一位碩士研究生。
那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初期。當時攻讀碩士學位需要三年時間,但我們那一屆特殊:由于一系列陰差陽錯,我們一九八二年九月入學,一九八四年底論文答辯,兩年半就畢業了。應該說,我從那時開始,才真正接觸到學術,而袁先生正是我的引路人。
早在中學時代,我就知道袁先生的名字。在家里的書架上,擺著《閱讀與欣賞》和《中華活頁文選》等讀物,其中《閱讀與欣賞》收錄的是“文革”前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同名節目中播出的文章。袁先生寫的是曹操《觀滄海》。他在文章中寫道:古人寫大海的詩篇不多,曹操的《觀滄海》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像“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這樣囊括宇宙、吞吐日月的境界,更是難得一見。袁先生從這個層次上來分析這首詩,讓我感受到魏晉詩歌從平凡世界中升華起來的力量。這也是我第一次在詩歌中認識了大海,為“文革”期間像我這樣渴望讀書但又前途渺茫的少年,打開了通往想象世界的一扇天窗。我做夢也想不到,七八年后,我竟然會成為袁先生的研究生,并且在跟隨袁先生研讀魏晉南北朝隋唐詩歌時,正是從曹操的作品開始讀起。
我記得同一冊《閱讀與欣賞》中還收了吳小如先生的一篇鑒賞文章。而那時,我剛讀過王瑤先生寫的《李白》,對唐詩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尤其是書中寫到李白青年時代在峨眉山隱居讀書,“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猜忌”(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又描述李白如何在二十五歲,只身出蜀,順長江而下,“仗劍去國,辭親遠游。南窮蒼梧,東涉溟海”(同上),都令我不勝神往。等到我一九七八年十月進入北京大學,才知道自己有多幸運—原來這三位先生當時都在中文系任教。
中文系七七、七八兩級的學生,都不會忘記袁先生教過的課。他關于中國古代詩歌藝術的選修課,得到了學生的普遍好評。32樓前的中文系黑板報上,曾經公布過學生的問卷結果:在中文系那一年的授課老師中,袁先生名列榜首。由于選課的人數太多,袁先生第一次講授這門課時,系里決定只對七七級開放。第二年袁先生重開此課時,我很早就報了名。等到本科畢業前夕,我已經拿定主意,要報考袁先生的碩士研究生,主攻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
一九八二年秋季,我進入了碩士班。等到袁先生從日本回來,我正好讀到了南北朝時期的詩文集。我交給袁先生的頭一篇讀書報告就是關于梁朝的“宮體詩”。兩周以后,又交了第二篇。關于這個題目,“文革”前只有可數的一兩篇論文,其他的論著和論文又都無從查找,所以只能從原始材料入手。袁先生讀過之后,約我到家中見面—當時的系辦公室在五院,但古典文學教研室只有一間辦公室,所以,平常與袁先生約見,都是去先生在蔚秀園的公寓。因為是第一次聽袁先生評論自己的讀書報告,心里不免有些緊張。但一見面,先生就告訴我報告寫得不錯,讓我松了一口氣。他接著建議我把兩篇報告合成一篇,從結構上做一些調整,然后話頭一轉,說別處也有待改進。他指著我引用《梁書·徐摛傳》的一段文字“摛之文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問我說:“這里的‘春坊’,你查過了沒有?”所謂“春坊”,即梁簡文帝太子當時所在的春宮,也是將宮體詩與簡文帝太子和徐摛之子徐陵編撰的《玉臺新詠》聯結起來的一個重要的中介環節。可是,我年少心粗,竟未留意,事后想來,簡直難以原諒。但先生并沒有批評我,而是要我回去查書,下次見面再談。這次經歷,讓我了解了先生指導學生的特點,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他“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長者風度和接人待物的方式。
三十多年之后,回想當年的研究生生活,不免會生出許多感慨。那個時候,碩士生很少。一九八二年入學的那一級,全中文系加在一起,不過十一位。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得到了導師分外的關照。八十年代的師生關系,的確有些不同尋常。一方面,自一九五七年到“文革”以來的整人時代已經結束,這是師生關系最好相處的時期:從老師的角度來說,不再有政治上的顧忌,用不著擔心學生告發批斗,也沒有同輩之間的某些歷史包袱,可以跟學生在很多問題上坦誠交流,因此也正是在空前寬松的歷史環境中,建立了一種新型的師生關系。另一方面,體制化、職業化和商品化的大潮尚未到來,師生關系比較單純,沒有各式各樣的利益和利害關系介入,也不會受到基金項目的牽制,更不至于在師道尊嚴的堂皇名義下,蛻變成為某種人身依附關系。當然,師生關系取決于許多因素,具體的情況也各有不同,很難一概而論。但在八十年代的特殊氛圍中,學生與導師相處,相對容易,往往亦師亦友,關系密切而且平等,如同是忘年交。見面時除了匯報讀書修課的情況,還可以無拘無束地無所不談。
并不是所有的學生都有這樣的機會,但在袁先生指導下讀書,的確是難得的幸運。碰到隨意聊天的場合,師母楊先生也會加入談話。從時下的新聞、思想文化界的形勢、學術動向,到學生正在討論什么問題、讀什么書,甚至流行什么歌曲,我們都有過熱烈的討論和交流。這樣的談話一直持續到我留校教書之后。一九八六年,崔健的搖滾樂開始流行,一時轟動了校園,袁先生和楊先生也都十分好奇。有一次,談到興頭上,我還在他們的催促下,唱了一曲《一無所有》—那真是一段一無所有但又簡單快樂的日子!
除了上課以外,這樣的談話成了我的研究生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而談話的話題,范圍廣泛而又即興改換。有的時候,袁先生會順手拿起一本碑帖或畫冊,說到他最近讀帖讀畫的感想。而先生在自己的詩歌研究中,也旁涉詩論、書論和畫論。此外,或討論魏晉玄學的命題,或上溯《山海經》和《漢書·藝文志》中的“小說”概念。他還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收集海內外博物館和私家收藏中有關陶淵明的圖像,并精心撰成《陶淵明影像》一書。這一切都給我留下了一個潛移默化的印象,那就是文學、藝術和思想之間可以觸類旁通,左右逢源,而且讓我相信,學術可以帶給我一個自由翱翔的天空。這樣談話的時候,時間總是過得飛快。如果是下午見面,聊得晚了,就在先生家里吃了晚飯才離開。
事后回想起來,先生在“文革”之后百廢待興的這幾年中,正在全力投入學術研究和寫作,許多重要的著作和論文都完成于這一時期。可是,每一次我們見面談話,先生卻顯得那么從容悠閑,為了我這一個學生,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和精力。在今天看來,有些不可思議,而在當時,這又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從老師到學生,都不像現在這樣忙碌,甚至惶惶然,如有不及。到了今天,當時的那種狀態和心境,都已恍如隔世,因此也格外令人懷念。
袁先生帶學生,把做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在二○一五年北大的迎新會上,他代表人文學科的教授致詞,又一次說到了這一點:他希望年輕人在北大四年,能夠得到精神的修煉和陶冶,“保持人的尊嚴、理性和智慧,以及人格的獨立”,“一言一行都透露出人文涵養”。這樣的忠告,對于當今的大學生,應該說非常及時,也非常重要。但是又談何容易?在為人處世方面,袁先生和楊先生從來都嚴于律己,以身作則。與袁先生相比,倒是楊先生更心直口快,防患于未然:見到袁門弟子,她不時會耳提面命,諄諄教誨。有一次聽楊先生轉述她曾經說過的原話,用語之率真,幾乎令人絕倒。楊先生一九五七年后歷盡坎坷,但幾十年下來,她直言不諱的個性,一點兒都沒改變。
說到人文涵養,我還記得袁先生于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學年赴日本講學的一件事情:在他任滿返京之前,東京大學中文系主任伊藤漱平教授,給北大中文系主任寫信,希望袁先生能夠延聘留任,并在信中稱袁先生“學識淵博,人格高尚”,當時北大校報好像還做過報道。這是一則海外講學、載譽歸來的新聞,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尚未真正展開的八十年代初期,十分罕見,故一時傳為美談。不過,我后來才知道,事情原來并不簡單。按照當時的政策規定,東京大學付給先生的工資,一大半都上繳給了教育部和北大,剩下的余額,已經微不足道了。可想而知,袁先生在日本一年期間,過得并不容易。但他授課認真,敬業盡職,與日本同行交往時,持身謹重,不卑不亢,贏得了他們由衷的尊敬。
還有一件小事,我至今記憶猶新。一九七九年,林庚先生在第一教學樓講授“《楚辭》研究”,這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次授課,因此,不斷有系里系外的老師和同學前來旁聽。有的時候,教室里的椅子不夠,只好從旁邊的一間教室臨時挪用幾把。管樓的師傅本來就脾氣不好,見狀更是不依不饒。有一次,她沖進教室,當著林先生的面,大聲訓斥,并勒令大家當即把椅子全部歸還原處,場面一時頗為緊張和尷尬。那天,袁先生正好在場,只見他從人群中站了起來,首先把責任攬了下來,向師傅道歉說:椅子是我搬的。您也看到了,今天聽課的人多,座位不夠。但下了課,我們保證馬上把椅子搬回原處,請師傅諒解。把自己放在這個位置上,我自知不可能做得像袁先生這樣好。他的聲音和語調有一種磁性的親和力。
寫到這里,我忽然想到,不知先生讀了這一段文字,會做何感想。袁先生在北大生活了六十余年,這些磕磕碰碰的事情,難以數計,何足掛齒?恐怕早就忘在腦后了。當然,先生更不喜歡人為地替他拔高,好在我也沒想拔高。北大今天的情況應該已經大不相同了,但在那個時候,后勤和行政部門尾大不掉,衙門作風十足,還不時給人氣受,弄得不好,斯文掃地。像先生這樣,以低調平和的姿態,從容應對,不失尊嚴,但也沒有因此而變得憤激不平,牢騷滿腹,或在性情上留下任何陰影,靠的正是個人的涵養,盡管于情于理,憤激不平也絲毫沒有不對的地方,甚至還入情入理,至少是情有可原。在我的印象中,袁先生總是那么陽光。他是一位謹慎的樂觀主義者。
熟悉先生的人大概都知道,他在人前人后,從不說別人的壞話。遇到令人不快的事情,也很少會放在心上。他希望我們常念著別人的好處,多諒解別人的難處,他常說的一個詞兒是“感激”: 比起他那些歷經磨難的同學,先生覺得自己相當幸運,沒有什么抱怨的理由。
有一次聊天,不知說到什么話題—好像是提到了俄國的哪位作家,袁先生正好起身去接電話了,楊先生評論說:你的袁老師沒有俄國“情結”。我聽了有些愕然,怎么會呢?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尤其是讀文科的大學生,當年都多少經歷過俄蘇文化的洗禮。連我這“六○后”,還趕上了一個余波:在“文革”期間,誰沒偷著讀俄國小說,聽俄蘇歌曲?但轉念一想,可不是嗎?楊先生的話還真的有些道理。
平常聊天,袁先生也會談到俄國文學,說他沒有俄國情結,也可能不夠準確。不過,在袁先生的大學時代,全國上下以集體組織的方式,大張旗鼓地學習俄蘇文化,難免引人反感。記得先生自己說過,他向來是閑云野鶴的逍遙派,對這類有組織的、一邊倒的活動,沒什么興趣,在那些群情激昂的狂熱場面中,也顯得落落寡合,心不在焉,甚至還多少有些反感和抵觸。更重要的是,以先生的性格,我想恐怕也很難認同俄國小說中常見的自我戲劇化的傾向和斯拉夫氣質—當然,契訶夫的小說戲劇,還有屠格涅夫的一些作品除外。就個人的涵養和趣味情調而言,袁先生是傳統的、文人的。
一九九七年秋季,袁先生到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四個月,也應邀來哥倫比亞大學做演講。我記得先生隨身帶著一大摞稿件,在紐約短暫逗留的那幾天,一有空,就拿出來讀上幾頁,還不時在上面做修改。原來,先生正在主編四卷本的《中國文學史》,除了主筆其中的一些章節,還負責全書的統稿。在此期間,袁先生去過不少地方講學,后來還到西海岸轉了一圈,一路上都一直帶著這部厚厚的書稿。聽說有一次上飛機,前臺的工作人員打量了一下這件塊頭不小的行李,建議他托運。先生一聽,這怎么行?他寧愿把其他的隨身物品托運了,也不能冒這個險。最后,他用了一個小手提箱,才把書稿帶進了機艙。
我知道先生在此之前主編過《歷代名篇賞析集成》等大型著作,但《中國文學史》(一九九九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情況不同,參與全書撰寫的學者一共有三十位之多,來自全國各地的不同高校。因此,從全書的總體設計到最終完稿,經過了反復的討論和多方的協調配合,工程龐大而復雜。此后,除了他本人的學術專著之外,袁先生還主持并參與撰寫了數種多卷本的大型學術著作,從四卷本的《中華文明史》,到三十四卷本的《中國地域文化通覽》,還有正在進展當中的《新編新注十三經》等,并親自擔任其中最為艱巨而困難的《詩經校注》的工作。而在過去的幾年中,《中華文明史》也相繼被譯成了英語和日語等不同語種。
僅僅舉出上面這幾個例子,就可以了解先生的另一個側面,那就是黽勉做事的敬業精神和持之以恒的工作態度。袁先生主持這些合作項目時,我已經離開北大,也不可能參與,但他注重細節、事必躬親的作風是不難想見的。近些年來,先生的工作負擔似乎更有過于從前。每一次我回京探望,在客廳里坐不上多久,就會有電話進來,通常都是有事相商,而不是一般的寒暄。每當這個時候,袁先生也不免要感嘆:你可不知道我有多忙!在同輩學者當中,袁先生看上去身體并不算強健,甚至還小毛病不斷,但他節制自律、認真守時,辦事從不拖拉,因此往往承擔了超限的工作量,并且效率驚人。除非外出,先生每次收到郵件,都當即回復。有一天晚上,我通過附件傳過去一篇一萬多字的文章,沒想到,第二天一早打開電腦,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他不僅通讀了全文,還建議我補充一條新的材料。
提起傳統文人,我們通常想到的不是工作倫理,而是“目送飛鴻,手揮五弦”這樣“瀟灑送日月”的姿態,而且我們心目中的文人又以“業余精神”而為世人所知,跟敬業的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印象固然不無道理,但恐怕又都不夠全面,因為中國文人歷來有“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和盡心任事的傳統,只不過往往被今人忽略。從先生的學術生涯中,我看到了這一傳統的發揚光大。
當然,盡心任事,又絕非服役的苦差,而必須是樂在其中,才有可能保有持續的熱情和興趣。先生能夠幾十年如一日,鍥而不舍,不知疲倦地工作,正是因為對中國文化和學術,抱有極大的熱忱,甚至可以說是承載了一種使命感—這是一個文化上的擔待。北大很早就成立了國學研究院,袁先生出任院長,又擔任了大型學術刊物《國學研究》的主編,他在許多場合都談到了國學的重要性。不過,等到后來在媒體上出現了“國學熱”,先生卻反而顯得游離其外。他更感興趣的是腳踏實地做事情,從《中華文明史》的外文翻譯,到英文刊物《中國文學與文化》(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社)的創辦等等,他都不遺余力,從各個方面來促成和推進。而在實際生活中接觸到的袁先生,也從來不喜歡唱高調。他風趣俏皮,對周圍的世界充滿了好奇心,也經常能夠在日常的工作和平凡的生活中發現意想不到的樂趣。
今年初,袁先生的同事和學生就開始張羅著為先生祝壽,結果被先生叫停,最后只是由古代文學教研室的同事出面,舉辦了一個三十六人參加的小型聚會。王能憲兄邀請雕塑家吳為山為先生塑一小型銅像,以志紀念。為此,先生“效白樂天、蘇東坡和陶體,兼采啟功韻語筆調,口占一詩,以申謝悃,兼酬諸契交”。我遠在海外,未能與會,但傅剛兄和蘇東兄當天就通過微信把詩傳過來了,讓我聊補缺席之憾。這首詩題寫塑像,但處處都在自我調侃,充滿了詼諧和機趣,最后的兩句說:“相期十載后,重聚各無恙。”
這正是我所熟悉的袁先生,也讓我想起了先生的一樁趣事。先生當年在青島上中學的時候,學過一些英文,一九五二年入讀北大,改學俄文。此后歷經“反右”和“文革”的蹉跎荒廢,大有“學書學劍兩無成”的遺憾。“文革”后重新拾起英文,雖然已經不再可能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先生卻從未放棄,甚至還學得興味盎然。那一年來紐約,我陪先生去看世貿大樓和華爾街,他一路上主動用英文問路,而且應答自如,讓我十分驚訝。眼看就快到華爾街了,先生不放過最后一次機會。沒想到被問者直截了當,用手一指:“噢,那就是了。”對話練習到此打住。等那人走遠了,我們相視大笑。
記得大概是一九八六年,袁先生曾經請白謙慎兄為他刻兩個閑章,一句是“翼彼新苗”,另一句是“即事多所欣”。袁先生在陶淵明研究上,用功甚勤,成績卓著,而陶詩在先生的心目中,也正代表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最高境界。這里引用的前一句出自陶淵明《時運一首》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寫暮春郊游的欣悅感,在和煦的南風中,他看見新苗仿佛生出了拍動的翅膀。后一句見陶淵明《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二:“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這兩首詩寫詩人初春之際躬耕南畝的心情:因為南畝離住處有一段距離,陶淵明感慨自己還從未在那里下田耕作過。這一天他起了一個大早,裝備好車駕:“夙晨裝吾駕,啟涂情已緬。鳥哢歡新節,泠風送余善。”他像第一次晨起外出的孩子那樣,對這新的一天的開始,充滿了期待和歡喜。
至于“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這幾行詩,袁先生在他的《陶淵明集箋注》中注曰:“意謂雖未計算一年之收入,而即此目前之農事已多所欣喜矣。”又進一步闡發說:“‘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得道語也。做事原不必斤斤計較其結果,愉快即在創造之過程中。亦即只管耕耘,不問收獲之意也。”這樣的說法,也同樣適用于袁先生本人,或者可以說,正是先生的夫子自道。以只管耕耘,不問收獲的態度和“即事多所欣”的期盼心情與新鮮感受,投入每一天的學術工作,這是先生對自己的期待,也正是他在學術的道路上,鍥而不舍、永不怠懈的力量之源。
在祝賀先生八十大壽之際,我們也期待著先生今后為大家帶來更多的欣喜和收獲。
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于曼哈頓河邊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