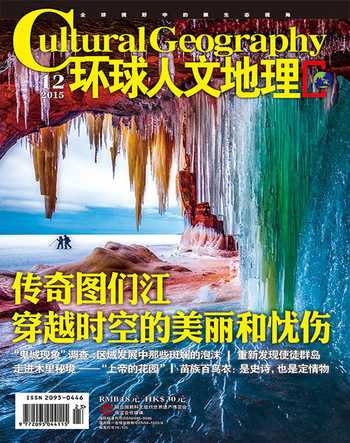樂山記憶 嘉州方物志異
龔靜染
“郡屬左蜀右?guī)`,山川原隰,六谷咸宜”(清嘉慶《嘉定府志》),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四川樂山處在蜀南平原與越西山地之間,水土滋潤(rùn),很適合谷物的生長(zhǎng)。當(dāng)年英國人威爾遜在中國西部采集的六萬多個(gè)植物標(biāo)本中,就有不少來自這一帶,最有名的如桫欏、珙
桐。但如歷史總有失蹤者一樣,方物也不例外,它們?cè)谝欢螘r(shí)間內(nèi)存在,而在以后的時(shí)光中卻神秘地消失了,而更神奇的是,除了一般意義上的物產(chǎn),樂山還有一些不常見
的靈異之物,可以說是幽深玄妙,讓人頓生尋覓之興。
蒟醬和瑞獸甪端、貔貅康熙《嘉州府志》中有一段話:“枸醬何狀,唐蒙食之,蜀人未之嘗也。概物產(chǎn)于嘉州,名實(shí)詎相副哉?”撰史者講出了樂山風(fēng)物歷史上的一個(gè)懸案。這里有段歷史故事:漢武帝初年,東越之亂平叛后,派唐蒙去傳諭南越。南越人款待唐蒙,美食中就放有蒟醬。唐蒙覺得好奇,便問蒟醬的來歷,原來蒟醬來自四川,是蜀人經(jīng)過夜郎國偷賣到南越的。撰史者在這里的疑問是:“枸醬”既然產(chǎn)于樂山,但當(dāng)?shù)厝藚s沒有嘗過其味,歷史記載是否與實(shí)際相符呢?“枸醬”又稱“蒟醬”,關(guān)于它的產(chǎn)地,《廣志》則直接說它就生長(zhǎng)在樂山。“蒟醬”生長(zhǎng)在一種胡椒科藤蔓植物上,果子長(zhǎng)得像紅瑪瑙,色澤鮮艷,可以用作藥材,醞釀成醬后,也可以作為調(diào)味品。其實(shí),“蒟醬”的珍貴就是到了明代也不減,馮夢(mèng)龍?jiān)凇队魇烂餮浴分姓f一罐蒟醬要值“五百貫足錢”,當(dāng)然非一般人所能享用。
在歷史上,嘉慶年間是清朝一?個(gè)特殊時(shí)期,人心動(dòng)蕩、社會(huì)復(fù)雜、暗潮洶涌,民間的詭譎之事也多,這在史志的方物記載上也有體現(xiàn),如嘉慶版的《嘉定府志》中就出現(xiàn)了“甪(lù)端”和“貔貅”的記載。“甪端”是一種獨(dú)角獸,形似豬,角長(zhǎng)在鼻端,象征祥瑞;而“貔貅”也是一種瑞獸,被民間稱為招財(cái)神,有守護(hù)避兇之意。其實(shí),這兩種獸都是民間傳說中的神異動(dòng)物,非真實(shí)存在。但在《隴南余聞》中關(guān)于“甪端”是這樣說的:“產(chǎn)瓦屋山,不傷人,惟食虎豹,山僧恒養(yǎng)之,以資衛(wèi)護(hù)。”而關(guān)于“貔貅”,《隴南余聞》中說:“產(chǎn)峨山,白木皮殿以上有之,形類犬,見人不驚,群犬常侮之,其聲似念陀佛,非猛獸也。”這里的記載是有鼻子有眼,可見民間傳說很盛,而被史官堂而皇之地記入正史的“毛之屬”中,更讓人大為驚嘆,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民眾的心理狀況也可見一斑。雪方池、燕支木和婆欏花在嘉慶版的《嘉定府志》中,提到了幾種過去沒有提及的東西:“雪方池見賞于《清異錄》,燕支木見稱于《徂徠集》,婆欏花則石湖詠之,王母桐花鳳則《峨山志余》載之。”
“雪方池”其實(shí)就是一種白色透明的硯臺(tái),只是甚為珍貴,相傳硯材產(chǎn)于峨眉山上。其實(shí)樂山出好硯,陸游也曾經(jīng)有一塊,是從大渡河里淘來的,“質(zhì)如玉,文如縠”(《蠻溪硯銘》),“文如縠”的意思是,硯臺(tái)的紋理如有皺紋的細(xì)紗,“雪方池”當(dāng)然就更加神奇了。“燕支木”又是什么呢?這是傳說中的一種靈木,傳說可以洞悉三世姻緣。古時(shí)把胭脂又稱作是燕支,“燕支木”其實(shí)就是胭脂木,“胭脂木,嘉州出”(清嘉慶《嘉定府志》)、“燕支木見稱于《徂徠集》”,而這個(gè)《徂徠集》就是石介的詩集。
宋景三年(1036),石介被任命到嘉州做軍事判官,但他到樂山赴任才一個(gè)多月,就得喪報(bào)回了山東老家,一去不返。雖然他在樂山待的時(shí)間極短,卻留下不少詩篇,其中就有關(guān)于“燕支木”的內(nèi)容。如“江山如畫望無窮,況屬升平歲屢豐。萬樹芙蓉秋色裹,千家砧杵月明中。斷霞半著燕支木,零露偏留筀竹叢。只欠流杯曲水宴,風(fēng)流未與左綿同”(《嘉州寄左綿王虞部》),其詩中的“燕支”、“燕支木”、“燕支板”都與胭脂有關(guān),證明樂山產(chǎn)“燕支木”,由于樹種珍稀,多為文房中使用;但清嘉慶《嘉定府志》上說“此木今亡”,讓人惋惜。
“婆欏花”又稱優(yōu)曇婆欏花,是傳說中的仙界極品之花,乃佛家花卉。其花形渾圓,猶如滿月,有瑞祥之氣,“三千年一現(xiàn),現(xiàn)則金輪王出。”(《法華文句》)當(dāng)然這都是被神化了的傳說,真實(shí)的婆欏花并不多見,我們只能深吸歲月之悠遠(yuǎn)清芬。志書中所謂“婆欏花則石湖詠之”,石湖即南宋大家范成大,范成大于淳熙二年(1175)在成都當(dāng)四川制置使,
南宋淳熙四年(1177)離任后從岷江轉(zhuǎn)入長(zhǎng)江回蘇州,其間著有《吳船錄》,其中多有關(guān)于樂山的記載,范成大要詠婆欏花,也一定是在此間的所見所聞。但“婆欏花”既然如此珍稀罕見,范成大以游客的方式路過樂山,就能隨意見到這種神奇的植物?所以,我倒認(rèn)為他可能見到的是廣為人知的“娑羅花”,也就是高山杜鵑。不過,高山杜鵑仍是珍稀植物,“生峨眉山中,類枇杷,數(shù)葩合房,春開,葉在表,花在中,或言根不可移,故俗人不得為玩。”(《益部方物略》)這個(gè)“俗人不得為玩”倒跟“婆欏花”的清高氣質(zhì)有些相似,《嘉州府志》說它“皆生在峨山頂三四十里以上,移之山半則萎矣”,更增加了這種可能性。
嘉州珍禽記趣
“桐花鳳”是四川一種小巧的珍稀鳳鳥,身長(zhǎng)不盈寸,全身翡綠色,燦爛之極。《峨山志余》中的記載不詳,在唐李德裕《畫桐花鳳扇賦序》有記載:“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暮春,有靈禽五色,小于玄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華落則煙飛雨散,不知所往。”在清朝李調(diào)元的《南越筆記》中也有記載:“桐花鳳,丹碧成文,羽毛珍異。其居不離桐花,飲不離露。桐花開則出,落則藏。蓋以桐花為胎,以露為命者也。兒女子捕之,飲以蜜水,用相傳玩。此種蜀中亦有。”說明“桐花鳳”不僅四川有,南越諸地也有。
當(dāng)年蘇東坡就回憶過他小時(shí)候見到“桐花鳳”的故事,“桐花鳳”在后來更多地被賦予了文學(xué)色彩。李清照曾有名詞《蝶戀花》,其中“乍試夾衫金縷縫,山枕斜欹,枕損釵頭鳳”為一時(shí)佳句。500年后,清朝詩人王漁洋步易安之韻和出了“憶共錦衾無半縫,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的詞句,其語意之深婉甚于李清照。
說到鳥類,樂山有兩種鳥特別有趣:“嘉定州有鳥,一名山和尚,一名雨道士,堪稱對(duì)偶。”(明·陸深《蜀都雜抄》)這兩種鳥都是玩禽,應(yīng)該比較常見,但因?yàn)槭撬酌缃竦娜藗儏s很少知道它們到底是什么鳥。民國《犍為縣志》上說:“山和尚,比紫翠差,大頭圓”,可惜描述并不確切,但“大頭圓”可能就是得名山和尚的原因,而“雨道士”則不甚了了,沒有任何解釋,是不是全身黑色、羽毛修長(zhǎng)的一種鳥?既然有類比,其形象一定有相似性,當(dāng)然也就愈加神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