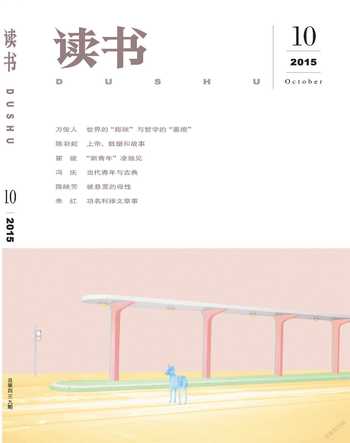被懸置的母性
陳映芳
在新時期以來的各種文學作品中,有不少兒女聲討母親或以扭曲的母子關系為題材的作品,以至于 “母愛缺失”、“母性喪失”這些詞語曾成了文學評論的熱門概念。同時期,在學術界也曾有《發現母親》(王東華著)這樣的專著,以洋洋八十余萬言痛陳母愛缺乏之于中國發展之危害,十多年來一版再版,影響廣泛。
作家的成長,以對童年精神傷痛的展示為方式,原不是特殊的現象。但一代作家不約而同地對“母親”展開集體控訴,這無論如何是值得關注的。它不只是文學現象,也應該被視為社會事件。此前,筆者因為研究中國歷史變動中的“青年”,以及八十年代的青年文化,曾搜集、閱讀過一批文化人的童年回憶,那其中多涉及“母親不在”的情節和感傷,如王朔談父母對孩子的疏離和冷漠,還有不少人回憶幼年時在全托幼兒園刻骨銘心的寂寞記憶……令人印象深刻。這其中,以李南央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和老鬼的《血色黃昏》、《我的母親楊沫》等為代表的非虛構作品,尤其因為作者以其親身的經歷、對他們的親生母親所做的凌厲批判,引起了社會極大的反響。
中國的母親們,究竟出了什么問題?
有關李南央的母親范元甄、老鬼的母親楊沫,以及她們所代表的革命女性們的母性問題,近些年已經有不少的分析和評論,包括她們的老同事們所做的歷史分析,還有李南央和老鬼這些子女們的痛苦反思。相關的討論深入到了革命歷史中的諸多悖論,也涉及了心理學的問題,還有親人間如何達成“寬恕”這樣的嚴肅話題。但是,筆者在有限的閱讀中,覺得有一個重要的當事人群體其實是沉默的,我們幾乎聽不到她們的表達或申辯—母親們,她們對于自己備受質疑的母性、對于子女們的控訴,是如何想的?那些母親中不乏女作家、女干部,她們應該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和話語權,但是,很遺憾她們沒有留下我們所期待的文字。我們知道,范元甄曾對女兒的某些記憶文字做出過反駁,也曾以她的方式對女兒表達了她的憤怒,且直到告別人世,她也沒有原諒女兒的行為。而楊沫做出了另一種回應:她在晚年回歸家庭生活,努力扮演了一個正常的母親角色,母子間也因此相互獲得了對方的諒解。
但是,對于被問題化的那個時代的“母性”,她們都沒有做出自己的解釋或辯護。
在這里,為便于分析,筆者且將那些被控訴的母親們大致區分為兩代人:革命年代的女性和社會主義時代的女性。先說社會主義年代的女性,這里主要是指上世紀五十到六十年代經歷了生育體驗的年輕的母親們。她們在社會主義工業化以及農村人民公社化的年代中,被要求全身心地投入到勞動生產/國家建設事業和各種政治運動中,她們的孩子或者被放入各種幼托機構,或者被交托給老人們照看,她們中的許多人在家庭和工作之間顧此失彼、精疲力竭,無可奈何地成了“王朔母親”式的媽媽。
這里所說的革命年代的女性們,正是李南央和老鬼的母親們。她們是曾經的進步學生、熱血青年,由民族危機和正義理想而投身于革命和戰爭。她們原是追隨著新文化的潮流從舊家庭(及其父權/夫權)的束縛中掙扎出來的“新女性”,她們也可歌可泣地為民族國家的事業貢獻了自己的青春。但她們在革命歲月中,無可避免地被嵌入到了那一個男性主導的權力體系內,同時又主動或被動地被安排到了一個個“革命家庭”中。一九四九年后,她們成了革命干部或干部太太,在許多回憶文字和文藝作品中,她們被稱為“大姐”或“馬列主義老太太”,被人崇敬,也飽受揶揄,更有一些人因為兒女的控訴而被當成了“被政治異化了的母親”的活標本。
這兩代母親,生命歷程各有不同,對母親角色的認同似乎也有較明顯的差異。但當面臨兒女們的激烈控訴或曲折指責(不少作家是通過虛構作品來抒發其母愛缺失的情結的)時,她們總體上都呈現了一種失語的狀態。她們應該會感受到憤怒和委屈,但可能不清楚該用什么理由來為自己辯護(除了那些被子女們認為是老套的陳舊教條之外),在經歷了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那樣的歷史轉折之后,母親們很難找到溝通兩代人心靈的有效方式。
但是,我們其實不難想象,在過去幾十年中,同時扮演著革命者和妻子/母親角色的她們,經歷了怎樣艱難的歲月。今天我們在一些回憶文字中,可以看到她們被組織安排婚姻時的掙扎,也可以看到她們曾承受婦科疾病和經歷難產等的身體病痛,更可以讀到嬰兒病死或被送給老鄉的情節。這些往事,雖然大多是被當作她們革命生涯的一部分而被回憶、被記載,她們的孩子們的保育院記憶在今天也被當成了佐證其身份的光輝歷程,但是這其中的種種悲劇性,我們仍不難去讀取、去體味—今天我們已經能借助于一些新的思想資源和學術文本,去重新梳理、重新審視現當代中國人家庭生活的歷史。例如記錄并探討了社會主義國家家庭制度演變歷史的《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它告訴我們,“家庭”的價值正當性和現實中正常的家庭生活,是如何被一種意識形態所否定,又是如何被國家制度實際取締的。又例如,郭于華教授的《受苦人的講述:驥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它讓我們通過歷史過來人的敘述,得以感知到在宏大歷史的背后,一個個具體的人是如何承受具體的痛苦的。在著眼于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體的敘事中,郭于華將當代中國農村婦女所遭遇的“身為母親無法正常地喂養和照料年幼的孩子”的經歷,定義為一種“苦難”—“婆姨們每日參加集體勞動所遭遇的另一種苦難”。她通過采訪,讓那些母親們將生活體驗訴說出來,連帶她感受到的那些母親們的“心痛”(“一位母親至今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還是淚水漣漣”)。通過她的記錄,被強制參加集體大田勞動的母親們所感受的不亞于身體病痛的“母親對于孩子的牽掛心痛”,穿越幾十年的時空,被呈現在我們面前:
滿月了四五十天就動彈上了。奶娃娃,人家歇(晌)了,我們杠(跑)回來奶來了。那照也沒人照,我們那老人也不照去,走起急的你哭鼻子,回來看到娃娃又要急的你哭鼻子。我們那二女子(小時候),那陣炕上不鋪個氈,就鋪個那爛席子,娃娃猴(小)著了嘛,娃娃頭發又稀,給娃娃頭發一滿擦的稀爛,腳底上擦爛。可心疼了,邇個也常想著了,真個。
在這樣的語境中,母親們既是母愛缺失的責任人,更是特殊文明下母性受到嚴重摧損的受害者。
當然,與投身革命事業的“新女性”們不同,這些農村的“婆姨們”,是被動地被卷入到了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中,按孫立平教授在郭著的“序”中所做的定義,她們是“被革命卷入者”。用一些革命女性(如楊沫)的話來說,那樣地疼愛孩子,是“動物本能”,是沒有水平、沒有覺悟的“家庭婦女”才會有的表現(老鬼:《我的母親楊沫》)。覺悟了的“革命女性”、“職業女性”們,似乎是不屑于,也不愿意將自己定位于母性受損的可憐的舊式婦女的,即使她們為自己自覺不自覺的選擇付出了種種代價—這些代價包括對正常的愛情生活/家庭生活的犧牲,以及與兒女間形成的種種情感隔閡。跨越歷史、打破隔閡,需要自我否定的特殊勇氣和客觀的機緣,也需要對宏大歷史的審思能力,這對許多母親來說,并不是容易的事。
問題在于,無論母親們的社會身份是什么、她們的階級覺悟有多高,她們都應該是有“心靈”的。孫立平將他給郭著所寫的序言取名為“傾聽‘被革命卷入者’的心靈”,或許正是點出了被各種“通識”所蒙蔽了的人類社會的一個基本“常識”:人之為人,是因為人性,人是應該擁有心靈的。那些在革命年代曾十月懷胎、一朝分娩的女同志、女戰士們,她們除了在極為貧乏的醫療環境、物質條件下承受過巨大的身體之痛,她們也可能因為不得不將親生骨肉交給陌生的農民而感受過母性受損的心靈之痛。如果不是因為客觀情景下不得不為,又如果不是因為她們所承受的痛被賦予了“犧牲”的意義,她們的選擇行為被賦予了神圣性,她們如何能承受這樣的傷痛?
還有一個疑問需要提出來:如果我們相信母性和父性都兼具社會性和生物性,我們又假設每一個孩子都是渴望得到父親和母親的關愛與照料的,那么,為什么,在革命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代中曾同樣缺位于家庭生活的父親和母親們,單單是母性受到了質疑,單單是母親的角色受到了指責和批判?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男人們不再能安于當一家之主,他們被期待為國奉獻。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父親們同樣也曾經歷了一個角色更新的歷程。只是,男性們在他們所扮演的革命者角色和父親角色之間,看起來并沒有發生新女性們那樣的困境。在這些年的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少理想的父親形象。一個現成的例子就是李南央的父親李銳。這是一個在革命事業中歷經磨難而不改初衷的理想主義者,同時在女兒心目中又是一個關愛孩子且屢遭妻子背叛卻還能顧全大局的父親。另一個豐滿的父親形象可列舉《巨流河》中的齊世英先生。臺灣作家齊邦媛教授在她的自傳錄中,以濃重的筆墨描寫了齊世英的一生,那是一個為國奉獻畢生而又重情重義的志士形象。散文家王鼎鈞評論說:“《巨流河》中的父親,可能是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中最成功的形象,齊老一生率領志同道合的人出生入死,國而忘家,最后都被大浪淘盡……”身為父親,雖“國而忘家”,卻仍能為兒女所崇敬,更能打動千萬讀者的心,這說明近代以來的“父親”,是可以因為“以天下為公”而舍“一家之私”的。這固然可以被理解為“忠孝不能兩全”這樣的傳統政治倫理在現代的延伸,但另一方面,也因為這樣的父親,即使是將照顧子女的責任交托給了母親,但時時處處,還會流露出對家庭和子女的責任及關愛,其“父親”之人性光芒,不僅有女兒的感受及知識成就可以折射,更還有如齊世英在抗戰中收留、照顧無數東北流亡學生這樣的大愛來證明。換句話說,“志士”與“父親”這兩個角色,不僅沒有呈現對立與沖突,反而是可以互相證明的。
這樣說來,在中國人的父母觀的現代變遷中,父親與母親的角色更新的機制是迂回不同的。又或者可以說,在啟蒙的思潮中,父性與母性受到了不同的對待。我們知道,新文化運動以來,“女性”在中國是曾被明確地區分成了新與舊的,“新女性”是跟隨了新時代的腳步走出了家庭的娜拉們,她們要掙脫的是社會對舊女性的一切束縛,包括賢妻良母的角色規定。而男性在近代中國似無新舊之分,男人們曾面臨的選擇主要是“新青年”與“舊青年”之區別。新青年是“覺醒了的人”,他們不應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滿足于充當家族的統治者,他們必須同時肩負起拯救民族、改造社會的使命。那么,作為新青年的中國男性在家里該怎么重塑他們的父親角色呢?按青年導師魯迅先生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的啟示,他們是要告別傳統的、壓迫婦女和孩子的父親角色,而成為開明進步的父親—“沒有法,便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具體來說,一是“理解”(理解孩子的世界與成人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二是“指導”(長者須是指導者、協商者而不是命令者),三是“解放”(讓孩子成為自立的獨立的人)。
“開明進步”,這正是我們評判一個現代好父親的重要標準。這樣的父親,接受了新式教育及現代文明的熏陶,或受黨的教育,在外可以拯救民族,可以以社會事業/職業生涯為重,在家亦可以釋放出曾被舊倫理長期禁錮的舐犢之情,其親子關系模式且符合現代民主、自由之新潮。齊世英、李銳這樣的父親們所以能被他們的兒女所鐘愛并為社會所敬重,蓋因為他們所呈現的父性,都具有魯迅倡導的、社會所期待的那一種新父親的品質(當然社會還廣泛地接受另一些帶有傳統色彩的父性──例如堅韌、奉獻、沉默如山的父親,這一種父性曾由羅中立的油畫《父親》所呈現)。無論如何,文化啟蒙、革命、工業化以及社會現代化等等,讓中國的男人在父親角色與人性之間,找到了一條新的出路,讓父性有了符合現代價值的落實。以這樣的父親觀為背景,我們可以看到,在家里依然實施“專制統治”的父親或對孩子施以暴力的父親們(如王朔的父親那樣),會受到孩子的抵制和譴責,但父親若是為了革命、為了國家而棄家不顧,則是可以被孩子和社會接受的。
但中國的母親們顯然缺少這樣的機運。中國人的母親觀是分裂的,中國社會的結構與制度也往往讓母親們無所適從。這些年來,我們可以從文學作品中,讀到許許多多的感念母親、頌揚母性的動人作品,那里面,有忍受所有苦難、甘心情愿地為丈夫/為家庭/為兒女犧牲一切的偉大母親,也有具備現代知識卻能盡心相夫教子、全力支持丈夫兒女打天下的完美母親。無數動人故事所呈現的社會的理想母親觀,大多是家庭本位的,是以男性及孩子為中心的。可是這一百多年來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除了一再地教育女性要“解放”、要“獨立”外,還持續地將婦女動員、驅趕到革命/戰爭和生產勞動的第一線。在“家庭”、“國家”與那個可能存在的“自我”之間,被各種“奉獻”期待所撕扯的女性,該如何面對自己的母性、能怎樣去扮演母親角色,這成了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女人實實在在的一個大難題。
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過去的故事所以讓人難以忘懷,是因為我們正面對著當下。“母愛缺失”是八十年代提示給我們的一個社會議題。那以后,筆者將這個問題帶入到了專業的教學和思考之中。這些年來,筆者所指導的學生中,先后有兩位同學將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確定為論文主題,一位是博士研究生,另一位是本科生。去年春天,當那位博士生結束論文答辯、聽到論文獲全票通過的結論時,他百感交集以至泣不成聲。后來我回顧他的研究歷程,多少能意識到,這樣的題目對于他意味著些什么。十多年前,當他在研討會上最初提到留守兒童的問題時,我沒有多加思索,就將八十年代的那一個歷史議題帶了出來:中國的父母們為什么能將孩子的養育責任托付給機構或他人?當時我并沒有預想到,這樣的一個似是而非的歷史命題,給曾經在鄉村學校當過老師的這位學生造成的是一種什么樣的困惑:留守兒童們不僅承受著因父母不在而面臨的種種生活困難,他們還被社會貼上了種種問題標簽,諸如學習成績差、心理素質差、情感體驗缺失等等,這對他們是不公平的。而另一方面,他們的父母難道是應該被指責的嗎?最后,他的論文通過實地調查和數據分析,證明了留守兒童的成績并不比父母在老家的孩子差(在他的調查中,內地農民不外出,往往不是出于對孩子親情需要的考慮,而恰恰可能是父母的能力不夠或責任心不強),而留守兒童的升學之所以能夠繼續、他們之所以能夠進入較好的學校,正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外出打工為他們提供了必要的經濟支持。與此同時,鄉村教育存在的種種問題,根子主要在于教育資源分配的嚴重不公;孩子們無法跟隨父母一起外出,則主要是因為他們無力承擔城市的生活支出和教育費用,事實上他們還面臨著城市教育的種種門檻。
這是個讓人備感無力的邏輯困境—父母們不得不離開孩子,母親們無法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理想的母職,不再是因為她們要爭取婦女解放或實現個體的人生價值,也不再是為了要為國奉獻,她們僅僅是“為了孩子”。這樣的生活悖論,這樣的選擇難題,與過去一百多年來中國女性所經歷的情景固然不盡相同,可是,對身處其中的母親們而言,這其中的歷史連貫性,應該不難被發現(類似的選擇難題也存在于城市,由于公共保育設施的嚴重缺乏,生育與撫育正成為今天無數家庭的沉重話題)。
可是困境還將延續—如果說八十年代的年輕人尚能在價值轉型時期對他們的母親發出質疑,那么,若干年后,當長大了的留守兒童一代回憶起自己母愛缺失的童年,面對“為了孩子”而漂泊于城市打工掙錢、犧牲了正常的親子生活的老人,他們還能夠發出義正詞嚴的指責嗎?他們如何才能跨越今天這樣的歷史而讓兩代人的心靈得到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