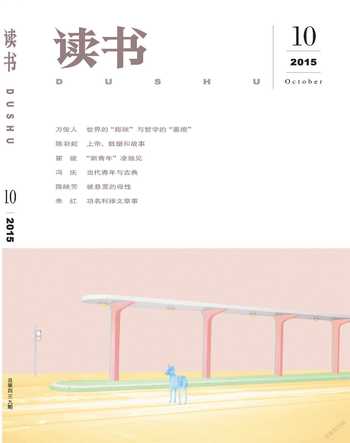外位性理論與個人主義的危機
羅衛(wèi)平
方方的小說《涂自強的個人悲傷》二○一三年初發(fā)表之后,引起了頗大的社會反響,成為諸多青年文學研究者近年來討論最多的小說之一。這部小說之所以特別觸動青年研究者,是因為大家了解大學畢業(yè)后變成“蟻族”的同輩青年的境遇,也對“拼爹”現(xiàn)象日趨嚴重和貧困代際傳遞的現(xiàn)狀感同身受。這部小說最后通過涂自強同學之口,說出了“蟻族”青年涂自強的悲劇包含的問題:“這果然只是你的個人悲傷嗎?”有評論者指出,這一悲劇事實上呈現(xiàn)了個人主義意識形態(tài)在今天遭遇的危機,人們強烈意識到,社會關(guān)系和社會資本積累對于個人生活歷程的高度重要性,開始從經(jīng)驗上發(fā)現(xiàn),八十年代以來彰揚的“個人奮斗”意識其實只是一種錯覺,個人總是處于一定的社會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之中。這樣看來,個體的自我需要直面自我如何建立與他人的社會關(guān)系的問題,包括個體之間通過何種形式組織起來的問題。
這也提示我們,個人主義應(yīng)該成為理論反思的對象。而從這個角度切入,或可重新理解巴赫金對話理論的內(nèi)涵和意義。巴赫金的對話理論揭示了一種值得探究的主體構(gòu)建圖景:人無法脫離他者而存在,自我與他者對話的過程,也就是主體構(gòu)建的過程。他指出,“理解”的對話性特征,根源于“我生活在他人話語的世界里”這一基本事實。“我的全部生活”,都是在他人話語中定位,都是對他人話語的反應(yīng);“對每個人來說”,“用話語表現(xiàn)的一切”“都分解為二”,一個是自己的話語的狹小世界,另一個是他人話語的無邊世界,“這是人類意識和人類生活中一個基本事實”(《巴赫金全集》第四卷,407頁)。人無法脫離他者而存在的狀況,就是所謂“外位性”。巴赫金所說的外位性(空間上的、時間上的、民族的)是“理解”的本質(zhì)特征,所有理解都有外位性,并沒有那種不需外位性的“理解”,“一般來講,要擺脫外位因素的實體存在恐怕是個無法實現(xiàn)的任務(wù)”(同上,521頁)。巴赫金毫不客氣地指出,上述基本事實其實“至今很少研究(很少被人意識到),至少沒有意識到它那重大的原則性意義”(同上,408頁)。
由此看來,把握巴赫金關(guān)于自我與他者對話的論述,外位性理論是關(guān)鍵。邱運華在收入《靜默的旋律—學術(shù)史與文化研究》的多篇論文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他指出,外位性理論貫穿了巴赫金的全部學術(shù)活動,進而成為一種有關(guān)人文學的理論。巴赫金在《論人文科學的哲學基礎(chǔ)》和《人文科學方法論》等札記中明確指出,所有的人文學科都帶有外位性和對話的特征,如果我們認為有的人文學科并不具有外位性和對話的特征,那只是我們并沒有意識到而已。
巴赫金將精密科學與人文學科相對比,指出人文學科是主體對主體的認識,“只能是對話性的”。精密科學是“獨白型的認識形態(tài)”,其中只有一個主體—認識(觀照)和說話(表述)者,與他相對的“只是不具聲音的物體”。但是,人文學科是一個主體對主體的理解,主體本身不可能作為物來感知和認識,因為他作為主體,“不能既是主體而又不具聲音”。因此,認識另一主體的積極性,就是“認識者的對話積極性”(同上,379頁)。在巴赫金這里,對話性是“理解”無法擺脫的特征。
巴赫金指出,在研究“語言”以及“意識形態(tài)創(chuàng)作的各個不同領(lǐng)域”時,人們避而不談“所有話語都分為自己的和他人的兩類”這一基本事實,而是認為存在著一個“抽象的第三者立場”,人們把這個第三者立場等同于一般的“客觀立場”,等同于一切“科學認知”的立場。他認為,在“抽象的科學認知領(lǐng)域和抽象思維領(lǐng)域”中,才可能有所謂“第三者立場”和“客觀立場”,但在人文學科(“關(guān)于精神的科學”)中不可能有這樣的立場。人文學科的研究對象,不是一個“精神”,而是兩個“精神”(一個是被研究的精神,另一個是從事研究的精神,兩者不應(yīng)合為一個精神),是不同“精神”間的相互關(guān)系和相互作用。對于巴赫金而言,那種認為人文學科有“第三者立場”和“客觀立場”的看法,不過是對人文學科的一種假想和誤解。
巴赫金對外位性和對話的思考,是在康德將人視為認識主體與認識對象的復合體的基礎(chǔ)上的推進。福柯在論述人文學科的重要著作《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中分析了作為現(xiàn)代思想和人文學科基礎(chǔ)的康德的“人類學”,那就是,“當自然史成為生物學,當財富分析成為經(jīng)濟學,尤其當語言反思成為語言學,以及存在和表象共同所處的那個古典話語消失時”,人與其模糊位置一起出現(xiàn),“即作為知識對象和認識主體:被奴役的君主,被注視的觀察者”(《詞與物》,莫偉民譯,406—407頁)。在這樣的關(guān)于人的“有限性分析”中,人是一個“經(jīng)驗—先驗復合體”,人既是認識的主體又是認識的對象。在福柯看來,這一“經(jīng)驗—先驗復合體”形成之日,才是現(xiàn)代性的開端,而不是“人們想要將客觀的方法運用于人的研究的那個時刻”。福柯的這一分析,指出了康德的批判哲學帶來的哥白尼式革命,將西方現(xiàn)代人文社會學科的基本問題設(shè)定為“我如何能知”,而不是古典時代的“我知道什么”。《發(fā)言與講座》所收的“巴赫金的講座”(一九二四年十至十一月)顯示,當時巴赫金特別關(guān)注新康德主義馬堡學派,并與《審美活動中的作者與主人公》的寫作有密切關(guān)系。其中指出,“康德的了不起”就在于打破了人僅僅作為“自然主體的整體”這樣一個“統(tǒng)一體”。參照福柯的分析,在古典時代,知識與普遍智力訓練的恒常而基本的關(guān)系,證明了有關(guān)一個最終統(tǒng)一的認識體(un corpus)的設(shè)想,而在十九世紀初,智力訓練的統(tǒng)一性被打破了,突破途徑之一是區(qū)分先驗主體性與客體的存在方式。
巴赫金承續(xù)和推進了康德有關(guān)人作為認識主體的有限性的思考。在康德那里,作為認識主體的人存在于各種經(jīng)驗事物構(gòu)成的可能性條件之中,具有歷史的厚度與縱深,同時也是有限的。同時恰恰基于這種有限性,人會不斷努力去突破這些局限,從而使現(xiàn)代生物學、經(jīng)濟學和語文學得以誕生。在巴赫金這里,外位性與對話理論進一步凸顯了“他人話語”對于人這一認識主體不可或缺的限制性意義,即“他人話語”是主體形成的條件。“我”只有在與其他的對話者互動的過程中,只有通過他人的話語,才能形成自我的主體意識,這是“我”的有限性所在。
巴赫金相對于康德最為重要的突破是,他認為主體認識活動的主要空間在于話語層面。無論是外位性,還是對話,都是就話語(自己話語與他人話語)而言的。巴赫金提供了一個在話語空間中構(gòu)建主體性的特別場景,那就是,在多種“語調(diào)”對話構(gòu)成的話語網(wǎng)絡(luò)和話語場域中,自我總是在某個時刻獲得某個暫時的位置。“外位性”意味著自我構(gòu)建的一個必要條件是,自我內(nèi)部要包含有異質(zhì)性的他者存在。自我內(nèi)部的他者與自我無法分離,但自我也無法將異己的他者完全吸納。因此對于自我而言,“外位性”也有內(nèi)在性的一面;“對話”是外在性與內(nèi)在性的結(jié)合。總的來看,居于流動位置的自我,既不是意義的仲裁者,也沒有真理在手,只是不斷通過與他者的對話構(gòu)建自身,這是自我的主體性構(gòu)建的基本事實。
在認識“我生活在他人話語的世界里”(以及必須通過“他人話語”構(gòu)建主體意識)的基本事實的基礎(chǔ)上,人們可以自覺地運用外位性這一“最強大的推動力”,以盡可能地發(fā)揮創(chuàng)造性和充實自己。巴赫金批判“教條主義的惰性”,認為抱殘守缺的教條主義“不可能自我豐富”。他指出,“理解者不應(yīng)該排除改變或者甚至放棄自己原有觀點和立場的可能性。理解行為中包含著斗爭,而斗爭的結(jié)果便是相互改變,相互豐富”(《巴赫金全集》第四卷,406頁)。在文化對話和經(jīng)由他人話語構(gòu)建自身主體性的過程中,“‘我’和‘他人’永無休止地互相爭論”要更為重要。并不是客氣和諧的并存才是對話,反而是互相爭論使得對話更有分量、更有意義,使得自我主體構(gòu)建更為充實。對于自我與他人社會關(guān)系的建立、對于社會共同體營構(gòu)而言,這無疑是真知灼見。
(《靜默的旋律—學術(shù)史與文化研究》,邱運華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