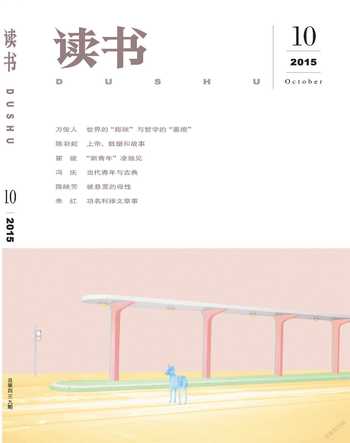三個德國人,必有一社團”
李伯杰
德語中有一句諺語:“凡有三個德國人在一起,必有一個社團。”(Drei Deutsche:ein Verein)意謂德國人特別喜愛結社。無論是德國人自己,還是外國人,都認為德國人特別熱衷于結社及過社團生活。有鑒于此,德語中才產生了用以形容這種現象的名詞,即“結社癖”(Vereinsmeierei),而特別熱衷于結社及社團事物的人,也被稱為“結社狂”(Vereinsmeier)。據“德國協會及聯合會全國聯盟”的統計,目前在全德國范圍內,德國的注冊社團共有五十九萬四千多個。半數以上的德國人都參加社團,而且各種社團的數量在過去十五年里翻了一番。
不過這句諺語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德國民法典》第五十六條規定,不是三個人,而是七個及七個以上的人聚在一起,并且擁有一個社團章程且明確規定領導機構的權限范圍,方能組成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社團。當然諺語畢竟是諺語;盡管這句諺語在法律上站不住腳,但是它想要表達的是德國人結社的欲望之強烈。
此外,所謂“三個德國人一個社團”,即德國的社團密度為歐洲甚至世界之最,也多少有些言過其實,實則是一個誤區。在英倫三島,也有類似的諺語,如“只要有三個威爾士人在一起,他們必定組建一個委員會”云云。所以,德國的社團雖然絕對數字巨大,但是其社團密度卻并非歐洲之冠,而是被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及荷蘭甩在了后面。在歐洲,各民族結社的欲望分布不均,北強而南弱,處在中歐的德國則處于中等偏上。當然,盡管實際上德國社團的密度比不上北歐國家,但是社團在德國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或是德國自己認為社團在德國人的生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在德國的各種社團中,人數最多的當數各種體育社團,其比例為所有社團的38%。在德國,結社的歷史源遠流長。中世紀時,德國城市里的市民就組織了各種職業行會,以保護各行業的利益。十七世紀時,各種語言協會紛紛建立,以保護和發展德語。到了十八世紀,各種協會,特別是文化協會,乘著啟蒙運動的翅膀經歷了第一次發展熱潮。而且這時眾多的文化協會有一個新的特征,即消弭了等級差別,英雄不問出處,唯一的條件是必須要有熱情、聰明睿智和文化修養。此外,柏林的“星期一俱樂部”也名噪一時;德國的各種讀書會、外借圖書館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建立。
但是直到十九世紀初,大規模的結社浪潮才席卷了德意志大地,德國人的結社運動才真正起飛。在隨后的十九世紀中葉,德國人的結社癖達到高潮。無論社團的數量還是種類,都得到了長足發展,社團不但在傳統的信仰、娛樂、職業、公益等領域活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滲透進政治領域。
德國的大規模結社運動肇興于十九世紀初,在十九世紀中達到頂峰,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傳統,至今還影響著當代德國人的生活。為何不早不晚,恰恰是在這個時期?答案只可能在當時的歷史環境里尋找。無獨有偶,德國文化中的森林崇拜現象也恰恰產生于十九世紀初、繁榮于十九世紀中,然后給德國留下了一個強大的傳統。所以這個時間點必定意義重大。而在這個時期,德國歷史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相同時期全面起飛的工業化。換言之,這個時期也是德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化轉變的巨大的轉型期。無論是大規模的結社運動,還是影響深遠的森林崇拜,其產生與繁榮的時間都與德國工業化的節奏同步,這個現象絕非巧合。那么工業化何以給德國社會、德國人帶來了巨變,又帶來了什么樣的變化呢?
德國社會帶著中世紀的生活方式和觀念被歷史裹挾進了十九世紀,進入了現代,進入了工業化的大潮中,前現代的社會形態和心態,與現代化大潮的激烈碰撞,德國產生了劇烈的社會變遷。變遷的一大表現形式,就是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在工業化過程中,人口的大規模流動本來是一種屢見不鮮的現象。但是在德國,人口流動卻帶來一個突出的現象,這就是“無根化”(Entwurzelung)。十九世紀的德國工業化過程中,社會的轉型帶來了人口的大流動,大量的人口,特別是貧困地區和農村人口不得不背井離鄉以尋找生計。
在中世紀的德國社會里,人口的流動性是很低的。多數人一般都是在某個地方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農村里的大量隸農沒有人身自由,沒有得到領主的允許就不能離開領主的領地前往他鄉。工業化的洪流席卷了德意志,貫穿于十九世紀的遷徙大潮把人們拋離熟悉的故鄉,帶向陌生的地方。這個變遷一則帶來了隸農獲得自由的機會,但是也帶來了相當多的負面后果。
對于草根階層而言,“無根化”的后果當然更為嚴重。失去故土的鄉民們,除了不得不面對一個全新的、陌生的、不友好的世界之外,還遭受著社會形態解體帶來的沖擊。在工業化之前的鄉村,人們的生活形態以“戶”為單位,一個“戶”所包括的范圍,除了戶主及其親屬外,還包括生活在這個“戶”里的雇工、使女等人。這些人一方面受著戶主的壓迫,但戶主同時也承擔了給該戶成員提供生存保障的責任。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們,如工匠師傅,一方面作為作坊的統治者居于統治地位,剝削和壓迫作坊里的其他人;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須承擔起對整個作坊的責任,給家庭成員以及學徒、雇工等“下人”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換言之,在中世紀生存狀態下的德國人,盡管生活并不富裕,但是基本的生存還是得到保障的。在這種生存形態中,“下人”們既沒可能也無需為自己的生存操心,一切皆有師傅或戶主做主。而在工業化進程中被“無根化”后的人們流落他鄉,不僅生活在陌生的地方、陌生的環境、陌生的人們中,而且舊有的生活形態不復存在。這樣的人們的心理需求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一種尋求庇護的心理需求日漸強烈。
工業化導致城市化。工業化促進了人口的流動,而城市化則把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聚集在一起。在迅速膨脹的城市里,聯系人們的紐帶不再是血統、家鄉、地域、親屬關系,而是就業,是工作機會,是居住地,如鄰里。一個城市里聚集了大量的人,一個工廠里聚集了眾多的人,這樣一來,物理的空間變得狹小了,但是人們的心理距離卻增大了,人與人變得極度疏遠。而且猛然間,原來的社會關系蕩然無存,人們突然處身在陌生的環境里、陌生的人群中。一種新的心理需求產生了,人們需要建立一個熟人環境,在其中人人互相認識、可以互相幫助和關心。這樣一個新的環境的需求,就給結社奠定了最為堅實的基礎。本來德語“社團”(Verein)一詞派生于動詞“vereinen”,意謂“變為一體,把……聚集在一起”。所以就其根本而言,德國文化中結社運動的“始作俑者”和深層原因主要就是德國社會的這個巨大轉型,結社便承擔了把人們聚集在一起,以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陌生感、創造安全感的重任。在歷史的變遷中,這個傳統不但保留下來,而且還不斷發展。
社會流動性導致“無根化”的現象,而沒有了精神上的根的人們在心理上飽受不安全感的侵擾,因此對于安全感、被庇護的感覺有著特殊的向往,這一點,可以從十九世紀下葉德國社會中對于“共同體”(Gemeinschaft)的神往和對于“社會”(Gesellschaft)的厭惡中看出。一八八七年,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發表了《共同體與社會》一書,提出“共同體”與“社會”的對立,以及消除“社會”、建立“共同體”的設想。所謂“共同體”與“社會”的分水嶺在于,在“社會”中充滿了矛盾和沖突,人生活在矛盾之中,被迫忍受生活的折磨;而在“共同體”中,一切矛盾、沖突都被化解,人與人生活在和諧、自然的關系中。每當社會矛盾激化、尖銳時,“共同體”與“社會”的命題就被提出來,最極端的一次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魏瑪共和國時期。
長久以來,德國歷史給德國人注入了一個特殊的心理需求,即所謂尋求“庇護感”(Geborgenheit),就像是一棵獨立的樹,比較容易被狂風吹倒;而一片樹林就比較能夠給予一棵棵樹木以庇護。個人得到整體的保護,整體又依賴于個體的加入以壯大自己。這樣一個民族心理,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獲得了新的表現形式,社團就是這種新的表現形式之一。
社團的加入和退出是自由的,在社團里,具有相同興趣、相同素質的人,能夠融洽相處、相互容忍、相互幫助,他們聚集在一起,一個沒有沖突的“共同體”就被構建出來了。在這樣一個組織中,人們不再或不太感到隔閡,身處異鄉、身處陌生人之中的不安全感消退了,即“社會”的矛盾、沖突被克服了,而“共同體”所許諾的和諧、統一似乎實現了。
十九世紀中葉,德國工業化的高潮期間,德國社會中的結社大潮也洶涌澎湃。這些社團中,數量最多、影響最大的當數各種歌詠協會。本來就酷愛歌唱的德意志人,在特殊的心理訴求的驅使下,加入歌詠協會,大家同聲高唱同一首歌,把心里的壓抑、苦悶、恐懼、失望趕出心窩,每歌唱一次,似乎就經歷一次“宣泄”,歌者的出身、信仰、地域、方言、職業似乎都不重要了,人們獲得一種被庇護的感覺。而在其他社團中,人們還的確可以得到幫助并施人以幫助。此外,在這個結社過程中,一大批“結社狂”也應運而生;而且只要有社團,就有結社狂們的身影。他們熱衷于結社、管理社團,不但把社團管理好,而且也鍛煉了管理才能,增強了社會的組織性。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三個德國人一個社團”的諺語產生了,結社也豐富了德國文化,留下了一個強大的傳統。
文化自有一種內在驅力(Eigendynamik),一種文化現象一旦形成,就會千方百計存在下去。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其存在的條件仍舊存在,那么這種文化現象就會長久地生存下去。如今,德國的社團文化依然強大,但是也應時代的需要產生了一些相應的變化。自十九世紀中期社團在德國大發展以來,社團便成為德國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德國的社團卻也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甚至走過了一條并不平坦的發展道路。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中,法蘭克福議會制定的憲法里規定,民眾有結社的權利。但是此前和此后,德國人的結社都受到政府的嚴密監督和控制。革命失敗后,政治性的社團遭受了滅頂之災,不問政治的社團的生存處境還比較好,政治性的社團則生存不易。納粹上臺后,對各種社團進行了更嚴格的控制,猶太人的社團、工人社團、政府不信任的社團都被禁止。除了官方組織的社團,如“希特勒青年團”一類的納粹組織才有生存的空間,社團生活經歷了倒退,各種社團的人數都在不斷下降,能夠持平已然不易,遑論社團的發展。唯一例外是德國的“小花園主協會”,其成員在第三帝國期間也一直不斷在增長。
“二戰”結束后,德國的社團經歷了多次轉向。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德國西部的社團經歷了大發展的黃金時代,其特點是各種娛樂性的、以物質消費為導向的社團獲得了長足進展。到了七十年代,德國的社團又經歷了一次變化,各種公民自發組織、自助組織大量涌現,此外還有大量的各種婦女組織、反核組織、同性戀組織、支持第三世界的組織等。而一旦這些組織能夠存在下去,往往就轉變為社團,例如“無國界醫生”、綠色和平組織等。這樣的社團與傳統的社團有所不同,其宗旨、組織形式、成員等都有別于傳統社團,已經鮮有傳統社團中那種“結社癖”人士。在今天,傳統的社團,如歌詠協會、射擊協會、遠足協會、讀書會等,面臨著成員不足的危機;而新型的社團則人丁興旺,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