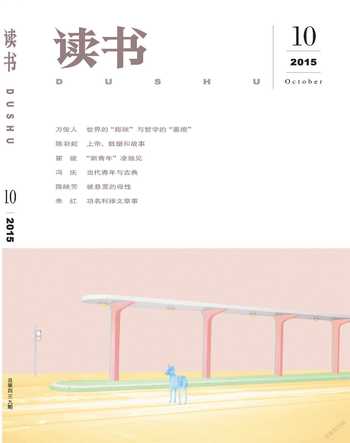法國的“小說證史”:從對抗走向和解
學界通常認為英美在近代發展出了一套妥協的政治文化,而法國大革命開創的左右對抗的激進政治文化則延續至今。的確,在十九世紀很長的時間內,大革命遠沒有窮盡其動力,舊制度復辟的危險隨時存在,大革命與舊制度時常劍拔弩張、兵戎相見。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在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結束革命動蕩,使現代民主共和政體扎下根來,是自熱月黨人到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歷屆政府和明智之士追求的目標。為此,需要彌補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斷裂,把法蘭西民族兩種對立的歷史拼接起來。這就要求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實現和解,在極端保王黨人與波拿巴主義者之間實現和解,在封建貴族與資產階級之間實現和解,在右翼與左翼之間實現和解,在舊制度的法國與大革命的法國之間實現和解。在十九世紀,各種和解方案爭相出臺,有的失敗,有的成功,有的毀譽參半,愛情、婦女、宗教、歷史充當了和解的說客。總之,從拿破侖簽訂《教務專約》,到路易十八接受《一八一四年憲章》,到七月王朝走中庸派路線,再到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建立,妥協精神經歷了一個由弱到強的變化過程,和解成為時代的主旋律。法國著名歷史學家莫娜·奧祖夫的《小說證史》,選取法國十九世紀九位作家的十三篇小說,從斯塔爾夫人的《黛爾菲娜》開始,以阿納托爾·法郎士的《榆蔭道》和《柳條籃》結束,中間邀請巴爾扎克、司湯達、喬治·桑、雨果、巴爾貝·多爾維利和左拉的作品為伴,透過一個個典型人物闡釋了舊制度與大革命在十九世紀經由沖突走向和解的過程。
巴爾扎克的《老姑娘》通過兩個既互相敵視又極其相似的人物,講述了復辟時期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斗爭。德·瓦盧瓦騎士代表傳統的一方,他參加過舒昂黨叛亂,穿著過渡時期的裝束,懷揣著對王室的紀念,像是舊制度的活化石。杜·布斯基耶代表革新的一方,他穿著革命時期的服裝,平庸粗魯,唯利是圖。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競爭就體現在這兩個人物對富甲一方的老姑娘的爭奪上。騎士由于深受貴族的輕薄所害,在梳洗打扮上耽擱了時間,讓杜·布斯基耶搶先幾分鐘向老姑娘求了婚,大革命戰勝了舊制度。但杜·布斯基耶獲勝之后不忘和解。他與老姑娘結婚后,把科爾蒙府邸修繕一新,推動城市的現代化,讓“宣誓派教士”和“倔強派教士”握手言和,把科爾蒙的沙龍變成貴族和資產階級聚集的場所,邀請各界名流各抒己見。
在巴爾扎克的另一篇小說《古物陳列室》中,新舊法國的沖突再次出現。德·埃斯格里尼翁老侯爵的兒子維克蒂尼安生性放蕩,他在巴黎花天酒地,偽造票據騙取金錢,最終面臨牢獄之災。是否應該對維克蒂尼安進行審判呢?這時出現了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貴族凌駕于法律之上,為了名門望族的榮譽,甚至是國王本人的榮譽,要求宣告維克蒂尼安無罪;另一種觀點認為訴訟牽涉的不是貴族階層的利益,而是法國本身的利益,應該遵循《一八一四年憲章》的精神,保證公民平等,消除等級特權。最終特權一派獲勝,維克蒂尼安在免予起訴的判決后重歸自由。但是他為了償還賬務,被迫與門第低的人結婚,這在另一種意義上也實現了貴族與資產階級的和解。
《悲慘世界》中的馬呂斯身上體現了法蘭西民族兩種不同版本歷史的沖突:他的外祖父是極端保王黨人,父親當過拿破侖的上校。外祖父把女婿當成強盜,剝奪了他對馬呂斯的撫養權。于是,馬呂斯從小跟著外祖父出入于極端保王黨人T夫人的沙龍,受到的是極端保王黨人的思想熏陶。直到父親病死后,他才知道父親曾經深深地愛著他,之所以把他的教育交給外祖父是因為受了要挾,因此他理解了父親的慷慨和英勇。于是,他貪婪地去了解父親跟隨拿破侖大軍馳騁歐洲的足跡,對拿破侖充滿了敬仰,皈依了波拿巴主義者,后來浸染了共和主義思想,投身到街壘戰中。但他不愿意接受這場革命,不由自主地擁護七月王朝,他想中止革命,停下來歇歇腳,放棄政治沖突,追求個人幸福。讓馬呂斯困惑的是,誰才是這自相矛盾的法蘭西民族歷史的繼承人呢?法蘭西民族的這兩種傳統是否能拼接到一起呢?《悲慘世界》的結尾展現了這種愿景:外祖父接受了民主時代,馬呂斯依照舊制度的儀式結婚,街壘戰老戰士遵守資產階級秩序。這個結尾恰恰反映了七月王朝的中庸之道。這個政體是半途而廢的革命的產物,是君主制與資產階級的妥協。它想徹底埋葬大革命,在歷史和未來之間尋求連接點,把法國歷史上的兩種傳統拼接到一起。
在法朗士的《榆蔭道》和《柳條籃》里,沒有確定的空間,沒有顯眼的人物,沒有矚目的事件,劇中的角色像是一群人偶,他們沒有靈魂,命運沒有交織,時刻都在獨白。奧祖夫認為,沉默匿名的外省和平庸無聊的人物正是為了凸顯法朗士對十九世紀法國社會的觀察,這就是“不變”:大革命與舊制度之間有連續性,甚至是等同的。一八七六年的軍事法則是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時期的法令匯編。在共和國的軍隊里,對上級動粗的士兵要處以死刑,這是源自舊制度時期軍官與士兵不出自同一個門第的觀念。共和黨人接受了舊制度下不平等的觀念,教權主義者坦誠受到大革命的影響。因此,將共和體制穩定下來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并不是一項大刀闊斧的革新,相反,這是一個平庸寬厚、政績平平、軟弱無力的共和國。正是這樣一個共和國終結了舊制度和大革命的百年戰爭,完成了法蘭西兩部完全對立的民族歷史的對接。
總的說來,和解的結果利于資產階級,貴族社會的原則被逐漸拋棄。金錢成為溝通不同等級的橋梁,成為社會平等的基礎。金錢能征服最倔強的群體,《呂西安·婁萬》中的德·桑萊阿爾侯爵一得知燕麥漲價了,就放棄考慮君主制的原則。《古物陳列室》中的維克蒂尼安、《貝婭特麗克絲》中的馬克西姆·德·特拉耶和《悲慘世界》中的馬呂斯均與門第低的資產階級家庭聯姻。金錢能讓銀行家與國王平起平坐,能讓證券投機商和名門望族歡聚一堂。
但是奧祖夫還沒有來得及花費多少筆墨頌揚資產階級的勝利,就筆鋒一轉,批判起資產階級社會的拜金、庸俗、卑劣和無聊。她借用小說中那些迷戀十八世紀生活的老貴族的眼光指出,要實現和解,人們必須放下成為英雄的夢想,放棄對舊制度舉止風尚的癖好,接受這個粗俗的時代,就像呂西安·婁萬一樣,為了融入七月王朝那個社會,他必須學會偽裝,做到口是心非,經過嚴格的“入會考驗”,把自己歷練成一個“無賴”。
然而,正是這種現實的力量、這種實用主義精神讓人們放棄空洞的自然權利,忘記僵硬的等級界限,接受靈活的處事態度。最終,復辟被避免了,革命被化解了,糾纏了整個十九世紀的斗爭緩和下來,共和民主制度終于找到了可以安全停泊的港灣。盡管這個體制并不完美,但它堅固得足以抵制后來德雷福斯事件帶來的震蕩,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沖擊。如果說現代民主政治的確立離不開妥協的話,法國并不是一個例外。十九世紀法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善于對抗的民族只有學會協商和妥協,才能真正地從革命走向民主。
通過小說淋漓盡致地呈現舊制度與大革命從對抗走向和解的過程,精辟犀利地詮釋后革命時代的法國政治文化,這種研究方法正是奧祖夫近些年來倡導和實踐的小說證史。在中國學界,小說證史屬于文史互證的一種類別,具有深厚的學術淵源。奧祖夫的小說證史與中國學界的小說證史有不少相似之處,兩者都強調小說和歷史的相通性,都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小說家能比歷史學家更好地呈現和理解歷史。在 《小說證史》的導論中,奧祖夫對十九世紀法國小說的功用進行了深刻的論述,她認為這一時期的小說具有雙重特性,它既與舊法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又擔負著解釋新法國的任務,因此可以成為協調新與舊的一個場所,適宜于描寫新舊混合的現象。小說更易展現人物心靈的奧秘,小說在講述典型人物和故事的過程中更能呈現真實的社會,小說的敘述能快能慢,能進能退,能更好地把人物和家族置于歷史的中軸線上。
與中國學者不同的是,奧祖夫認為,小說不僅呈現歷史,而且親自促成了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和解。小說反對固定不變,不相信人類幸福會永存下去,也不相信烏托邦式的公社生活。它總是把故事設置在帶有濃郁鄉土印記的地方,使家族世襲根植到歷史之中,賦予小說主人公一種頑強的個性,將他們態度曖昧甚至表里不一的真實一面展現出來。這一方面使讀者加強了對真實世界的體驗,明白了事實與希望之間存有鴻溝,從而放棄對烏托邦的幻想,卸下改造靈魂的自負。另一方面,還使讀者認識到傳統沒有滅絕,過去仍然對現在施加淫威,促使人們尋找過去與現在的和解之路。因此可以說,十九世紀法國的小說熄滅了激進革命的火焰,識破了烏托邦的虛幻,培育了后革命時代溫順恭良的國民精神,促成了具有和解精神的政治文化的形成。
(《小說證史:介于舊制度與大革命之間的十九世紀》,莫娜·奧祖夫著,周立紅、焦靜姝譯,商務印書館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