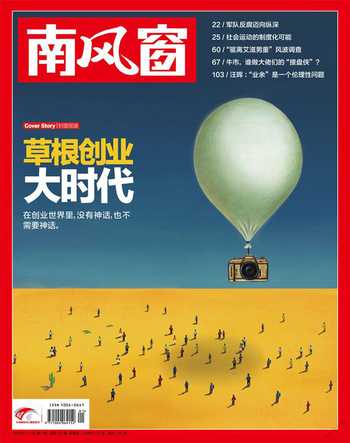社會運動的制度化可能
唐昊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筆者認為,如何將社會運動納入法治化的制度軌道,是未來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課題。
社會運動經常被和集體行動、政治革命相提并論,三者同是作為制度外的集體行為,外在表現相當類似,以至于當某種集體行為突然來臨時,對政治家來說,最困難的就在于判斷這種集體行為的性質,以及相應對措。當然,其實還有更難的—在事情發生前就能夠判斷:何時發生和發生什么?
社會運動需要一定的制度化為前提。在相對開放的社會,人們又可通過多種途徑參與政治和表達理念,利益代表機制似乎都比社會運動更加精準也更加有效。而在相對封閉的社會里,大眾的訴求缺乏合法的表達渠道,一旦發生抗議和反對,就容易走向極端。“只有在政治機會不完全封閉與不完全開放的條件下,社會運動才有機會持續發展。”
眾所周知,在中國社會,底層的人們常常不知道通過什么方式才能表達和保護自身的利益。于是當事情壓迫到眼前時,通常選擇最直接的抗爭方式。據統計,1993 年我國發生群體性事件0.87萬起,2005 年上升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萬起,至于近年來群體性事件仍保持著多發態勢。
底層民眾的訴求只是具體利益的抗爭,但其數量、規模及激烈程度常常令人震撼。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在目前的政治經濟結構很難阻止這些群體性事件的發生,那么退而求其次,至少要知道該如何應對。
雖然關于社會運動的理論很多,但是那些近距離接觸或參與過社會運動的學者都很清楚:對社會運動的現場,很難用社會學理論去分析,很多時候來自心理學的解釋倒是更加靠譜一些。這是因為在現場,參與的因素太多且相互影響,沒有辦法被歸納為幾個主要變量來進行分析。沿用傳統的社會科學的分析路徑往往難以抵達真實的原因。至于總結運動規律,更是科學理論的奢侈品。
這種時候,對人與人之間、集團與集團之間互動的微妙情形進行把握,就更像是一門藝術,而不是科學。沒有固定的分析框架的情況下,學者更需學會體會他人。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場。生活是如此豐富,現場感對于集體行動來說無比重要。現場所發生的集體心理互動,往往能夠決定社會運動的即時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政治革命退潮,社會運動開始興起。與政治革命相同的是,社會運動也是一種集體行動。與政治革命不同的是,社會運動所追求的社會改造目標,是在承認現有政府合法性的前提下發生的。在激烈性和對抗性上大大低于政治革命,因此成為政治革命最好的替代品。這個時期社會運動的數量增多,但烈度明顯小于之前的無產階級革命,且對社會制度的完善起到了正面作用。在這個意義上,社會運動增多反而成了政治穩定的標志。60年代的五月風暴,70年代的民權運動,以及數年前的占領華爾街,這些運動在二戰前完全可以成為一場革命,但在現代法治框架下,卻和平收場,并成為改造僵化的右翼政治的動力。
在任何社會中,只要社會發展與政治發展不同步,就有可能發生社會運動。執政者如果應對得法,大多數社會運動是不會演變成為革命的—實際上,很少有社會運動一開始就提出顛覆性的革命目標。相反,很多當代社會運動最后被納入制度化的軌道,成為制度自我更新的動力。多數社會改造團體也是在社會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并將短期運動化為長期目標,從而收到治理的效果。
但在兩種情況下,社會運動會脫離原來的溫和目標而走向極端,這兩種情況都與現場處置有關。一是雙方或一方試圖用速戰速決的處置方式,瞬間激化矛盾,在雙方心理都高度緊張的情況下擦槍走火。當運動中最為關鍵的“沉默的大多數”走上街頭,事情就無可挽回。南越僧侶自焚、突尼斯的所謂“茉莉花革命”都屬此列,簡單粗暴的處置方式最終導致不可挽回的結果。二是遲遲不處置,則無法阻止持續的負面情緒相互激蕩,運動因此不斷升級,方向也逐漸趨向不妥協的原教旨主義,最終導致來自雙方的極端主義正面對決。俄國十月革命、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伊朗霍梅尼革命中,都有一個由情緒互動導致運動升級的過程。
在十月革命之前,針對饑餓、不公的游行示威不斷。即使二月革命發生,沙皇之后的每個政權都面對著貴族、資本家、士兵、工人、農奴、孟什維克或布爾什維克的多元反對力量,每一個政權都在第一時間對群眾開槍,導致革命一波接一波地發生,且越來越激進,每個階層和其他階層的妥協都已不可能。直到最左翼的布爾什維克上臺,很多俄國人還覺得他們只是眼花繚亂的政權更替中的一個過場而已,沒想到這一次已是革命的終結。
霍梅尼革命最初也是當時發展中國家中司空見慣的抗議示威。民主派、宗教極端主義者、利益受損的中產階級,都對巴列維國王不滿,他們發起了要求改革的抗議活動。巴列維國王強硬拒絕改革,卻也同時拒絕對人民開槍。在連續多日未采取有效措施的情況下,眾叛親離,巴列維國王只能流亡海外。但伊朗在霍梅尼回國后卻并沒有建立現代政權,反而建立了伊斯蘭共和國,經濟發展等各項指標就此衰落。
不止一個歷史學者曾經設想過,法國大革命其實可以避免、十月革命在俄歷二月就應完結、霍梅尼革命原本不會發生。但現場決定了一切。那些無法預期的心理激蕩使得群眾和執政者都難以做出理性的抉擇。在現場,政府如何回應是最重要的,但也是最容易出問題的。最近這一輪阿拉伯“茉莉花革命”發生時,有些政府連催淚彈都沒有,直接動用實彈,一開始就違反了社會運動應對法則。此外,和當代社會運動高度依賴集體理性不同,早期社會運動更加訴諸集體非理性,因此謠言往往影響重大。對于這一點的處置,保證信息流通和政府公信力是非常重要的。但往往政府在信息管控的同時,輸掉了最重要的公信力基礎,使雙方心理上的接近變得不可能。
在認知社會運動時,需要將社會運動放在制度變遷的動態過程中看待。社會運動并不等同于游行示威,也包括宣傳、行為藝術等面向社會的倡導行為,在社會運動內部也有不同的訴求分級和行動分級。只要將社會運動的行動等級保持在非暴力的水平以下,基本上可以控制其負面影響。進一步的對策可以將其納入法治化的制度軌道,成為常態政治表達,甚至可以發揮其在政治發展過程中的積極作用。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更有效、積極和徹底的應對來自三個層面:法治、共識和組織。
法治框架的建設是社會運動制度化的基礎。公民意識既是教育的結果,同時也是在法治建設的實踐中磨練出來的。西方國家建立的行政與戰略技術兩個層面規范化的操作流程,對騷亂事件在內的各類自然和人為的危機事件建立管理制度,建立廣泛的社會對話協商機制,迅速回應,直接談判。
但法律條文只是維持秩序和社會互信的最低標準而不是唯一標準。集體認同和集體共識的建構是社會運動最核心的任務。這種認同不但要求社會本身有著認同和共識,也鼓勵政府和社會一起發現共同的規則、信仰和利益交互點,而非總是唱反調。
此外,依托于一定的社會網絡和組織,而不是不確定的個體,才能形成社會運動和形成對社會運動的應對。組織將有效地過濾掉群眾運動中非理性的因素。如果社會組織化程度不足,那么個體與個體之間缺乏信任,行為失控的可能性就大增。歐洲的社會運動行為方式的溫和性,和中東的伊斯蘭運動形成鮮明對比。因此,發展社會組織是既鼓勵社會運動良性發展,同時又削減其破壞性的有力工具。
從參與者的角度來看,無論社會組織發達與否,集體行動都可以發生,但集體行動的結果,卻是與社會的組織化程度分不開的。因為就像業主維權的案例顯示的,每個集體行動中,都會有3種人,積極參與者、條件合作者和觀望自利者,他們對集體行動的投入程度是不一樣的。從政府的角度看,如何找到運動的中心并以談判的方式維系其理性,是重要的。而只要政府的應對能夠守住底線(避免大規模流血等),大多數人就還是“沉默的大多數”,在這種情況下,參與集體行動的人會越來越少,等待集體行動出現結果的人會越來越多,集體行動就在觀望自利中走向流散。
當然,上述做法也只是技術上的控制,如果耽迷于技術管控,而不去解決社會運動真實的原因,那么政府就只能阻止社會運動,而無法化解社會運動。不斷積累的社會動能遲早會超出技術層面所能掌控的范疇,到時對政治體系的危害更加巨大。
社會運動參與者其實是政府潛在的合作者,只要秉持這個前提,對社會運動的應對就不會離譜到哪里去。對執政者來說,最好的處置并非無條件地接受運動目標,而是對社會運動目標、內容和過程的整合,即推動運動“制度化”。這是超出現場處置的純熟的制度調整與社會壓力共同作用才能取得的效果。其結果是使社會運動不再是某種過渡性的、異常的現象,而是被整合成為常態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社會運動自有其制度化的基礎條件。實際上,社會運動是和政黨、利益集團類似的政治參與形式。只不過,政黨和利益集團的組織性更強,其所代表的人群更加明確。而社會運動所代表的人群也許更加多元。回想歷史上政黨和利益集團也曾被視為政治不穩定因素,但最終都被納入制度化的軌道而成為常態參政機制。
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梅耶認為,社會運動制度化包括三個主要組成部分:常規化(routinization)—挑戰者和當權者都有共同的“劇本”(script)可遵守,能夠辨識熟知的行動模式以及潛在的危險變化;包容及邊緣化—愿意遵守常規的挑戰者可以獲得在主流機構進行政治交換的渠道,反之則不然;吸納(cooptation)—挑戰者將通過不破壞常規政治的方式來實現其訴求及策略。而無論是常規化、邊緣化還是吸納,社會運動的制度化始終強調兩點:首先是組織或制度自身從非正式到正式、從不健全到健全的發展過程;其次是組織或群體的行為、生活方式被社會普遍接受,成為制度的一部分。有時,當社會運動達到其目標后,就變成了體制的一部分,直至成為新的社會運動反對的對象。
在付出了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期持續政治革命的巨大代價后,西方國家在二戰之后終于學會了對于社會運動的把控。政府所要做的并不是承諾馬上解決問題(這很少有可能),而是一方面維護既有的法治框架,另一方面回應其參政訴求,使自己也成為社會運動的一部分。這樣做幾乎可以化解大部分社會訴求。當然,你也可以說政府是通過規范集體行為和慢慢解決問題的方式拖垮或收編一個社會運動,但這樣確實有效。
歷史是一個充滿了偶然性的存在,但對每一個利益集團來說,每一種行為方式都有著必然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