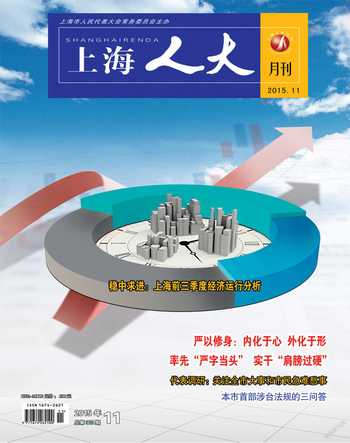理念與制度
丁冬
從個體自治到國家干預,反家庭暴力立法在世界范圍的逐步推開是伴隨著各界對家庭暴力性質的認識轉變而展開的。傳統法學意義上的家庭是一個私人生活的共同體,更多注重個體的自愿結合,以及“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隱私保護。在此種視域里,家庭暴力更多地被理解為一種家庭內部事務或矛盾的范疇。而隨著女權主義運動的推進和人權研究的深入,家庭暴力性質的界定從家庭內部事務范疇變為社會公共問題的范疇。由此引發了立法規制的呼吁。《聯合國反對家庭暴力的示范立法框架》將反家暴視為推進人權和人類基本自由的重要途徑和方法。
中國反家暴立法的呼吁和研究歷時多年,期間還形成了反家暴立法的專家建議稿。2015年8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初次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并公開征求意見。總共三十五條的草案全文,總令人有意猶未盡的感覺。2015年新修訂的立法法明確規定“法律規范應當明確、具體,具有針對性和可執行性”。反家暴立法應在這些方面著更多筆墨,把握和處理好立法的粗疏與細密,讓法律更有生命力。筆者認為,反家暴立法應重點厘清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立法理念上的“粗與細”。“立法宜粗不宜細”是特定歷史背景下立法策略的選擇。長期以來,我國立法實踐中存在著一部法律出臺后,需要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以及大量的規范性文件支撐細化的現象。一部法律所衍生的法律規范疊床架屋,體系冗雜,不僅有存在法律沖突的可能性,也不利于知法、守法、用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曾指出,立法過程中要盡量減少配套性法規、規章的數量,增強法條的可操作性。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立法資源、技術更為成熟的當下,立法的精細化、精準化應該更加被重視。縱觀此次反家暴立法草案,在家庭暴力的界定、家庭成員的范圍、反家暴的責任部門、人身保護令的申請與適用、家庭暴力的法律責任等條款的設計上,尚顯粗疏。比如,對于家庭暴力的界定,草案僅以列舉的方式規定了身體型家庭暴力行為,對于生活中存在的性暴力、精神型暴力等并未涉及。草案中對于相關部門在反家暴工作中的角色定位和具體職責也沒有作出比較清晰的界定。對于新設立的人身保護令的申請主體、程序在可操作性方面也有所欠缺。這些問題都應該通過立法的細化進行完善。
第二,立法與其他相關法律法規的配套銜接。聯合國在反家暴法示范立法框架中指出“……制定全面的家庭暴力法,該法應與刑法和民法中的相關條款組成一個整體,而不只是對現有刑法和民法的旁支末節的修補。”一個運轉良好的法律體系,應當是各部門法律相互銜接、配套的。反家暴立法參考美國等國家的民事保護令制度,新設了人身保護令制度,并將其作為一項單獨的訴訟程序。這種創設性的制度有助于保護家庭成員免受家庭暴力的侵害。但該制度與民事訴訟法的配套銜接問題應該加以重視。一旦將其作為一項獨立的訴訟程序,則在人身保護令的申請程序、條件、審理方式、執行與解除等方面應結合司法實踐在法條措辭、具體制度設計上作更為精準的規定。

第三,立法應將法律實施問題納入考量視野。黃宗智教授曾指出,法律的表達與實踐之間的背離是中國法律實施過程中的一個大的問題。要努力做到法律的表達與實踐的一致,既需要法律本身的科學合理,也需要有良好的法律實施保障機制。反家暴立法草案中對于法律責任條款的設定顯得過于單薄,在法律實施過程中欠缺基本的可操作性。這一點需要在立法中予以重點考慮和解決。
反家暴立法的制定是我國人權保障事業推進的一項重要舉措。反家暴法的出臺具有國家反對家庭暴力的宣示性意義。但是反家暴法不應僅僅是宣示性的,更應該是能夠切實有效發揮立法保障家庭成員人身安全和精神安寧作用的可執行的法律。這需要改變過去立法宜粗不宜細的傳統立法理念,從具體制度機制層面優化法條的設計,而不能將此太多地寄望于配套性法律法規體系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