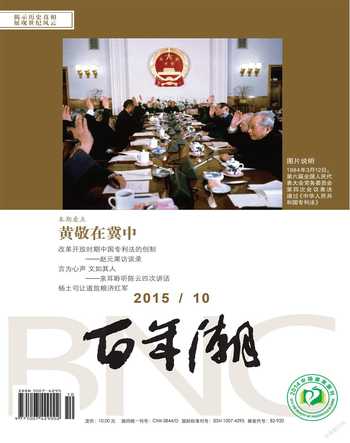“死”字旗所昭示的
楊勝群
抗戰文物不計其數,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都感動著人。四川一家博物館收藏的一面“死”字旗,是最感動人者之一。1937年9月,淞滬抗戰正酣,在大西南的四川省,20萬川軍請纓馳援,萬里赴戎機。北川縣曲山鎮王建堂等100名北川子弟就在這個行列里。出征那天,白發蒼蒼的父親給王建堂和他的伙伴送來一面用白布制成的大旗,上面書寫著一個大大的“死”字,旁邊還寫著一行小字,“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分”,“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后裹身”。
古來征戰幾人回。20萬川軍“百戰死”者眾,“十年歸”者寡,但這面“死”字旗最終竟回到了故土,靜靜地躺在博物館里向后人昭示著什么。
“死”字旗,讓人真正知道了什么叫“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19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失敗后,與西方侵略者簽訂了一系列割地賠款的條約。先覺者意識到了落后挨打的民族危機,呼吁國人睜眼看世界,但統治者們看到的卻是大清國的所謂“同治中興”,一直到甲午戰爭爆發前,還在做盛世美夢。中日甲午戰爭,東方大國竟然敗給了“東方小國”,這讓許多人驚醒了,一些人喊出了“救亡”的口號。統治者顯然也看到了問題,但當然不會承認是腐朽的社會制度造成的,他們所能想到的解決辦法,則如同要用幾根木柱子去撐起搖搖欲墜的大廈暫時不倒。好在中國只是丟了臺灣,還沒有到最危險的時候。直到“東方小國”在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驅使百萬虎狼之師,再次席卷他們覬覦已久的這片東方最大的陸地,要讓這片土地上的主人亡國滅種,中國人才全體意識到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才“被迫發出最后的吼聲”!這個“死”字,就是中華民族發出的最后的吼聲!
“死”字旗,讓人真正知道了什么叫“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在手里的武器遠不如人的情況下,中國人只能用血肉之軀構筑自己的防線。淞滬之戰,中國軍隊傷亡25萬人,三個月內幾乎平均每天損失一個師。臺兒莊戰役殲敵11000人,當然是大捷,但中國軍隊傷亡7500人,其中滇軍的一個營500人犧牲了499人。真正是一寸河山一寸血!中國軍人要么“我死國存”,要么“我生國亡”,在打出“死”字旗后,他們對生與死的選擇就不那么難了!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楊靖宇,只要放下手中的槍走出林海雪原就可以生,但他選擇了用樹皮、棉絮果腹,戰至生命最后一息。他的八個女兵,只要后退幾步就可以生,但她們選擇了攜手走進冰冷的烏斯渾河……
“死”字旗,讓人真正知道了什么叫“不愿做奴隸的人們”,什么叫“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這里的奴隸,是亡國奴。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站到“死”字旗下的不只是中國軍人,還有不愿做亡國奴萬眾一心同侵略者干的普通老百姓。日軍全面侵華開始后,即迅速占領中國沿海港口,切斷了中國抗戰物資的海上運輸通道。漢族、回族、傣族、佤族、傈僳族、阿昌族等26個民族的幾十萬婦孺老幼,在九個月內,硬是用肩挑手扛,拼命修成了長達1000多公里的滇緬公路,為中國抗戰打開了一條新的生命線。抗戰后期,為滿足盟軍對日戰略轟炸的需要, 29個縣的幾十萬民工在四個月內,硬是用鋤頭和石磙,拼命在成都地區修成了四個機場及配套設施,被美國人稱之為中國“2000年前修筑萬里長城以來空前的一次”民工工程。
“死”字旗,昭示著中國一段血與火的歷史,昭示著中華民族一種生生不息的精神。
(作者是全國政協常委、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