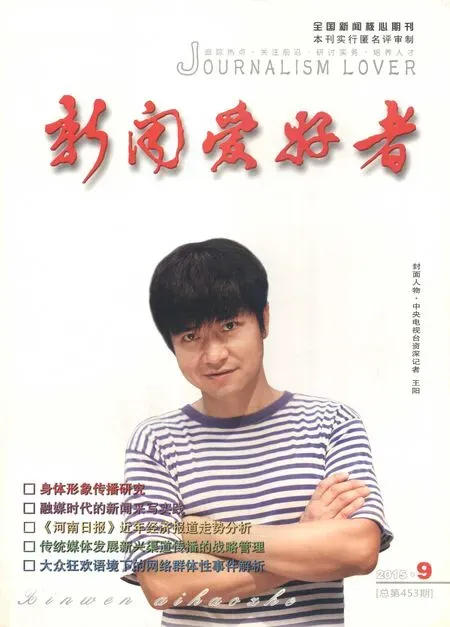延安時期《邊區群眾報》女性新聞的社會功能
□田頌云
延安時期《邊區群眾報》女性新聞的社會功能
□田頌云
延安時期《邊區群眾報》的女性新聞,具有時代特色,也有獨特的社會功能。它動員婦女參加經濟建設,促進婦女參與教育發展;婦女典型人物具有示范作用,它激發婦女參政議政熱情,倡導女性婚姻自主,反對舊思想和封建迷信。它宣傳報道邊區政府的婦女政策,建構了婦女的主體性,從而推動了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婦女發展。
《邊區群眾報》;女性新聞;發展
延安時期《邊區群眾報》創刊于1940年春,毛澤東親自題寫報名,由周文主持的大眾讀物社創辦,是主要面向基層干部和群眾的黨報。這份報紙在延安時期的新聞宣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邊區群眾報》刊登了一些女性新聞,在促進女性發展上起了很大作用。作為陜甘寧邊區的黨報,它與政治結合緊密,有許多內容與女性相關,對共產黨解放婦女的相關政策進行宣傳,促進了當時女性的發展。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與女性有關的新聞,因為其時效性不強、故事化的敘事等,與現在對女性新聞報道有很大區別。而只要是和女性相關、涉及女性的內容,都是本文研究的對象。
作為黨和政府的耳目喉舌,邊區政府非常重視《邊區群眾報》社會功能的發揮,也提倡群眾要利用報紙來提升自己。1946年,在《邊區群眾報》創辦6周年時,3月31日刊登毛澤東的題詞“希望群眾多利用報紙,推動工作,學習文化”。這一期的社論《你是群眾報的主人,你要利用它》指出,“群眾報就是辦給群眾看的”“利用報紙,恐怕是推進工作的重要辦法之一”。這里的“你”就是指群眾,也包括婦女。《邊區群眾報》的女性新聞話語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形成的,有時代特色,也有獨特的社會功能。
一、動員婦女參加經濟建設
女性應該自力更生,用自己的雙手去勞動。在當時的中國農村,女性參加勞動也是在維護自己的經濟權益,經濟地位的提高也是其家庭地位提高的基礎。1940年2月,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婦委的一封信》中指出,“邊區婦女工作之少成績,主要是沒有注意經濟方面”,而婦女的偉大作用“第一在經濟方面”,“提高婦女在經濟、生產上的作用,這是能取得男子同情的,這是與男子利益不沖突的。從這里出發,引導到政治上、文化上的活動,男子們也就可以逐漸同意了”[1]。因此,邊區政府在開展婦女工作時,開始轉向動員婦女參加勞動生產,參與經濟活動,從解決經濟問題出發來解決其他問題。
到了1943年,中央發出指示:“在日益接近勝利而又艱苦的各根據地,戰斗、生產、教育是當前的三大任務,而廣大的農村婦女能夠努力參加生產,與壯丁上前線同樣是光榮的任務。而提高婦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達到解放的道路,亦須從經濟豐裕和經濟獨立入手。多生產,多積蓄,婦女及其家庭生活過得好,這不僅對根據地的經濟建設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依此物質條件,她們也就能掙脫封建的壓迫了,這就是在整個群眾中廣大農村婦女的特殊利益所在,也就是抗日根據地婦女工作的新方向。”[2]這個決定確立了婦女運動中以經濟建設為重。
上述內容在報紙上也有所體現,婦女與經濟的報道都是在維護婦女的經濟權益。經濟決定話語權,婦女對家庭的經濟貢獻大了,經濟地位提高,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自然也會提高。婦女參加勞動生產的內容多樣,紡織、喂豬、鋤草、采摘、割麥、拾麥穗等,幾乎涵蓋了家里和地里的所有勞動,體現了婦女的勤勞及自身價值。這些勞動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婦女紡織,它是邊區政府大力提倡并在邊區形成一定規模的生產勞動。1942年,陜甘寧邊區婦聯到延安柳林二鄉蹲點,調查婦女參加紡織勞動,發現這是符合婦女實際的形式,因此,就進行推廣,并在報紙上宣傳報道。1943年12月9日的《劉老婆說明年再組織六十個婦女紡線》、1947年2月26日的《婦女們:多紡線,多織布!全邊區做到穿衣自給》等,從時間上我們可以看到婦女紡織的報道年年都有,是受到重視的。在這個過程中,還涌現了一批婦女紡織模范典型,并有專題報道。
另兩篇新聞為1947年2月8日的《我要土地?我要土地?婦女們的勁可大》,以及1947年2月22日的通訊《有了骨頭好長肉婦女翻身要爭地》,這兩篇文章鮮明地提出婦女爭取土地權的問題。在當時的邊區農村,婦女的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都很低。土地權益的提出,能提高她們的地位,也能讓人們重視對包括土地權益在內的婦女權益的保護。這兩篇報道,將土地和婦女的勞動以及翻身解放聯系起來,并將經濟層面的解放和政治層面的解放相結合。
二、促進婦女參與教育發展
作為根據地婦女工作的三大任務之一,邊區政府十分重視教育工作,并根據婦女的實際情況,開展了靈活多樣的教育活動,主要是社會教育,而非正規的學校教育。1938年《三個半月來冬學運動的總結(上)》中指出:“邊區女子因封建習氣濃厚,婦女教育特別落后,在冬學運動中卻給了婦女們一個很大的刺激。進學的數目雖然還是那么微小,但也總算開始建立了一個基礎。進學的女子約占學員總數的七分之一,并且學習常常站在男子的前頭。如淳耀縣竟有九十多個青年婦女參加冬學,她們的進步比男子還快,有的能識三四百字以上,能說出飛機有幾種,毒氣有幾種,并能答復一些簡單的抗日問題。”[3]
在對婦女與教育的新聞中,冬學的報道是最多的。如1944年11月5日的《邊區群眾報》,這一期主要和冬學有關。有兩篇是婦女冬學,《真武洞女小按群眾的生產成立學習的組織》報道的是真武洞女小根據群眾的具體情況和婦女的情況來調整識字的內容和時間。另一篇是《辦婦女冬學要注意什么?》:

《邊區群眾報》
第一,有的地方可以辦婦女冬學,可是,婦女上學不但要本人愿意,還要勸說她的公婆丈夫也愿意。第二,紡織是今年婦女冬天的中心工作。所以,婦女上冬學,一定要和紡織結合起來,甚至不必另外成立什么婦女冬學,就在紡織組內進行識字讀報。第三,婦女們現在最需要的,是接生養娃娃的知識。所以,綏德提出,婦女冬學,教接生為主,這是很好的。
這篇簡短的報道闡釋了婦女冬學工作中應該注意的三個問題,這些問題是對婦女冬學有實際影響的因素,其分析和闡釋對婦女的冬學教育具有指導意義。
1945年5月13日的《利用廟會,改造廟會!娘娘廟會上宣傳養娃娃紡線線“布施”錢入到衛生合作社》,這則新聞報道的是在延安柳林的娘娘廟會上,200多個婦女圍著婦聯的同志看《怎樣養娃娃》的畫本子,這屬于醫療衛生知識的宣傳教育。1945年10月14日的《注意邊區婦女衛生紡織學校招收學生》,則報道了邊區婦女正規的學校教育情況。
從婦女與教育的報道中我們可以看出,邊區婦女的教育不僅是文化知識的學習,還包括其他生產技能和衛生知識等的學習,內容較豐富,對婦女的生產生活具有積極意義。這類新聞反映了當時的邊區政府靈活的政策,報道中也有一些女性表現突出,這說明女性也是追求上進的。婦女在接受各種教育的過程中,自身的素質也得到了提高。
三、婦女典型人物具有示范作用
典型報道在延安時期的報紙中占重要地位。在陜甘寧革命根據地,一批典型通過《解放日報》《邊區群眾報》等進行了廣泛傳播。“典型報道有一套完整的理論,這一理論是由雙層面構成的。第一層面來源于毛澤東的黨報理論,它作為指導方針構成典型報道理論的基礎。第二層面是毛澤東的典型方法,它作為報道方式的內在規定構成典型報道理論的主體內容。”[4]要研究典型報道,需要與毛澤東的黨報理論聯系起來。毛澤東的黨報理論強調“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突出新聞傳播的群眾性,記者要深入群眾進行調查工作,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在記者進行廣泛調查的過程中,一批勤勞勇敢、善良純樸的典型人物涌現出來。
《邊區群眾報》的女性新聞報道中的婦女典型主要是女勞動英雄、婦紡模范等。《邊區群眾報》的女性新聞報道中的典型人物,雖然個人情況不同,但是也有共同點,即勤快、能干、肯吃苦。婦女典型人物為郭鳳英、折碧蓮、張荏英、杜鳳英、郭蠻兒、石老婆、王三女,一共有7位女性,其中有關郭鳳英的報道有兩篇,在1943年和1947年分別進行了報道,可以看到這個典型人物的個人發展情況,具體為1943年12月19日的《女英雄郭鳳英紡線,種地,又攬工》,1947年2月26日的《郭鳳英當了村主任》。
這類報道在女性新聞中極為突出,因其報道的是女性的榜樣,和其他的女性報道不同。有些報道中的人物是有姓名的,這體現了對婦女的尊重。因為在當時的中國,婦女的地位較低,許多人沒有姓名。結婚后被冠以夫姓,大多是以某某的婆姨、老婆等來稱呼。而這些人物典型在報道中都有姓名,她們的名字被傳播,事跡被書寫,說明婦女的社會地位有很大提高。在中國新聞史上,這些女性典型人物是一批最先進的婦女的代表,也因其主體性的建構而占有重要地位。
在認知層面上,典型報道也符合人們的認知方式,即從個別到一般。典型人物是個別的、特殊的,從對她們的了解,逐漸擴展到對普遍事物的了解。女性典型人物報道具有鼓舞、引導和示范的功能,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通過典型人物引領和組織廣大根據地的婦女,對婦女工作的開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從這些報道中可以看出我國新聞典型人物報道的特點,其新聞性、政治性較為突出,多以宣傳為主。由于版面和體裁的限制,大部分的女性典型報道比較短,對人物的介紹不夠詳盡,對女性典型人物的塑造是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不夠豐滿,但是在只言片語中,可以看到女性獨特的品質,她們作為典型的示范價值依然得以發揮。
四、激發婦女參政議政的熱情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婦女的解放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結合,也被提到了一定的政治高度。在此過程中,我們也特別強調婦女的參政議政。
在抗戰時期的革命根據地,婦女在政治上的權利受到重視。婦女們十分珍惜自己的權利,參政議政的熱情高漲。各根據地婦女的參政人數都很多。陜甘寧邊區的有些地方,女性選民人數甚至超過男性。還有的婦女進入各級參議會。“綏德各保四百六十位參議員有八十位女參議員,占全體參議員的六分之一。”[5]
在《邊區群眾報》與婦女參政議政有關的報道中,有幾篇是婦女當了村長、鄉長和縣長的。如1941年8月3日《安塞歡迎邵縣長》,報道的是安塞縣新上任的女縣長邵青華受到了熱烈歡迎。
另外,1945年9月16日的《怎樣發動婦女講話?》報道的是選舉經驗,如何讓婦女積極發言議政。1946年3月29日的《女議員批評重男輕女的提案》,報道的是女參議員李平英批評并糾正一些人重男輕女的看法。
從這些報道中我們可以看到,個別優秀的女性成為各級政府的領導,發揮著主體性作用,表現出一定的領導能力。還有的女性參政議政,代表女性發聲,批評重男輕女的思想。這些報道都表明在當時比較艱苦的社會環境中,婦女的政治權利得到了保障,也進一步激發了邊區婦女的參政議政熱情。
五、倡導女性婚姻自主
在舊中國,婦女的婚姻不自主,買賣婚姻一直存在,實質是把婦女當作商品,也是對婦女的壓迫。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婦女的婚姻自主問題。1939年4月,陜甘寧邊區政府頒布了抗日民主政權下的第一個婚姻條例。盡管婚姻條例已經頒布,但是女性的婚姻自由施行起來很困難,買賣婦女、買賣婚姻依然存在。這在《邊區群眾報》上也有所呈現,該報有買賣婦女的事件報道,也有反對買賣婚姻的來信及政府對買賣婚姻的處罰等報道。如1945年3月25日的《貪錢賣妹子,男大女太小這門親事政府應該禁止》等。另外兩篇是1941年7月20日的《反對買賣婚姻》,1945年5月13日“來信和回信”欄目刊登的《怎樣禁止買賣婚姻》,都表明了反對買賣婚姻的態度。
針對買賣婚姻嚴峻情況,邊區政府在1946年4月23日通過了《陜甘寧邊區婚姻條例》:
第一條男女婚姻以自愿為原則,實行一夫一妻制。
第二條禁止強迫,包辦及買賣婚姻。[6]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暴力的報道,多是公婆虐待兒媳(有的是童養媳),如1946年6月16日《婆婆虐待媳婦政府應當糾正》、1946年7月21日的《陳老漢保證再不打媳婦》等。其中,1945年9月30日的《新正陽坡頭張家老婆把媳婦硬是折磨死了》是一個極端的例子,顯示出當時的婦女在家庭中沒有自主權,承受家庭暴力乃至死亡的事實。也有一些新聞報道了家庭和睦、婆媳關系融洽,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社會在不斷發展,婦女的家庭地位得到提高。1945年4月29日的《婆婆媳婦和好了老牛能夠換好牛》、1946年3月3日的《吃稀吃稠在一鍋媳婦到底是自家人》,這些新聞報道了一些群眾經過政府的宣傳教育,認識到媳婦也是自己家里的人,也是需要尊重的。婚姻家庭關系對女性來說非常重要,婚姻的自主,家庭的和睦,都是該報報道的內容,也對當時邊區婦女的婚姻家庭觀念有一定的影響。
六、反對舊思想和封建迷信
在20世紀40年代的陜甘寧邊區,廣大群眾的思想還較傳統守舊。一些舊的思想和做法是對婦女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控制。
《邊區群眾報》的女性新聞中有關舊思想的報道,主要是婦女纏腳的問題。纏腳是對婦女身體的規訓,是舊的社會文化對女性身體的束縛,也是對婦女整體的控制。“如果站在解放的開端處,婦女解放就是腳的解放。腳的解放意味著行動的自由,而自由之于女人,則是行動的可能性,而非政治意義上的公共自由。”[7]可以說,不讓婦女纏腳是從身體層面對婦女的解放。
1945年9月2日的《邊區群眾報》刊登的《媽媽的痛苦不再傳給女兒》報道的是一個開明的媽媽,反對丈夫給女兒裹腳的事情。1946年3月29日的《不要再給女娃娃纏腳!》,講的是一位讀者親眼所見一些農村地區給女孩纏腳,看到她們走路很困難,就給編輯部來信,希望政府宣傳勸說群眾不要再給女娃娃纏腳。這些報道都是在對舊的思想作抗爭,也是對婦女解放的深刻教育。
有關婦女封建迷信的報道,如1945年9月9日的《賈家婆姨腦筋舊害得女子爛耳朵》、1945年10月7日的《老娘婆信迷信雞嘴塞在娃嘴里差些害了娃的命救活娃還是江醫生》。還有對婦女養孩子有一定幫助的,如1945年4月15日的《“扣娃”送了娃的命》。這篇報道開頭寫道:“冬春交季和秋冬交季的時候,鄉下的娃娃最容易得傳染病,這些病本來是可以用藥治好的,可惜有些老百姓不懂,信神信鬼,把娃娃害了!”報道對比了娃娃得傳染病的時候,“扣娃”(即送鬼)和給娃娃看病吃藥,結果“扣娃”送了娃的命,給娃吃藥后病好了。通過對比,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式讓婦女意識到不應該相信封建迷信。
這些報道反映出婦女的舊思想和封建迷信對其造成的嚴重危害,通過新聞事實的披露對群眾破除舊思想、反對封建迷信具有積極的作用。
在中國,婦女運動是整個革命運動的一部分。19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發布的《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是與婦女相關的第一個指導性文件,其中指出:“婦女解放是要伴著勞動解放進行的,只有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權,婦女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六大的《婦女運動決議案》指出:“只有共產黨,只有無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才能完全解放婦女。”[8]婦女的解放被納入到階級和民族的解放斗爭中,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因此,邊區政府的支持是根據地婦女發展的關鍵。
1946年4月7日《邊區群眾報》上刊登中共西北局書記習仲勛的文章《慶賀邊區群眾報六周年》:“這個報紙是邊區群眾公認的好報紙,誰都喜歡它,誰都愛護它。為什么好?是因為它不但容易讀、容易懂,并且說出了邊區群眾要說的話,講出了邊區群眾想知道的事情。”“日本打敗了,邊區較前鞏固了,《邊區群眾報》是有很大功勞的。”由此可見,《邊區群眾報》作為邊區政府的耳目喉舌,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邊區群眾報》的女性新聞也說出了婦女的話,在廣大革命根據地婦女中很受歡迎。《邊區群眾報》這些女性新聞不管從文本層面還是話語層面,都具有時代特色,不僅宣傳了邊區政府的婦女政策,建構了根據地婦女的主體性,還推動了婦女的發展。
[1]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37—1945)[M].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261.
[2]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37—1945)[M].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646.
[3]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第四輯[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54.
[4]吳廷俊,顧建明.典型報道理論與毛澤東新聞思想[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3).
[5]動員邊區婦女來參加選舉運動[N].解放日報,1942-06-21.
[6]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第三輯[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133.
[7]張念.性別政治與國家:論中國婦女解放[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103—104.
[8]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7—1937)[M].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325.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學與傳播學系2014級博士生)
編校:張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