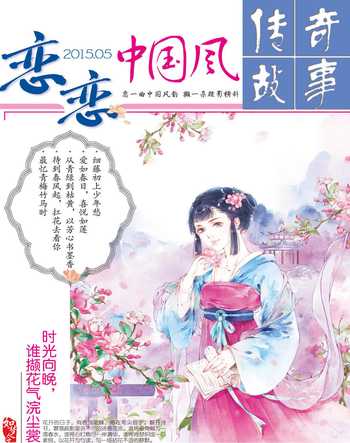一次驚鴻,從此比肩
嵐楓
1930年的一天,周培源正在朋友劉孝錦家做客。他是清華學堂公派出國的學生,只用了三年時間,就在加州理工獲得了博士學位,還拿到了最高榮譽獎。回國后任教清華大學,那年,他剛剛27歲。
周培源年紀輕輕便執教清華,可謂前途光明,劉孝錦開他玩笑,說他的愛情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周培源拊掌大笑,說清華的女生少,物理系的女生更少,哪里有人瞧得上他。
他這話不過是開玩笑。周培源生于無錫,有著南方男子少有的高大身材,相貌也周正英俊。哪里是別人看不上他,只不過是他一門心思埋頭苦讀,才耽擱了戀愛。
朋友也笑,說不如替他介紹。清華女生少,她所在的北平女子師范大學可是秀色滿園。說著,她果真拿出一沓同學的相片來。
周培源一張張翻著相片,突然停了下來,指著其中一張道:“就是她了。”
劉孝錦細看那張照片,倒吸一口冷氣。都說周培源眼界高,傳言果然不虛。相片上的女孩子大多氣質不俗,可這么多人里,他只看上了王蒂澂。
王蒂澂那年20歲,就讀于北女師英文系,是公認的“校花”。
劉孝錦回望周培源,只見他望著相片微笑,下巴輕輕揚起。自古才子配佳人,劉孝錦決心成人之美。
她安排了一次宴會,把周培源和王蒂澂都請了過來,并將兩人座位安排到了一起。
那天兩人都如約而至。王蒂澂一身淡雅衣裙,輕輕入座,周培源坐在她身側,離得那么近,他將她看得很清楚。她生得細巧纖瘦,瓜子臉,柳葉眉,眼睛是單眼皮,細細長長。不算多美艷,但她的秀氣卻讓人無端生出許多憐愛來。
上菜時,她吃得很少,他猜想她是不好意思,便熱情地替她布菜,夾很多到她碗里。其實她不吃是因為菜不合她的口味,望著碗中堆積如山的韭菜,她忍不住笑起來。
他看著她笑意深深的眼,不由自主地紅了臉。
此后,他便總去北女師的宿舍找她,去得多了,門房阿姨都認得他了,每每見著他走來,就在門口喊:“王蒂澂小姐,有人找。”
她素來是大方率真的人,他也隨和開朗,在笑鬧中,他和她的愛情潛滋暗長,彌久愈深。
1932年,他們舉行了婚禮,婚后居住在清華南院。晚飯后,兩人總相攜出門散步。漸落的夕陽下,他們并肩而行的背影,亦是清華園一道絕佳風景。
婚后三年,他們生了兩個女兒—如枚和如雁,給他們生活增添了許多樂趣。然而,就在這時,她患上了肺結核。
因為肺結核有傳染性,她需要與家人隔離,于是,他把她送到了香山眼鏡湖邊的療養院。那年,他除了上課和探病,還需照顧兩個幼女。可他從沒耽誤過探視。從清華到香山,當時只有一條崎嶇不平的土路,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數十里,風雨無阻。探視有時間限制,他來了便舍不得走,被護士“驅逐”出門后,他就悄悄來到窗戶處,爬上窗臺。
她躺在病榻上,看到他站在高高的窗臺上沖她揮手,兩只手都是黑灰。怕被護士發現,他不敢出聲,只比著嘴型說好好養病,見她看懂了,便笑得像孩子一樣。
她哭了,眼淚打濕了枕巾。在香山療養一年,總算是痊愈了。
之后幾年,他們相繼有了如玲和如蘋。春天的北平,櫻花綻開,如錦如雪,微風拂過,櫻花翩然墜地,在北京高遠的碧空下,美得宛如畫境。櫻花樹均由周培源打理,他極愛花,還常常戲稱家中有“五朵金花”,其中四朵是女兒,另一朵是王蒂澂。
她的一生如蓮純潔,始終嬌嫩清芬,與他成婚的這些年,她沒有處過什么淤泥之中,因為他始終把她捧在掌心。
每年春天,他們都要結伴出門踏青,他一路攙著她,生怕她磕著碰著。他對她好到連女兒們都“嫉妒”了,每次郊游,拎著大包小包行李的女兒總在后面無奈地喊:“對不起!麻煩你們兩位分開一會兒,幫我照看一下東西。”
王蒂澂習慣晚起,每天早晨,他都會在她睜開眼時,和她說“我愛你”。直到有天她突然生了場大病,再也站不起來了。可是,他還是和從前一樣,每天一大早跑到她床前,問她:“你今天感覺怎么樣?腰還疼不疼?別怕困難,多活動……我愛你,六十多年我只愛過你一個人。你對我最好,我只愛你!”
那一年,她已經80歲了,他也年逾九十,他們都老了。
他五十歲左右便右耳失聰了,從那時起,說話就不由自主地大聲嚷嚷,生怕別人聽不見。每天早晨,他對她的表白也嚷嚷得眾人皆知。
長大了的女兒們,聽到老父親的綿綿情話都忍俊不禁。王蒂澂不好意思,嗔道:“你好煩啊。”他只是笑,笑容還是那樣澄澈明凈。她突然想起,曾經他也是這么笑著看她,在香山療養院高高的窗臺上,在師姐劉孝錦家的宴會上,他看著她,笑得如同小孩子。
某個早晨,他又來和她說話。他看起來有些疲憊,王蒂澂想他大概沒有睡好,于是催他再睡一會兒。他說:“好的啊。”然后乖乖上了床。這一躺下,就再沒有起來。
她還以為他又在和她開玩笑,他一向是個幽默的人。可是很快,她便知道了,這一次,他是真的走了。
那是1993年,那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而漫長。
沒有人再“煩”她了,沒有人再把她這個老婦人當小孩子寵了,沒有人再對她展露明凈笑容了。她發了很大脾氣:“你不講信用!說好了,你先送我,可你連個招呼也不打,你說走就走,你連再見也不說……”她一面怒著,一面慢慢握住他的手,很涼,她的淚水一滴滴落下。
一生當中,他對她的承諾從來沒有不作數過,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