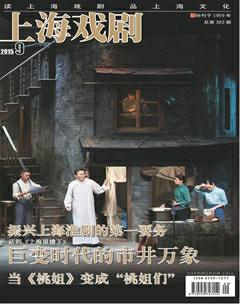抗戰與中國戲劇
戲劇是要為抗戰服務的,但是不能認為,只有直接表現抗日戰爭的現實題材才是為抗戰服務。戲劇的根本意義原應該是真實地反映多方面生活,塑造典型人物,提高人們的思想認識,浸潤人們的高尚情操,促進社會進步。因此,不僅直接表現抗戰的戲是為抗戰服務,凡是以先進思想和真實形象表達愛國主義、人道主義,鼓舞人們向上,追求真善美,反對假惡丑的戲都應該肯定是為抗戰服務。
劉厚生《抗戰戲劇散憶——話劇對抗戰勝利的貢獻》2015.7
(夏衍)“顛沛三年,我只寫下了三個劇本:在廣州寫了《一年間》,在桂林寫了《心房》和《愁城記》。這三個戲的主題各有不同,而題材差不多全取于上海——一般人口中的孤島,和友人們筆下的‘愁城。為什么我執拗地表現著上海?一是為了我比較熟悉,二是為了三年以來對于在上海這特殊環境之下堅毅苦斗的戰友,無法禁抑我對他們戰績與運命表示衷心的感嘆和憂煎。……想寫一個文化青年由小圈子斷然跳到大圈子去。”這里面有著夏衍自己的影子,田漢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寫在了《序〈愁城記〉》一文里:但夏衍是可信的。他告訴我們該走向大圈子里去。他自己就是首先從小圈子里跳出來的人。
沈蕓《戲劇抗戰:風云激蕩中的“霧季公演”》2015.8
那時節(指抗戰前,編者注),各地的活動總是在都市里打圈子;結果呢,熱鬧過幾天便又依然沉寂。抗戰以后,戲劇要負起喚起民眾的責任,于是就四面八方地活動起來,到今天已經是抗戰需要戲劇,戲劇必須抗戰,二者相依相成,無可分離。這是多么使人興奮的事呢!有些人或者還不相信文藝到底有什么抗戰的力量,因而也就以為設若文藝躲開抗戰也許更委婉漂亮一些。我說,這是閉著眼瞎講,完全與事實不合。對戲劇,我是外行,不錯;但是我所看到的事實,至少也使我沒有造謠扯謊的罪過。
老舍《抗戰戲劇的發展與困難》19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