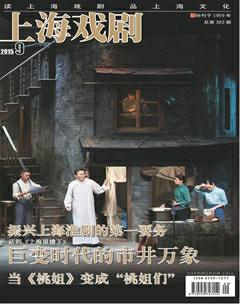“潮”笑欽差
臧保云
第一次感到,俄羅斯經典戲劇距離年輕一代觀眾,并不遙遠。
俄羅斯亞歷山德琳娜大劇院的《欽差大臣》,無疑是一出“潮”劇。導演瓦列里·福金將此劇從“經典”的神壇上解放下來,既保留了原作的批判力度,又為其灌注了新的活力,不僅贏得有著俄羅斯情結的老一輩觀眾的贊嘆,更有意義的是,它拉近了與當今年輕觀者的距離,讓他們在劇場里笑并反思。對于一部產生于19世紀的劇作,瓦列里·福金自有其21世紀的闡釋系統,無論空間布置還是節奏把控,都散發出新時代氣息。
導演以造景和調度傳達的現代空間概念,首先打破了人們對于經典戲劇的既定印象。戲以市長向大家宣布欽差大臣要前來視察的消息開場,觀眾對碎碎念的語言機巧并不感興趣,亮點在造景。一個簡單的手繪景片,假定了故事發生的場景,眾人被推至舞臺前方,隨景片的橫向挪移進行調度,在揶揄、調侃中暴露慈善醫院、郵局、教育、警察署等各個部門的腐敗,直指批判的核心。布景上開出的一扇小門,又填補了平面調度帶來的不足,一眾有頭有臉的官員從狹窄的小門中魚貫而出,自然生出了視覺上的滑稽感,并于一開場便奠定了群像基調。時不時從門后冒出的仆人,也為相對沉悶的“交待戲”增添了不少生趣。
旅館這場戲,則著重于縱向空間的延伸。立在空曠舞臺上的,與其說是一間寫實的小旅館,不如說是一種功能性造景。正如同電影畫面的內部蒙太奇,樓梯被巧妙地設置為縱向調度的手段,機智地對演出空間進行調控和布局。搞笑的旅館伙計靈活地從下面鉆出來,心虛的市長小心翼翼地邁下樓梯,不明就里的赫列斯塔科夫則躲在奧西普的身后瑟縮著,人物行為帶動焦點變換,流暢又不失生動。這家旅館低調、不考究,卻因住著一位“大人物”而使市長等人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當錯認赫列斯塔科夫為欽差之后,旅館又成了可移動的身份標志,被眾人推向舞臺縱深處。在空曠的舞臺上,讓戲集中發生在一處逼仄的鏡框里,聚焦局部帶來更為飽滿和張揚的戲劇性。此一場節奏輕快,引得笑聲陣陣,少不了導演對于道具和空間的精當處理。
舞美原是走極簡路線,卻在進入市長家不久后,風格陡轉。盡管依然是垂下來的景片,色調卻華麗起來,巨大的柱子很是醒目。垂吊的兩大片哈哈鏡說明導演走的并不是寫實的路子,舞臺上是一個夸張、變形的空間。導演在此劇中突出的是“對心理主義的深度探究”。市長的家其實是眾人的權欲之城,是他們夢想中的彼得堡。住到彼得堡是權勢上升的象征,“欽差”的到來,使他們對這座城的想象更進一步。市長太太和女兒的表現尤其迫不及待,她們像小丑一樣攀附在又大又粗的柱子上,期待獲得榮寵。而當一封信件道出真相、市長一家的幻想落空,大柱子適時地升上去時,市長夫婦緊緊將其抱住,不舍得放開。全劇唯一的“豪華”造景終于道出了導演意圖,他從極簡走向華麗,是要借一個極端絢爛的美夢以及最終的美夢成空,犀利地嘲諷一群小丑的欲望和貪婪。同時,立體空間設計,方便導演進行交叉調度,各色人等與“欽差”從不同角度產生關聯,舞臺呈現力求豐富和動感。
從平行調度到縱深調度再到眾人在“欽差大臣”的操控下滿臺亂轉的交叉調度,充分闡釋了導演的現代空間觀念,他不刻意追求經典“再現”,而擅以舞臺造景和空間調度的契合,延展敘事的層次。
“節奏感是導演最重要的素質之一。”諷刺喜劇的重心往往不在突出某個個體形象,而是通過整齊劃一的滑稽群像反映世態,塑造類型化、符號化的群像因此成為該劇的主要戲劇任務。對于群像戲來說,節奏尤其關鍵。本臺演出,導演以合唱隊的人聲伴奏這種簡潔又有質感的形式,來控制節奏、輔助敘事。腐敗已經侵蝕到這座城市的每個部門,代表各個部門的眾官員為求自保并獲得利益,必須在“欽差”到來時極盡所能地表演。于是,隨赫列斯塔科夫手中教鞭的揮舞,合唱隊介入敘事,眾官員步履一致、丑態畢現,活生生一幅“群丑圖”。漫畫人物的同時,諷刺的力度亦被推向極致。
對整齊劃一的節奏感的追求,實際是以突出動作性的現代劇場性,來代替文本中“重復”的力量。原劇中,法官、郵局局長、督學、慈善醫院院長等人對赫列斯塔科夫的爭相獻媚,是一沓重復而同質的動作。重復當然是有力量的,它的力量在于強調和突出,以求眾人丑態盡顯;但同時,也難免冗長、拖沓。眾官員無比漫長的行賄過程,在本次演出中被處理得干脆得當,只滅一次燈的功夫,就看到了行動的結果:赫列斯塔科夫手上拿著一堆塞了錢的信封。澤姆利亞尼卡則以夸張的賄賂行為,成為這群人的代表,解釋了被省略的內容,批判力度絲毫不亞于一系列重復性動作。當得知市長與“欽差大臣”攀上親之后,眾人前來奉承的歡慶場面,便是以合唱隊的歌唱和集體舞蹈來表現的;而當真相被揭露,他們又集體迸發出一陣刺耳而尖刻的嘲笑聲。機械的、整齊如一的節奏,形成一種強烈的喜劇張力,在反諷之余,毫不客氣地透視落井下石的滑稽官場。
將劇情刪繁就簡,以節奏感突出劇場性,是現代劇場美學理念的重要體現。在劇場里,觀眾暫時忘卻了果戈里這位大師,而沉醉于瓦列里·福金新潮的批判體系中,并嘆服于其與時俱進的戲劇理念。批判的意義不在于嘲笑,而在于反思。當騙局已成定局,真的欽差大臣就要前來時,市長整理好儀容,蹣跚走出已落空的“彼得堡”,來到舞臺前方,景片落下,回復第一場的布景——他又在絮絮叨叨,開始了與眾官員的第二次“戰略部署”。一出丑態百出的諷刺喜劇在尾聲竟引人心生悲憫,觀眾真正嘲諷的不是這些夸張到變形、滑稽可笑的喜劇人物,而是他們指涉的荒唐世相。諷刺喜劇的精神,大概就在于此。
聰明的導演應該知道,這是個解放經典,甚至“下放”經典的時代。戲劇演出的價值在于引動觀眾,我們需要放下“經典”的姿態,讓它親切地面世,而不是守著歷史和時代給予作品的光環,困坐枯城。“潮”不是反叛經典,而是為經典尋求當下闡釋的多種可能,是一種追求進步的態度。俄羅斯亞歷山德琳娜大劇院帶來的《欽差大臣》,并不是零瑕疵(比如第一場戲的處理依然相對保守),但整體地看,它是經典作品真正意義上的當代演繹,因為我們在一個模糊了時代感的城市,看著俄羅斯人,聽著俄語,卻并不感到陌生。回想起焦晃等前輩藝術家于五六年前在上戲劇院演出的《欽差大臣》,嚴肅、規矩、華麗,卻高高在上。
也許,我們仍需一次戲劇觀的大討論。
(作者為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教師,上海戲劇學院在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