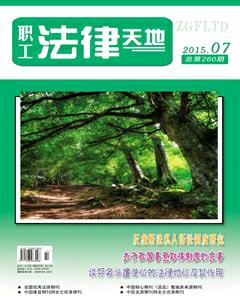淺析行賄罪的輕刑罰化問題
楊錚銳
摘 要:針對行賄之風愈演愈烈的形勢,很多學者認為應當加重行賄罪的刑罰,最好是同受賄罪同罰。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妥的,文章從行賄之風的形成,行賄罪輕刑罰化在司法實踐中的作用,刑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則,我國的刑事政策以及國外關于行賄罪的立法實踐角度論證對行賄罪輕刑罰化是有據(jù)可循的。
關鍵詞:行賄罪;輕刑罰化;法律依據(jù);事實依據(jù)
行賄罪是指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含在經(jīng)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guī)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數(shù)額較大,或者違反國家規(guī)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各種名義的回扣費、手續(xù)費)的行為。關于行賄罪侵犯的客體,理論界存在爭議,有的認為是侵犯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有的認為是正常的社會管理秩序,有的認為是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有的認為是侵犯了國家的廉潔制度。根據(jù)《刑法》第三百九十條的規(guī)定:“對犯行賄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賄謀取不正當利益,情節(jié)嚴重的,或者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chǎn)。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很多人對此表示質(zhì)疑,認為,受賄罪可以判處死刑,而行賄罪最高才無期徒刑。而且實踐中,行賄罪多以緩刑而告結,應當與受賄罪同罰。
一、行賄罪刑罰輕于受賄罪的法律依據(jù)
從司法實踐上來看,行賄者多得到了緩刑或減刑,而將行賄輕刑罰化對打擊貪腐受賄是極為有效的。行賄受賄一般都是一對一進行的,只有行賄者和受賄者雙方知曉,在當前刑偵技術還不夠完備的情況下,定案的依據(jù)往往只有受賄人的供述,行賄人的證言和少量的書證物證,證據(jù)較為單一。所以對行賄者口供的依賴性就大大提高,偵查人員一般都是先要獲得行賄者的口供,然后再借助行賄者的口供去尋找其他的直接證據(jù)。而且受賄者一般都位高權重,在沒掌握證據(jù)之前不宜直接接觸,而行賄人就成為最直接和有效的橋梁。將行賄罪輕刑罰化有利于瓦解行賄者和受賄者之間的同盟關系,降低司法成本,使行賄者成為司法人員查獲貪腐分子的支持力量。實踐中,檢察機關往往和行賄人達成某種默契,以減輕甚至不追究行賄人刑事責任為條件,換取他們的供詞,在受賄案中以證人身份出現(xiàn),事實上,這種交易方法也行之有效,有利于受賄案件的偵破。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對行賄罪輕刑罰化是切合現(xiàn)實的一個考量。
從刑法理論上來說,罪刑相適應是我國刑法的一個基本原則,對一個罪設置刑罰,必須以該罪的社會危害程度作為基礎,以其侵害法益的程度范圍方式為依據(jù),侵害法益嚴重的,刑罰應當重,侵害法益較輕的,刑罰應當輕。對于行賄罪來說,盡管行賄者確實是權力尋租的造意者,是受賄發(fā)生的源頭,但是,僅僅只有行賄者單純的行賄行為,而沒有受賄者的收受行為,一般不會直接對國家和社會造成實際的損害,不論是學者們認為的正常的機關活動,正常的社會秩序,還是廉潔性。只有受賄者收受了行賄人財物后,才形成賄賂,因為賄賂的本質(zhì)是權錢交易,受賄者不收財,權錢交易沒有達成,也就不是賄賂了。因此從另一個角度講,沒有受賄也就沒有行賄,或者說通常意義上的行賄。所以,相較于受賄罪,行賄罪對法益的侵犯體現(xiàn)出間接性、依賴性,在危害程度上有所降低。這是行賄罪的刑罰應該輕于受賄罪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當前刑事政策上來說,對行賄罪輕刑罰化也是必然的選擇。我國現(xiàn)在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在新時期的發(fā)展。寬嚴相濟政策中的“嚴”,主要針對罪行十分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依法應當判處重刑的;而“寬”主要是指對于情節(jié)較輕,社會危害性較小的犯罪,或者罪行雖然嚴重,但具有法定酌定從寬處罰情節(jié),以及主觀惡性相對較小、人身危險不大的犯罪。從橫向角度來說,行賄罪不論從社會危害性還是人身危險性上都要輕于受賄罪。最高人民法院印發(fā)的《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中也明確指出,對于國家工作人員的貪污賄賂行為若發(fā)生在社會保障、征地拆遷等領域嚴重損害群眾利益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要依法嚴懲。
二、行賄罪刑罰輕于受賄罪的事實依據(jù)
首先從行賄背后的原因上來說,是比較復雜的。從文化上來說,我國向來注重人情關系,傳統(tǒng)倫理更是以家族倫理為中心推及社會各種關系,形成一個人際關系網(wǎng)。而且以宗法關系區(qū)分親疏、遠近、厚薄,形成等差之愛,把人情當作一種“資源”。其實這也是一種禮尚往來強調(diào)互惠的文化傳統(tǒng),這種習氣由來已久,滲透到人們?nèi)粘I罟ぷ鞯姆椒矫婷妫錅Y源還是要在這種熱衷編織關系網(wǎng)的文化傳統(tǒng)中探尋,這是一種慣性的延續(xù)。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是傳統(tǒng)習俗中的這些糟粕成為當下行賄之風盛行的文化誘因。但是行賄的道德環(huán)境越來越寬容了,我國傳統(tǒng)的人情社會環(huán)境中,民眾對行賄人的行為越來越持寬容的道德態(tài)度,對于行賄人的行為并不指責其做法是可恥的,人們更痛恨的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腐敗及容易滋生腐敗,缺少透明監(jiān)督的制度。除此之外,行賄也有其重要的經(jīng)濟環(huán)境。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經(jīng)濟飛速發(fā)展,百姓的經(jīng)濟能力也大幅提高,金錢成為衡量一個人能力地位水平的重要指標。在膨脹的物質(zhì)欲望面前,人性中理智節(jié)制的一面大大被削弱。而且伴隨著資本、技術、知識引進來的同時,資本主義腐朽沒落的生活方式也裹挾而來,享樂主義盛行,在相當多的“小環(huán)境”中,一些人所認同、所喜歡、所欣賞、所流行的不是高雅,而是粗俗、庸俗、媚俗、惡俗,貫穿的是赤裸裸的物欲,有些人被逼得入鄉(xiāng)隨俗,不入流什么事情都辦不成。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現(xiàn)在爆出的行賄數(shù)額數(shù)萬、數(shù)十萬一個比一個高,而且形式多樣化,房子、車子、干股,有形的無形的,甚至“性”也成為行賄的手段。行賄的成因,為對行賄輕刑罰化提供了事實上的依據(jù)。
三、結語
綜上所述,盡管目前我國對行賄罪的定罪和量刑并不盡完整,但是堅持其輕刑罰化的趨勢是符合法理符合實踐要求的,我國應該在堅持行賄罪輕刑罰化的前提下進一步完善行賄罪的刑事立法,以讓其充分發(fā)揮在打擊貪腐犯罪,維護社會正義方面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董桂文.行賄罪量刑規(guī)制的實證分析[J].法學,2013,(1):152-160.
[2]韓東成.新形勢下懲治職務犯罪的立法與實踐——職務犯罪偵查模式的轉(zhuǎn)型[J].上海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2014,(3):8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