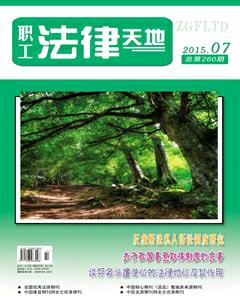關(guān)于有限責(zé)任公司對外擔(dān)保效力探析
艾攀
摘 要:有限責(zé)任公司對外擔(dān)保的現(xiàn)象在國內(nèi)屢見不鮮,隨著人大2005年對《公司法》大幅度的修訂,公司對外擔(dān)保制度的法律地位通過相關(guān)的法條被進一步確定。縱觀有限責(zé)任公司對外擔(dān)保相關(guān)內(nèi)容的立法演變,主要體現(xiàn)為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公司作為獨立的法人能夠行使處分自己財產(chǎn)的權(quán)能;另一方面,公司對外擔(dān)保能夠極大的帶動市場經(jīng)濟的活力。本文將就有限責(zé)任公司違反公司章程對外擔(dān)保的效力問題展開論述。
關(guān)鍵詞:有限責(zé)任公司;對外擔(dān)保;效力
一、公司對外擔(dān)保概述
公司對外擔(dān)保,是指公司以自己名義和自身財產(chǎn)為他人的債務(wù)提供擔(dān)保。擔(dān)保行為在公司經(jīng)營活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對公司股東、債權(quán)人等的利益有著重要的影響,同時也關(guān)系著公司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和生死存亡,公司“濫保”行為危害巨大。在現(xiàn)實交易中,為加快融資速度,公司往往更為注重效率,追求快速、便捷,而忽略了交易安全,對于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等程序能省則省,決定擔(dān)保的過程很隨意。很多情況下,甚至是法定代表人一人即決定了對外擔(dān)保事項。這種現(xiàn)象在私營企業(yè)中尤為突出。近年來,受經(jīng)濟危機、金融危機的影響,不少公司遭遇了滅頂之災(zāi)。有的公司本身經(jīng)營狀態(tài)良好,卻也受因不當(dāng)?shù)膿?dān)保行為所累,被效益不佳的公司拖垮,一家公司倒下往往會發(fā)生一連串的不良連鎖反應(yīng)。同時,因股東不滿法定代表人等高管擅自決定擔(dān)保而產(chǎn)生的爭端也屢見不鮮。
我國法律制定部門也認(rèn)識到了該問題,在《公司法》、《擔(dān)保法》等法律法規(guī)中對此作了相應(yīng)的限制。除法律強制性規(guī)范外,公司章程是公司平時行為的規(guī)范、準(zhǔn)則,但受有限責(zé)任公司封閉性的影響,公司章程內(nèi)容一般不為外界所知。
二、幾種常見的違規(guī)擔(dān)保情形及效力分析
1.違反公司章程實體規(guī)定越權(quán)擔(dān)保
包括公司章程禁止對外擔(dān)保和超越限額對外擔(dān)保兩種表現(xiàn)形式。根據(jù)擔(dān)保權(quán)人的主觀狀態(tài)可區(qū)分兩種情形:一是擔(dān)保權(quán)人知道或應(yīng)當(dāng)知道章程規(guī)定的,則超越權(quán)限范圍的應(yīng)為無效;另一類是擔(dān)保權(quán)人不知公司章程規(guī)定的前提下,則不宜一律認(rèn)定無效。如果公司章程未對外公開,擔(dān)保人也未向擔(dān)保權(quán)人予以披露,擔(dān)保權(quán)人與公司股東或高管之間也不存在特殊關(guān)聯(lián)等可推定其知道公司規(guī)定的情形,即可以證明擔(dān)保權(quán)人是善意的,則依據(jù)《合同法》第50條的規(guī)定,構(gòu)成表見代理,擔(dān)保權(quán)人的信賴?yán)鎽?yīng)受到充分的保護,此時的擔(dān)保行為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是有效的。但是,如果作出擔(dān)保決定的機關(guān)為股東會(股東大會),那么無論是否超越了章程的規(guī)定,也應(yīng)當(dāng)認(rèn)為該擔(dān)保行為是有效的,因為股東會(股東大會)是公司的最高權(quán)力機關(guān)和決策機關(guān),也是公司章程的制定機關(guān),其此時作出的對外擔(dān)保決議應(yīng)視為對公司章程的臨時修改,不應(yīng)認(rèn)定為是越權(quán)行為。
2.違反程序規(guī)定對外擔(dān)保
包括未經(jīng)法定程序由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對外擔(dān)保和作出擔(dān)保決議的機關(guān)不適格兩種表現(xiàn)形式,例如章程規(guī)定擔(dān)保決議的機關(guān)為股東會(股東大會),但實際作出擔(dān)保決議的機關(guān)卻是董事會。首先仍應(yīng)當(dāng)分析擔(dān)保權(quán)人是否知道或者應(yīng)當(dāng)知道公司章程對擔(dān)保決議機關(guān)和程序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即是否具有主觀善意,一般情況下,公司章程屬公司內(nèi)部規(guī)范,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但對于《公司法》第16條第3款規(guī)定的為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dān)保的情形,筆者認(rèn)為,法律對該種情況作出了明確的禁止規(guī)定,擔(dān)保權(quán)人對此是應(yīng)當(dāng)是明知的,即使公司章程未作出規(guī)定,只要是未經(jīng)公司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通過,都應(yīng)當(dāng)是無效的。當(dāng)然,例外情況是擔(dān)保權(quán)人不知道是債務(wù)人是公司的股東或?qū)嶋H控制人。實務(wù)中,還存在幾種特殊情況:一是提供擔(dān)保后,股東會(大會)或董事會再行決議對擔(dān)保行為予以追認(rèn);二是雖未按章程規(guī)定經(jīng)股東會或董事會進行開會表決,形成董事會(股東會)決議,但相關(guān)股東或董事均在同一合同中以擔(dān)保人或見證人身份簽名,或者通過其他方式作出認(rèn)可的意見。對該兩種情況雖然形式上違反了章程的程序規(guī)定,但實質(zhì)上已獲得了公司最高權(quán)力部門的準(zhǔn)許,并不損害公司的利益,從對債權(quán)人利益的保護原則出發(fā),應(yīng)對擔(dān)保合同的效力予以肯定。
3.擔(dān)保合同相對人“善意”問題判定
對有限責(zé)任公司對外擔(dān)保的效力的認(rèn)定,判斷擔(dān)保權(quán)人主觀是否善意為重要。那么,如何判定擔(dān)保權(quán)人“應(yīng)當(dāng)知道”公司章程規(guī)定呢?換句話說,擔(dān)保權(quán)人對公司章程是否有審查義務(wù)呢?筆者認(rèn)為,可以從章程的公開程度和擔(dān)保權(quán)人的身份兩方面進行考量。
我國法律、法規(guī)未對有限責(zé)任公司章程作出強制公示的規(guī)定。一般情況下,有限責(zé)任公司的章程不對外公布,第三人也無法獲知有限責(zé)任公司的章程內(nèi)容,要求第三人對公司章程進行實質(zhì)性審查顯然超越了其能力范圍。有限責(zé)任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內(nèi)部自治規(guī)范,僅對公司股東、管理人員等內(nèi)部人員和事務(wù)具有約束力,不能約束第三人。同時,《公司法》第16條約束的對象是提供擔(dān)保的公司及其股東和內(nèi)部管理人員,而非擔(dān)保合同相對人。因此,筆者認(rèn)為,主動披露公司章程、遵守章程規(guī)定、保證擔(dān)保合同效力應(yīng)是提供擔(dān)保的公司的義務(wù),擔(dān)保權(quán)人只要盡到了一般注意義務(wù),做到對公司章程的形式審查,不應(yīng)再強求其對公司章程進行實質(zhì)審查。
但對于具有特殊身份的合同相對人,則不宜作如此寬松的解釋。筆者認(rèn)為,特殊身份人主要有以下幾類:一是公司或其關(guān)聯(lián)企業(yè)的股東、董事、管理人員的親屬或密友;二是已離職的原公司的股東、董事、管理人員;三是其他應(yīng)當(dāng)知道公司章程的人員,如曾參與起草或?qū)徸h公司章程的人員、能夠接觸到公司章程的法務(wù)人員或文件管理行政人員、對章程進行備案登記的工商部門人員等等。對于有能力對公司章程進行審查的特殊人員,其不僅僅是一般的注意義務(wù),而應(yīng)當(dāng)具有較為嚴(yán)格的審查義務(wù)。其疏于審查的行為導(dǎo)致?lián):贤瑹o效的,應(yīng)自行承擔(dān)相應(yīng)的過錯責(zé)任。
綜上所述,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公司之間對外擔(dān)保的行為將會愈加廣泛。公司對外擔(dān)保行為也是公司的日常商業(yè)行為,是維持公司正常經(jīng)營所需,司法首先應(yīng)尊重公司的意思自治,不輕易否定擔(dān)保合同的效力。但商業(yè)競爭過于激烈,為維護交易秩序,限制公司濫保行為,司法實務(wù)中也要適當(dāng)運用對擔(dān)保合同的否定手段,以達到規(guī)范公司行為的目的,使當(dāng)事人理性地投資,依法履行注意義務(wù),審慎評估和防范風(fēng)險,注重交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