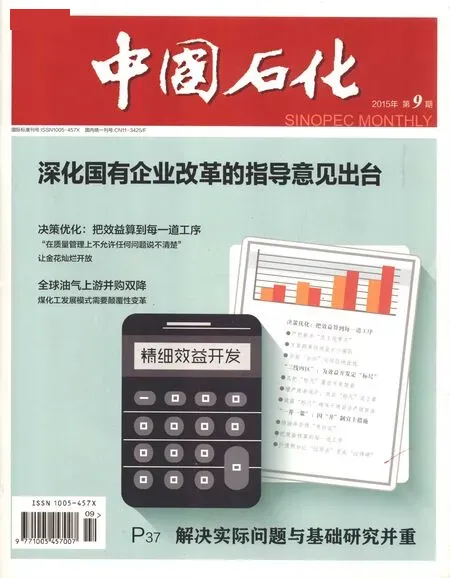讓金花燦爛開放
——第一套流化催化裂化裝置工程設計歷程回顧
□ 陳俊武/口述 李建永/整理
讓金花燦爛開放
——第一套流化催化裂化裝置工程設計歷程回顧
□ 陳俊武/口述 李建永/整理
在當時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如果沒有不分你我的大協作精神,沒有為國家奉獻的精神,沒有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就不會有今天我國催化裂化的輝煌成績。
今年5月8日,是我國第一套流化催化裂化裝置在撫順石油二廠建成投產50周年的日子。回憶起被譽為煉油工業“五朵金花”之一的流化催化裂化技術攻關歷程,依然歷歷在目。50年來,我國流化催化裂化技術之所以能夠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從當初依賴技術引進到當今工藝包整體技術出口海外,成為加工能力位居世界第二的催化裂化大國,主要在于上級領導部門的正確決策和堅定支持,產、學、研一體化的大協作精神,所有攻關人員“為國家爭光、為民族爭氣”的堅強意志。
受命
那是1961年12月的一天,在原石油工業部北京設計院南樓的一個會議室里,聚集著二十多名石油部和京、撫兩院(北京設計院和撫順設計院)的領導和設計人員。長長的會議桌上攤著一摞剛從國外某煉廠拿回來的煉油裝置流程簡圖和設備示意圖,大家正聚精會神地聽著考察團敖明模、何振鵬等同志介紹情況。
這次考察,他們不僅取得了一些新型煉油設備如舌形塔盤、分餾塔、立式加熱爐等方面技術資料,而且還實地參觀了西方大國對我們一直封鎖的、代表煉油先進技術水平的“IV型流化催化裂化裝置”。與會人員都為我國當時煉油工業技術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差距之大而震撼。每個人的心里都是熱乎乎的,好像寒冬中突然來了一股暖流!
當時,號稱煉油技術的“五朵金花”之一的流化催化裂化工藝裝置開發工作剛剛啟動。我們手頭雖然有了初步的技術資料,但是要實現中國人自己設計、自己制造設備和自己施工建設,的確還存在不少困難。
千頭萬緒,工程設計必須先行。石油部主管煉油工作的領導十分重視,親自掛帥,成立了由撫順設計院(洛陽工程公司前身)、北京設計院(中國石化工程建設公司前身)技術骨干組成的“新技術組”,我和張福詒同志分別被任命為正、副裝置設計師。參加新技術組該裝置設計工作的還有北京院的袁宗虞、李樹鈞、戴家齊,撫順設計院的徐貽璜、謝泰嵩,以及北京石油學院的楊國威等同志,后來又增加了北京設計院的何宇、蘭州煉油廠的杜克勤等同志。這些同志工作熱情很高,對開發流化催化裂化新技術更是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盡管當時全國處在“大躍進”后的困難時期,頓頓吃的是大鍋煮白菜,睡的是零攝氏度的陰冷大房間,卻沒有一個人叫苦,幾乎每夜都加班到十一二點,夜以繼日地對技術資料進行消化,并與前蘇聯的IA/1M、美國的UOP等技術資料對比,確認了我們自己的流化催化裂化工藝技術路線,并結合國情制定了設計方案,有的設備打算“照貓畫貓”,有的打算全面搬用,還有些則打算利用一些庫存設備(如蘇聯為IA裝置提供的風機和氣壓機),同時還要委托當時的一機部抓緊試制一些專用新設備、新機械。在平面布置方案上,我們一反過去按設備分區的“四合院”式布局,采用當時國外流行的“三條線”布置方案。這樣就使裝置成為集新工藝、新設備、新結構和新布置為一體的、名副其實的新裝置,讓各個專業的設計人員都可以在各自區塊內大顯身手,為培育“金花”做貢獻。
由于我們對流化催化裂化裝置缺乏經驗,仍然習慣于用前蘇聯的舊設計指標去衡量,對一些疑點難以把握。例如旋風分離器的分離效率怎么會那么高?輔助燃燒爐的熱強度何以那樣大?雙動滑閥的靈敏度是否一定要達到四百分之一,等等。我們把這些問題分門別類地整理好,作為正在辦理手續的出國考察重要內容。

□ 1965年,部分設計人員在撫順石油二廠國內第一套催化裂化裝置前合影。
經過來自全國不同部門、不同單位、不同專業的科技人員夜以繼日地努力,我們于1962年6月底完成了整個裝置的初步設計,并通過了上級部門組織的中間審查。
遠征
經石油工業部申請,國家主管部門批準由何宇、虞冠新、李樹鈞、戴家齊、杜克勤、鄒玉書、吳欽偉和我8名同志組成赴國外某煉廠考察技術組。我們于1962年8月上旬出發,先乘火車后乘飛機,取道前蘇聯和捷克,歷時半個月到達了向往已久的國度。
當地石油公司給予了我們熱情的接待。薩拉經理接見了我們,安排我們參觀了該國一個有600多名員工、以革命英雄尼柯·洛佩茲命名的煉油廠。廠長指定了一名叫恩利克·馬丁內茲的中年人陪同我們,我們親熱地稱他為亨利。
我們提出了一個全面考察煉油廠的計劃,把重點放在IV型催化裂化裝置上。遺憾的是該裝置由于燃氣透平葉片損壞,委托國外制造的配件尚未交貨,處于停工狀態,設備也都封閉,看不到內部構造。我們只好改變方式,依靠主觀努力,收集相關的技術資料。
煉廠機動科的資料室里存放有藍圖、工程標準、操作說明書、產品樣本等資料。面對浩如煙海的資料和圖紙,僅憑我們考察組的幾個人在短時間內是無論如何都看不完的,更別提抄錄了。廠方破例同意我們周五下班后借出、周一上班時歸還。經過連續幾個周末的努力,我們獲取了大量生產一線的相關資料。
在石油公司的設計室,存放有不少第二底圖和重份藍圖。對方熱情友好地破格讓我們查閱資料。經過一段時間查閱和分析,我們基本摸清了開展流化催化裂化施工圖設計所必需的圖紙和資料。他們還贈送了一部分有備份的設計藍圖,使我們收集到了許多珍貴的項目施工圖紙。
當時,我們并不以取得以上技術資料為滿足。我們要求自己做到的是不僅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我從外文資料中獲悉有“催化裂化數據手冊”的信息,因此格外注意查找。功夫不負有心人,我不僅看到了該數據手冊,還看到了另一本對工程設計十分有幫助的《設計準則》。此外還查閱了不少國外知名石油公司的科技報告和技術交流報告(文集)。
為了將這些寶貴的資料帶回國,我和杜克勤兩個一人翻書、一人按相機快門,先后拍攝了200多個膠卷,高質高效地完成了資料微縮膠卷復制任務。
歷時半年的考察結束時,我們不僅帶回了施工圖設計所需的資料,還為科技信息部門提供了大批翔實的技術資料,經過分類作為內部資料翻譯出版后,為我國煉油工業發展壯大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借鑒,極大地縮短了我國煉油工業與國外同類技術先進水平的差距。
攻關
1963年3月,東北地區寒氣逼人,項目施工圖設計如火如荼地開展。新技術組中北京設計院的同志也移師撫順參加了大會戰。撫順設計院領導對這項任務十分重視,組織了精銳力量全面突擊,各級技術領導親自過問。我作為裝置設計師,自然責無旁貸。
首先,重新審定了初步設計方案。有些地方和國外煉廠情況不同,經過分析研究,結合國情重新予以確定。例如主風機采用電動機驅動,氣壓機改為離心式,用蒸汽透平驅動;對于某些關鍵設備的尺寸,我們按照領導指示“照貓畫貓”。裝置投產后僅僅過了幾年,有了實際經驗和體會,加上理論分析,我們對這些關鍵部位才敢于改動,而且取得了成功。
有了參考圖紙,不等于國內就可以設計和制造。我們手頭只有國外制造的系列產品的裝配總圖和安裝圖,要靠我們自己從零件開始進行設計。如雙動滑閥、單動滑閥和帶阻尼機構的單向閥等都是既大又靈敏的設備,技術要求很高。以袁宗虞老專家為首的機械專業和自動控制專業的設計人員為此花費了不少心血,并在試制過程中和制造廠緊密結合,不斷改進,終于按時交貨,為今后系列化批量生產、滿足全國新建裝置的訂貨奠定了扎實基礎。
換熱器雖然是通用設備,但過去用的是前蘇聯標準,管子和折流板孔的間隙大,折流板間距大,降低了殼程傳熱系數。我們在工程設計中一律改用新型換熱器結構,委托撫順機械廠制造,我們派人參加制作和性能標定。結合設備制造任務,我們還開展了新材料的研究試驗工作。“兩器”內部和旋風分離器內部的隔熱耐磨襯里材料就是委托建工部建材研究院承擔的。他們在較短時間內拿出了成果,基本達到了當時的美國水平。哈爾濱鍋爐廠也完成了隔熱龜甲網的試制,并建成了生產線,使我們徹底拋棄了前蘇聯的硅酸鹽襯里老型號,避免了開工中的襯里容易脫落及隔熱效果不佳的麻煩。
對于龐大的反應器和再生器,我國當時能夠自行制造,決定由石油部的第一工程建設公司在現場制造吊裝,何應訓專家負責實施。
對于大型旋轉式機械設備,由于試制周期長,石油部制定了國內外“雙管齊下”的方針。主風機先用前蘇聯IA裝置供貨的庫存設備,同時向沈陽鼓風機廠訂制了D800型新產品。離心式氣體壓縮機制作難度稍大,當時軸封采用封油的技術一時難以解決,我就向沈鼓介紹了在國外煉廠看到的抽氣密封結構。這一結構搞成后在國內用了十多年,起到了一定作用。對于國內當時還不能生產的氣壓機,則抓緊國外訂貨,很快落實了訂貨周期和生產周期最長的“三機”設備。
當年控制儀表采用的是氣動單元組合式儀表,石油部責成蘭州煉油廠負責試制,他們的研發非常高效,及時提交了大部分儀表。對于關鍵部位的變送器、二次儀表及溫控儀表則仍沿用國外設備。裝置儀表盤采用全模擬形式,在國內屬首次應用。
與此同時,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為主承擔的微球催化劑和大慶原油減壓餾出油的催化裂化條件實驗也按計劃進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豐碩成果,有力地保證了我國第一套催化裂化裝置的建設進度。
凱歌
施工圖設計于1963年秋,完成后,石油部及時組織了審查,從而使土建基礎工程得以盡早開工。1964年的春天,石油二廠工地上呈現了一派欣欣向榮的新氣象。撫順設計院從事二廠擴建設計的同志在院領導率領下組成小分隊進駐現場。我側重生產準備工作,張福詒同志側重現場施工。考慮到生產工人對流化催化裂化操作不熟悉,“兩器”操作又很復雜,我向廠方提出組織催化裂化學習班,受到了工人和技術人員的歡迎。
1964年7月,由于原先考察過的那家國外煉廠催化裂化裝置將要開工,為培養我們自己的生產和管理骨干,石油部再次組織生產技術人員前往實習。我和來自蘭煉的孫玉寶、王貫之,石油二廠的徐宗詩、張俊德等11名同志經過兩個月的西班牙語培訓后,于當年9月到達原先考察的煉油廠。當時那家煉廠催化裂化裝置正處于大檢修階段,我們在催化裝置兩器內部爬上爬下,了解兩器的結構特點和檢修內容,還進一步了解了一些專用檢修機具。在后來的倒班和生產實習階段,我除學習開、停工和正常操作、事故處理等方法外,還觀察有關操作參數的變化規律,特別注意把國內的裝置設計和現場實際數據進行對比,整理出了100多條需要進行設計修改的意見,寄回國內讓同事們進行修改。
根據上級指示,實習結束后,我們提名邀請了五名熟悉生產操作、儀表和化驗的國外煉廠老工人和我們一道回國。他們對我們國內第一套流化催化裂化裝置的開車成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記得剛回到撫順石油二廠那天,我就被叫到項目指揮部開會。當時,石油部基建司的敖明模同志已在現場坐鎮,會議內容是決定是否先用小球磨粉的催化劑考驗設備,然后再用從英國購買的微球3A催化劑開工。我根據國外煉廠學習的體會,認為完全不必要先用小球磨粉劑試運轉,有信心直接用3A微球開工。會議經過熱烈討論,最后同意直接用3A催化劑開工。后來的事實證明這項決策是正確的,不僅縮短了開工置換的時間,而且節省了操作費用。
1965年3月,工程收尾還在緊張進行,試運工作已開始有條不紊地展開。為了確保裝置一次試運成功,石油部從科研、設計、制造和生產單位抽調精兵強將,組成上百人的開工隊伍進行試運大會戰,由石油部基建司司長任向文任試運總指揮。在試運領導小組下設立了現場指揮組、技術參謀組和調度組,分頭開展工作。我參加了生產、施工和設計三方的協調會,對各方提出的400多條收尾項目進行了審定。自4月下旬開始,我作為值班工程師參加了一線倒班,經過大家共同努力,確保裝置順利闖過了流化關、新鮮催化劑老化關、進油關。5月5日晚8點30分,裝置反應器開始進油;經過43個小時的試運轉,于5月8日完全打通全流程,生產出合格的汽油和柴油。進入平穩生產后,裝置各項指標均達到設計要求,實現了裝置處理量、主要產品收率、產品質量和消耗指標的“四個一次成功”。我國煉油技術一舉跨越二十年,達到了當時世界先進水平。
彈指一揮間,我們的流化催化裂化技術已走過了50年的發展歷程。50年來,我始終認為這項煉油領域的戰略性重大成就首先歸功于石油部領導的正確決策。在當時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如果沒有不分你我的跨部門、跨單位的大協作精神,沒有為國家奉獻的精神,沒有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就不會有今天我國催化裂化加工能力達到1.5億噸/年、供應市場70%汽油消費量的成績。無論到何時,這種艱苦奮斗、求實創新的精神都值得我們發揚光大。
(作者單位:洛陽工程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