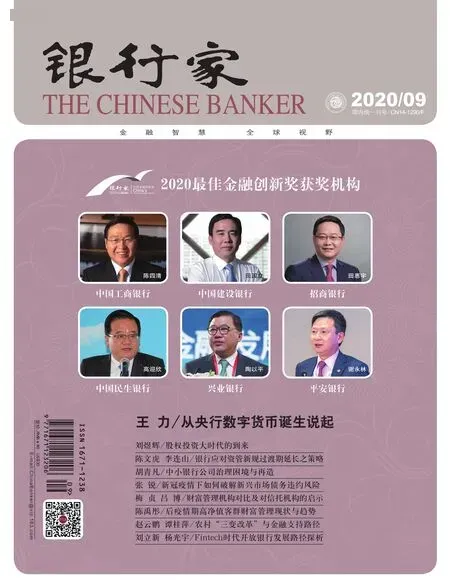再貸款創新及其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彭興韻
再貸款在貨幣政策操作中的地位再次上升
再貸款,即我國央行對金融機構發放的貸款,是我國央行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之一。改革開放以來,再貸款在我國央行貨幣政策操作中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2001年之前),再貸款是央行調控基礎貨幣的主要渠道,因而央行對金融機構債權構成了央行資產方的主要部分。對金融機構債權主要包括公開市場操作中回購交易形成的“買入返售”、再貸款和再貼現。2001年以前,由于公開市場操作并沒有成為央行調節基礎貨幣的重要政策工具,再貼現很少,因此,體現在央行資產中的對存款性金融機構債權基本由再貸款構成:即央行對金融機構無擔保的貸款。由于那時再貸款是我國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的主渠道,因此,那時央行對存款性金融機構債權增減,反映了央行根據宏觀經濟形勢變化而實施貨幣政策的銀根松緊的變化。例如,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國內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和通貨緊縮,央行為了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就通過增加再貸款來投放基礎貨幣。
第二階段(2002~2013年),再貸款在央行貨幣政策操作中日趨式微,再貸款基本被閑置。主要原因在于,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后,由于貿易順差的持續增長和人民幣升值預期下資本流入的大量增長,央行持有的國外資產大幅增加,外匯占款成了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的主要渠道。在這種背景下,央行貨幣政策操作就主要是為了沖銷外匯占款,央行沖銷流動性擴張的基本手段,先是大量發行央行票據,繼而通過大幅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以深度凍結流動性。由于之前央行的再貸款余額較少,難以通過縮減再貸款的方式來沖銷外匯占款導致的流動性擴張。因此,接下來的幾年里,央行再貸款在貨幣政策操作中基本上沒有發揮什么作用。盡管2005年前后,央行發揮金融穩定的功能而同包括一些證券公司在內的金融機構發揮了再貸款,但這并非常規貨幣政策操作的范疇。
第三階段(2014年至今),再貸款在貨幣政策操作中的地位得到極大提升。在2008年后,發端于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讓人們迫切認識到,全球經濟再平衡對全球宏觀經濟和金融體系穩定至關重要,因此需要重建新的貿易與金融秩序。在這種背景下,盡管中國仍有大量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入,但由于中國同時實施了“走出去”的戰略,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大幅增加,同時在美國大規模經濟刺激下,美國經濟企穩、美元升值,也吸引了一些短期資本流入美國。結果,中國人民銀行持有的國外資產不僅沒有隨貿易順差而增長,反而還略有下降。這為中國人民銀行資產結構的調整創造了非常積極的條件,即2001年后一直被“閑置”的再貸款開始有了發揮作用的空間。尤其是,2014年以來,再貸款在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的作用更加突顯,這反映了央行資產負債表中,央行對金融機構債權大幅增加。2015年5月末,央行對金融機構的債權總量上升到了38697億元,較2010年初的19697億元增加了近一倍。這表明,幾乎被“閑置”十多年的再貸款,在中國貨幣政策操作的地位再次上升。
經濟新常態下的再貸款操作創新及其功能的擴展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貨幣政策操作環境也隨之發生巨大變化。新的貨幣政策環境需要貨幣政策操作手段、方式、方法隨之而發生相應的變化。近年來,央行就在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引領貨幣政策新常態,通過不斷完善和豐富再貸款調控工具,使得再貸款在貨幣調控體系中的功能得以不斷擴充。
央行在再貸款的應用中,首先要不斷創設新的再貸款工具。目前,再貸款工具包括:支小再貸款,即是向金融機構發放的專門用于發放小微信貸的再貸款,這是為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而采取的定向再貸款;支農再貸款,即央行向一些符合條件的中小金融機構發放并由后者用于“三農”的央行早前還創設了支農再貸款,央行創設支小再貸款與支農再貸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市場缺陷;常備借貸便利,旨在向符合審慎要求的地方法人機構提供短期流動性支持,其主要目的是發揮常備借貸便利的利率作為市場利率上限的作用;中期借貸便利,向符合宏觀審慎管理要求的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提供中期基礎貨幣,可以發揮中期利率政策的作用,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和三農的信貸支持力度,促進降低貸款利率和社會融資成本;抵押補充貸款,是央行以抵押方式向金融機構發放的貸款,合格抵押品范圍主要是高信用級別的債券和優質信貸資產;信貸資產質押再貸款,以金融機構非標準化的信貸資產作為從央行獲得再貸款的合格抵押品,這一政策工具的應用,將極大地擴展中小金融機構從央行獲得再貸款的合格抵押品資產范圍,提高了這些金融機構信貸資產的流動性。
在創新再貸款工具的同時,央行還大量擴充了再貸款的抵(質)押資產。中央銀行在向管轄權范圍內的金融機構發放貸款時,通常會有合格抵押品的要求。金融機構向中央銀行申請貸款時所提交的抵押品,通常是其持有的某種金融資產。至于哪些金融資產可以充當合格抵押品,各國(地區)中央銀行則有不同的規定和要求;同時,同一個國家的央行在不同的時期、不同宏觀條件下,所要求的合格抵押品資產范圍也會有較大不同。例如,在2008年次貸危機后,美聯儲不僅拓寬了貸款對象,也拓寬了合格抵押品資產。過去較長一段時間里,我國央行對金融機構的再貸款并無合格抵押品的要求。2014年以來,央行就在不斷地擴寬合格抵押品資產的范圍:(1)高信用級別的債券,如國債、中央銀行債券和政策性金融債券。(2)商業銀行持有的信貸資產。抵押補充貸款便是以高信用級別的債券和優質信貸資產作為合格抵押品的。但央行在2014年開展試點并在2015年推廣信貸資產質押貸款中,所要求的合格信貸資產的品質,會遠低于抵押補充貸款的要求。(3)將地方債納入央行SLF、MLF和PSL的抵押品范圍內。此外,地方債還被納入中國國庫和地方國庫現金管理抵押品范圍。這是在2015年為配合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積極推動地方政府債務置換而采取的一項舉措。
隨著再貸款工具的豐富和完善、再貸款合格抵(質)押品范圍的擴大,再貸款的功能也隨之而豐富。但隨著央行不斷創新再貸款工具,再貸款在中國貨幣政策操作中發揮著四項重要新的職能:
第一,管理市場流動性。常備借貸便利是向地方法人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它與正(逆)回購操作、SLO一起,構成了中國央行對市場流動性管理和調節的工具體系。2013年6月,中國貨幣市場一度出現“錢荒”,緊張的貨幣市場流動性使短期貨幣市場利率高到難以承受的水平,給債券市場帶來了極大的沖擊,乃至隨后一年左右的時間里,中國債券市場利率都處于較高的水平。在那次錢荒之后,央行便創設了常備借貸便利,以應對市場流動性的意外波動。
第二,引導信貸結構調整。再貸款發揮著引導金融機構信貸投向三農、小微和棚戶區改造等國民經濟薄弱環節的功能。隨著新常態下政府更加注重定向調控,央行也試圖利用再貸款促進信貸結構調整、引導貸款利率的結構變化。支小再貸款、支農再貸款和抵押補充貸款,都發揮著引導金融機構信貸投向的功能。因此,再貸款不僅僅是總量政策工具,更是結構調整的工具。
第三,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央行的重要職能之一,就是發揮最后貸款的作用,為陷入流動性困境的金融機構提供援助,阻止少數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困境惡化為系統性的金融危機。1999年中國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后,央行為了幫助它們從國家銀行收購不良貸款就向它們發放了數億元的再貸款;2005年為了化解證券公司風險,央行就曾向數家券商提供了大量再貸款;2015年6月下旬和7月上旬,股票市場大幅下挫,為了穩定資本市場,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央行又向中國證券金融股份公司發放了數千億元的貸款,并承諾對資本市場的流動性救助不受限額的局限。所有這些,都是央行再貸款維護金融穩定職能的重要體現。
第四,引導和管理市場利率。央行在《2014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談到常備借貸便利時指出,其主要目的是發揮常備借貸便利的利率作為市場利率上限的作用;在談到中期借貸便利時指出,“發揮中期利率政策的作用,促進降低貸款利率和社會融資成本。”這表明,央行在貨幣政策操作中,不僅關注合意貸款規模,事實上也在逐漸關注利率期限結構,期望通過再貸款操作來引導市場短中期市場利率走向。
再貸款功能的擴展及其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央行再貸款工具的創新、抵押品范圍的擴充會極大地改變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在貨幣經濟學中,不同的理論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有不同的理解。例如,貨幣主義就認為從貨幣政策的調整到最終目標變動之間,就是一個“黑箱”;凱恩斯主義者則十分強調利率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核心作用。貨幣政策無論是對投資支出、消費支出還是凈出口的影響,都要通過利率水平的變動而發揮作用。至于利率變動到最終需求變動之間,則又衍生出了許許多多的理論解釋,例如,財富效應、信息不對稱及金融加速器機制等等。根據以往的貨幣政策理論,貨幣政策屬于總需求調控工具,從總需求到結構變動,則由不同行業、企業借款者,基于資本的邊際產出與銀行利率之間的比較而完成的。由此,貨幣政策雖被視為國家干預的工具之一,但貨幣政策在促進經濟總量均衡的具體實現過程中,則仍主要依賴于市場機制。在充分信息的市場環境中,貨幣政策影響利率總水平,利率的變化不僅能夠實現總量均衡,也能夠實現結構均衡。
然而,數十年的貨幣政策實踐發現,即便政府不斷地利用貨幣政策干預經濟,但經濟的周期波動并沒有因此而減少,結構失衡也總是伴隨著貨幣政策松緊的變化而發展甚至惡化,完全依靠利率機制,并不能保證資源被引導到政府所期望的行業和領域中去。現在,中國被廣為詬病的“貨幣一放松,資金就流向股市或房地產”、“資金脫實就虛”之說,就證明了傳統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存在明顯的“市場失靈”。正因為過去著眼于總量的貨幣政策在實踐中遇到了這樣那樣的結構性麻煩,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全球主要國家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實踐中,就不再單純依靠總量貨幣政策和傳統傳導機制,而采取更加靈活的、總量與結構并重的貨幣政策操作方式。中國再貸款工具的創新、擴充再貸款抵押品,就是著眼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缺陷而采取的大膽、有益的嘗試。
在一定程度上,再貸款工具的創新、合格抵押品范圍的擴大,縮短了貨幣政策向實體經濟傳導的鏈條,改變了傳統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具體地說,央行抵押品范圍的擴大,對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貨幣政策不僅保留了傳統的總量調控功能,也使它具有了結構調整的功能,因而縮短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傳統的貨幣政策傳導是由央行調整貨幣總量而影響利率,再經由利率來影響總需求與經濟結構的。央行擴大抵押品的范圍,依然會影響社會資金總量供給,并進而影響利率總水平。同時,央行通過調整再貸款的抵押品范圍,提高了被納入抵押品范圍的資產的流動性。這會降低其利率中的流動性溢價,降低其利息成本,同時也會使其更受金融機構的青睞,更多金融資源被配置到被納入到抵押品的領域中去。比如,央行將地方政府債券納入再貸款抵押品的范圍,就提高了地方政府債券對機構投資者的可接受性;央行將金融機構的小微企業信貸資產納入再貸款抵押品范圍,就會提高金融機構發放小微貸款的積極性,提高中小企業融資可得性。
第二,它不僅會改變流動性的總量結構,也會改變市場的流動性結構,從而影響市場利率結構。被納入到了央行合格抵押品的金融資產,其流動性會有相應地提高。2014年,中債登將低品質債券調出質押庫,結果造成了債券市場較為激烈的反應,根本原因就在于,這極大地降低了被調出質押品范圍的債券的流動性,其流動性風險溢價有所上升。反之,一種資產被納入到央行再貸款抵押品范圍,則提高了其流動性,使其利率中所包含的流動性溢價有所下降。因此,央行調整再貸款抵押品的范圍,會對市場利率結構產生一定的影響。例如,央行將地方政府債券納入再貸款抵押品后,地方政府債券的利率就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降低了地方政府債務的利息負擔。
第三,不斷細化的再貸款工具和抵押品范圍的擴大,使得央行的貨幣政策可以更好地發揮定向調控功能,減少對總量貨幣調控的依賴。2014年以來,政府就一直不斷強調定向調控。2014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后來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都強調要“更加注重定向調控”,就表明政府認識到了傳統貨幣政策手段及傳導機制存在的不足,因此,希望通過“定向調控”的方式,直接減少貨幣政策傳導的環節和鏈條,使貨幣政策更直接地發揮政府所期望的作用。央行定向調控的手段多種多樣,例如,定向降準、過去的定向央行票據都屬于定向調控的手段。實際上,相對于定向降準和過去的定向央行票據,如今的再貸款在央行的定向調控中更加靈活、針對性也更強。
在此,還需要強調的是,盡管再貸款功能的擴展和抵押品范圍的調整,使得貨幣政策的傳導更直接,也可以影響市場利率總水平與結構,但是,無論是流動性管理功能、結構調整還是引導市場利率結構變化,單單有再貸款是不夠的。再貸款要更有效地發揮流動性管理功能、引導利率總水平和利率結構,就需要協調再貸款與公開市場的使用。尤其是,貨幣政策要更好地引導利率走勢和利率(期限)結構,進一步完善中國的公開市場操作,尤其是搭配不同期限的國債甚至金融債券的現券操作,通過改變債券市場需求結構來引導市場利率期限結構。另外,在全球主要央行日益強調前瞻性指引的時候,應進一步提高我國央行再貸款操作的透明度,提升再貸款操作在公眾預期管理中的作用;再貸款作為流動性管理,應當更多地是為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提供緊急流動性援助,以防止市場流動性因個別金融機構的困境而枯竭。
(作者系第一創業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金融所貨幣理論與貨幣政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