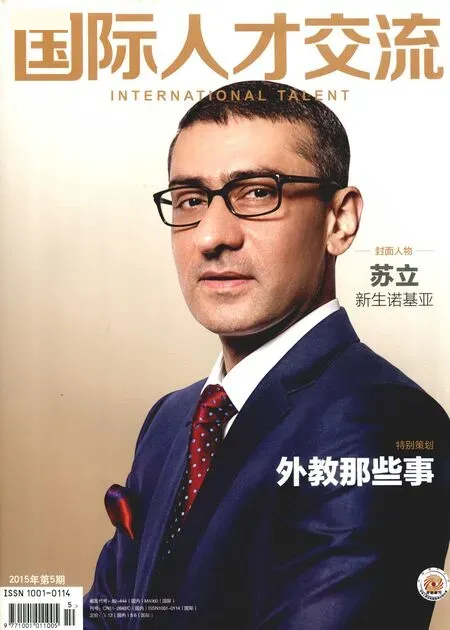歷史演變中的外國專家門診部
文/李蔚峰

愛潑斯坦先生在外國專家門診部取藥
北京友誼賓館位于北京的西北郊,因此在建館時被稱為國務院西郊招待所(第二招待所)。1956年3月9日由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定名,第二招待所改名為北京友誼賓館。建館初期,北京友誼賓館主要接待來自蘇聯幫助我國建設的各個行業的專家及家屬。當時賓館除了提供客房、餐飲、娛樂、購物、交通等服務之外,還設立了幼兒園、照相館、郵局、縫紉部等配套的服務項目。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項目當屬外國專家門診部,負責提供醫療保健服務。該門診部的前身是西郊門診部,隸屬中央保健局領導,業務上則掛靠在北京友誼醫院。門診部設于友誼賓館當時稱為南工字樓的一層和二層,設有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耳鼻喉科、皮膚科、口腔科、放射科、掛號室、候診室、化驗室、注射室、藥房等科室,當時大醫院有的科室,這個門診部基本上都有,而且設備在當時也算得上是一流的,可以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目的就是要為蘇聯專家及家屬提供良好的醫療保健服務。
新中國成立初期:成長
當時由于新中國成立不久,缺乏具有精湛醫術的醫生以及有護理經驗的護師,也由于語言上的溝通障礙,因此在這家門診部里,主要科室的主治醫生大都是蘇聯人,護士也大都由蘇聯人擔任。那個年代,中蘇友好已深入兩國人民的心中,所以,中蘇兩國的醫護人員合作得非常融洽,呈現出一派互幫互學、真心交流、感情深厚的友誼景象。蘇聯醫護人員在日常的門診中真心向中國醫生們傳授醫術,蘇聯的護士們則像親姐妹似的手把手地教中國的護士們如何護理病人。中國的醫護人員為了更快學到醫術和護理經驗,總是虛心地學習和請教,還利用業余時間學習俄語,提高交流能力。在中蘇兩國醫護人員的共同努力下,為來華工作的蘇聯專家和家屬提供了良好的醫療保健服務。1960年夏,隨著中蘇兩國政治關系的不斷惡化,蘇聯政府突然撕毀合同,撤走了所有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住在北京友誼賓館的蘇聯專家也迫不得已離開這里,在西郊門診部工作的蘇聯醫護人員也依依不舍地和中國的醫護人員告別返回了蘇聯。
蘇聯專家撤離友誼賓館后,其他國家的外國專家陸續搬了進來,主要是來自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如阿爾巴尼亞、民主德國、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等,當然還有來自拉美國家的一部分專家,但人數上遠遠不能與蘇聯專家相比。因此,西郊門診部的規模進行了縮減,門診部的面積從原來的兩層減為一層,可是為保證醫療質量,科室的數量并沒有減少,繼續承擔著為住館的外國專家及家屬的醫療保健服務,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期間,門診部的醫護人員依然堅守崗位,為住在賓館的外國專家及家屬們服務。
1976年,當唐山發生地震波及北京的時候,住在友誼賓館的外國專家和北京市市民一樣,在院內搭起了帳篷居住。那時正值炎熱的夏季,為防止地震后的次生災害,保證住館外國專家及家屬的身體健康,門診部的醫護人員夜以繼日地工作,白天他們挨個到地震棚查看每個專家的健康情況,給他們量體溫、測血壓、看心律,給患病的專家送藥、打針輸液等;夜里還要堅持值班,隨時為外國專家及家屬提供醫療服務。
80年代:發展
1980年開始,西郊門診部從原來掛靠友誼醫院改為掛靠北京積水潭醫院,并改名為北京積水潭醫院外賓門診部。主要考慮到友誼醫院離友誼賓館比較遠,交通也不方便,而積水潭醫院離友誼賓館比較近,外國專家如有急重病到那里去診治比較方便。2005年辭世的著名的國際主義戰士,伊斯雷爾·愛波斯坦及其家人曾經受到過門診部醫護人員的醫療保健服務二十多年,對那里的服務深有感觸。在他寫給國家外專局和國管局的一封信中,他是這樣評價門診部的:“自從50年代外國專家局建立以來,門診部為外國專家做了大量的有價值的工作。每當出現危急和傷殘等危及生命的情況,在這里都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轉危為安。門診部的醫護人員一直在幫助專家們保持健康,負責每年為他們體檢,對他們的健康狀況做詳細的記錄,以便觀察比較他們每一年健康方面所發生的細微變化。對于那些行動不便的老專家,門診部制訂了一系列的定時上門送診服務,通常是每周為他們量血壓做記錄、檢查心肺功能等。當他們的身體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異常跡象時,會得到及時的提示和治療。門診部為所有外國專家和他們的家屬都提供了及時和有效的醫療保健服務,包括接種各種防控疫苗,特別是對他們的子女們更是這樣。”
正如愛老所說的那樣,門診部的醫護人員的的確確為外國專家及家屬提供了家庭式的親情化醫療保健服務。今年已經年近100歲的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外國老專家伊莎白和她已辭世的丈夫柯魯克以及她的3個兒子柯魯、柯馬凱和柯洪剛雖然不住在友誼賓館,而是住在離賓館很近的北外家屬樓,但他們還是常常花十來分鐘騎著自行車來這里看病。她的二兒子柯馬凱回憶道,他父親到了晚年,身體不好,哥仨經常帶著父親來門診部看醫生,因為要去協和醫院路途太遠,交通也不便。柯馬凱本人小時候腿不太好,骨頭出了點問題,他自己經常騎著自行車來這里看醫生進行理療,醫生和護士阿姨對他都態度特和藹,至今回憶起那些往事,今年已經六十多歲的柯馬凱依然心存感激之情。我國著名的翻譯家、文學家楊憲益先生和他的英國妻子戴乃迭生前在友誼賓館居住了很長時間。戴乃迭在晚年的時候患病,臥床不起,門診部的醫護人員幾乎每天都要去家中看望她,為她進行必要的醫療護理,直到她住進醫院的特別護理病房。還有已經離世的美國老專家陳必娣、奧地利老專家魏璐詩、日本老專家土肥種子、川越敏孝、河野八重子等都曾在生前患病期間得到了門診部醫護人員的特別照顧和精心護理。每次這些老專家的子女來友誼賓館都會到門診部去看望那里的醫護人員,對他們給予他們父母的關心和照顧表示感謝。

門診部的醫務人員正細心為外國老專家做檢查
門診部除了承擔為住館外國專家及家屬的醫療保健服務之外,由于歷史上形成的原因,他們還承擔過為中國科協、外專局的工作人員、賓館的員工和家屬以及住館的其他內外賓客的醫療服務。像科協的一些知名科學家:華羅庚、牛滿江、盧嘉錫、王大珩等都在來賓館開會或參加活動時,到門診部看過醫生。賓館的員工們更是“近水樓臺先得月”,老一點的員工依然記得,他們無論是在工作時受傷還是有點頭疼腦熱的都會第一時間到門診部去看病,有時甚至還會把他們的子女或父母帶到這里來看病。在他們眼里門診部就像是賓館的職工門診部似的,醫護人員不但醫術高超,手到病除,更主要的是他們態度和藹熱情,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樣。
另外門診部還承擔著國家外國專家局的一些重要任務。那就是每年春節前中央或國務院領導與外國老專家座談、向外國專家頒發“友誼獎”、重大節日前舉辦歌舞晚會、音樂會等,門診部都要派醫護人員相隨,以確保外國專家的人身安全。特別是從5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為了保障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以及其他國家來華工作的外國專家的身體健康,每年暑期都會組織外國專家和家屬到避暑勝地北戴河休假療養。門診部的醫護人員隨著住在友誼賓館的外國專家來到北戴河外國專家休養所提供醫療保健服務。他們堅持每天到外國專家的別墅樓巡診,特別要為外國老專家進行例行的身體檢查。他們每天頂著高溫,冒著酷暑在海邊值班,別人都可以下海暢游,納涼消暑,或到海邊散步,享受大海帶來的快樂,可他們卻要堅守崗位,確保在海里游泳的外國專家的人身安全。很多時候外國專家特別是他們的孩子在游泳時不慎被海里的石頭把腳扎破了,有時甚至被海蜇蜇傷了,都會得到在海邊值班醫護人員的及時救治。有他們在,外國專家和家屬就沒有了后顧之憂,可以安心休假了。
90年代:改革
到了90年代,隨著我國醫療制度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來這里看病的中國人也隨之減少,由于門診部一直從事著為外國專家提供醫療保健服務的原因,也是為門診部未來的服務對象進行明確定位,因此后來門診部改名為外國專家門診部,一直沿用到現在。雖然名稱改了,但是他們依然和以前基本上一樣,重點是為住館的外國專家服務,在遇到突發事件時,他們仍然會挺身而出。1994年,臺灣蔣經國的三子蔣孝慈,時任臺灣東吳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來京參加一個交流活動,住在友誼賓館貴賓樓,一天在房間突發中風,無法動彈,當時值班的蘇平大夫及時趕到他的房間,進行必要的處置,防止其病情加重。隨后又及時將他送到大醫院,避免了重大意外事故的發生。
外國專家門診部的醫護人員為外國專家的醫療保健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是他們的待遇卻與他們的付出不成正比。從最初掛靠在友誼醫院到后來掛靠在積水潭醫院,雖然業務上歸兩所醫院管理,但是門診部醫護人員的待遇與那兩所醫院醫護人員的待遇卻有著非常大的差別。無論從工資收入、到獎金的發放,甚至是在職級的提升,以及分房子等方面,都相差甚遠。但是門診部的醫護人員把為外國專家服務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他們一直認為,為外國專家服好務就是在為我們國家引智工作、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作貢獻。因此幾十年以來,他們都在辛辛苦苦地、默默地奉獻著自己的青春年華。
21世紀:堅守
2004年由于中國政府相關部門放開了對在華工作的外國人居住地的選擇權,他們可以在任何地方租房或買房子居住,取消了原來外國人只能住在允許接待外國人的賓館或公寓的規定。住在友誼賓館的外國專家除了由中國政府出資在外購房的外國老專家之外,其他的外國專家也都紛紛搬出了友誼賓館,在離他們工作較近的地方或他們喜歡的地方租房或買房居住。住館外國專家的數量由50年代的一千多人,到六七十年代的數百人、再到八九十年代兩三百人,而到了2004年只剩下了三十多人,到目前僅剩下不足十人。
由于外國專家住館人數的減少,外國專家門診部所屬的上級領導曾有過撤銷該門診部的想法,但是在外專局、國管局、北京市衛生局、積水潭醫院和友誼賓館的共同協商下,考慮到友誼賓館當時還有兩戶日本老專家生活和居住,另外還有幾戶來自中央電視臺和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外國專家在館居住,因此外國專家門診部仍然要繼續保留并做好醫療保健服務。雖然只有幾戶外國專家,但是他們的工作量沒有因此而減少許多。因為有一對日本老專家夫婦,先生叫森新一,今年已經98歲,夫人叫森洋子也已過90,而且倆人膝下無子女。醫護人員每周定時來到他們的房間為他們進行身體檢查,發現問題及時診治。特別是先生患有眼疾,一只眼基本上已經失明,而且患有老年性的焦慮癥,經常無故發脾氣,每次一發脾氣不是不吃飯了,就是拒絕用藥,甚至做出一些過激的行為。每次都是醫護人員趕到房間,對他進行心理疏導。有時是在半夜的時候發生這樣的情況,醫護人員也總是會來到他的房間進行說服和勸慰,從不叫苦叫累。賓館的服務人員笑稱:“專家門診部的醫護人員都成了他們夫婦倆的專職特護了!”
在外國專家門診部醫護人員的精心護理下,目前夫婦倆的身體狀況都有所改善,享受著晚年生活。當然兩位日本老專家都已進入人生的最后的里程。我想隨著住在友誼賓館的這兩位僅有的日本老專家的離去,外國專家門診部也就到了它使命的終結之時,我衷心地希望即使時光流逝無情,我們都不應當忘記那些默默地為外國專家服務的醫護人員,永遠記住他們用青春年華所譜寫的為外國專家服務的贊歌!(本文部分內容系采訪已退休的外國專家門診部蘇萍大夫所得,謹表感謝!)

作者(左二)與門診部醫護人員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