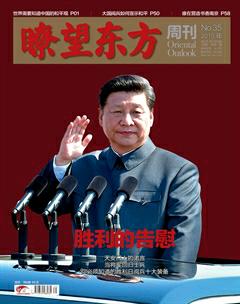怎樣治霾,才能收獲“常態藍”?
水灑風吹式治霾是“塔西佗陷阱”
張愛軍(遼寧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博士生導師)
有評論人士稱,中國人還得忍受霧霾至少三十年;也有部分地方官員則說,治理霧霾幾年內即可告成。需要警惕的是機會主義、臨時抱佛腳式的治理霧霾方式。
治理霧霾不能靠風吹水灑。前有北京拿PM2.5區域傳輸占比吐槽:說河北和天津“污染”北京,而河北卻說霧霾最嚴重的春冬兩季盛行北風,污染物其實是從北京吹來的;其后還有嚴重缺水城市鄭州靠灑水治理揚塵的傳聞。盡管這些議論離嚴肅的科學探討上有距離,但至少說明,城市的治霾方式是否有長遠戰略目標,已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要警惕掉入“塔西佗陷阱”。2014年初,有超九成省份的政府工作報告涉及空氣污染治理,至少15個省份簽訂了治理霧霾、力保藍天的“軍令狀”,但效果呢?如果讓治霾承諾流于政治豪言卻不能實現,政府公信力無疑將受到傷害。
有觀點認為,霧霾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必然付出的代價,只要是經濟發展了,即使帶來霧霾也是值得的,而且也來得及去治理。但從目前的現實情況看,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發展伴生的次生災難越發嚴重,所以要求發展和治理思路必須改變。
要轉變政績觀,從以GDP為導向轉變為以人為本、以生命為本、以尊嚴為本,經濟發展是為了國民福祉,如果國民生命健康因此嚴重受損,經濟增長就喪失了意義。
超越“塔西佗陷阱”,破除GDP迷信是關鍵,科學民主決策是前提。要完善重大行政決策“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和集體討論決定”的程序規則,使公共利益在政策內涵中得到充分體現。
依法治污就可“理直氣壯”
潘林青(媒體從業者)
今年2月初,山東省臨沂市為解決大氣污染突出問題,依法對500家企業實行停產整治或限期治理,目前已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不過,臨沂這一“鐵腕治污”做法也引發了不少質疑,比如“治污影響百姓就業、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
“怎樣治污”是個大問題。如果地方政府“做樣子”,人民群眾就會有意見;如果地方政府“動真格”,污染企業就會受不了。手心手背都是肉,決策該如何取舍?藥輕了不治病、藥猛了治死人,發力該如何適度?
看上去“兩難”,其實并非無解,答案就是“依法”兩字。近年來我國出臺了新環保法等多部與環保相關的法律法規,何為污染、誰來監管、如何防治、如何處罰等方面規定已經很清楚,地方政府只需據此執行即可,不必瞻前顧后、羞羞答答。
但在現實操作中,即便依法依規,仍可能招來質疑和不滿:一是有的地方政府執法過程簡單粗暴、知法犯法,侵犯人民群眾合法權益;二是地方政府無過錯,但治污損害了污染企業等既得利益者利益,引發他們罔顧法律強烈反彈,比如制造虛假輿論混淆視聽、組織工人對抗執法等。
這就需要區別對待。對于第一種情況,地方政府要及時“糾偏”“改過”,依法補償相關人員的損失;對于第二種情況,地方政府要有“啃硬骨頭”的勇氣,堅決打擊污染企業藐視甚至對抗法律的囂張氣焰,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和公正性。
一言以蔽之,執法要“一把尺子量到底”,真正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與此同時,也要在法律法規允許的范圍內,保障好因污染企業關停而下崗的職工等群體的利益,減少治污帶來的“陣痛”。
國際經驗表明治污對經濟有帶動作用
張樂偉(河北某地級市公務員)
十八大以來,中央對生態文明高度重視,新《環保法》的實施讓環保執法有了“牙齒”。
有地方環保干部稱,環保工作從政治、經濟和輿論三個角度來說,壓力都是“超常態”的。這個說法并不為過。
一種輿論壓力在于如山東省臨沂市的“休克式治霾”會否導致人仰馬翻?急踩剎車會不會使得民生受困?陣痛肯定會有,但也不必過分夸大。從國際經驗來看,采取防止污染的措施對經濟還有帶動作用。
例如,1974年日本迎來排煙脫硫投資額的頂峰,有數據表明如果這個措施推遲10年,大氣污染受損額將增加12萬億日元,而GDP增加額將減少6萬億日元左右。次年,日本公害對策投資占設備投資約18%,占GDP6.5%,防止公害的機械制造業生產額則達到7000億日元。
治不治已不再有分歧,必須治;怎么治卻尚缺共識。
鄭州“灑水治霾”經媒體曝光后,城市管理局被指飲鴆止渴,揚湯止沸。其實把治霾不力的大帽子扣在環保部門一家頭上,他們不免覺得委屈;而臨沂500家企業限產減排的大動作背后,必然站著一個強有力的地方政府。
所以,要有明確的分工使各政府部門權責更加明晰,最大可能避免監管死角和出現事故后的相互推諉現象;要以詳盡的法律法規有效分解治污工作中的各個環節,形成完整鏈條,讓治理污染不再成為環保部門的“一家之事”。
同理,問責的范圍應進一步擴大,治霾不能靠環保部門“單打獨斗”,問責制度需要讓經濟管理部門主動分擔環保監管職責,各級政府更應成為問責重點。
給敢斗硬的環保部門更多權力
謝德體(全國人大代表,西南大學資源環境學院院長)
2015年,此前地位頗為尷尬的中國環保部門“動起了真格”。盡管治理污染不能僅靠環保部門,但一個強有力的環保部門對于環境保護的意義不言自明。
在我看來,如果想確保環保高壓不是一陣風、讓環保部門挺直腰桿成為常態化,那么就 需要從兩方面著手:一是要政府重視,二是要嚴格執法。
政府重視,不僅僅是思想意識上的重視,更需要將環境保護納入到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成為一種制度。
發展不能只追求表面數字的光鮮,而應該是一個綜合指標,目前迫切需要重新制定新的發展評價體系并將環境保護納入進去,用這樣的標準去衡量一個地區或者全國的發展水平。
要把環境保護納入到干部考核當中。干部升遷如果只考核GDP,領導干部考慮的可能就只是“大干快上”搞工業,如果把環境保護納入干部考核,環境污染地區的領導干部將被問責,領導干部們就會有所顧忌。
環保部門是政府的一個組成部分,政府重視了,環保部門監管才能夠不受干擾,才能夠嚴格執法重拳治污。
環保部門要嚴格執法,首先需要賦予其相應的權力。以前環保部門為什么說話不算數,因為它缺“牙齒”,“咬人”不疼,罰款數額小、監管手段有效。新《環保法》的出臺就是給了環保部門執法的權力和利器。
同時,嚴格執法還需要環保部門敢于斗硬,善于啃硬骨頭。不少污染企業是地方的納稅大戶,這就需要環保部門要有膽識,排除困難秉公執法。
環保是全社會的事,而不是環保部門的“一家之事”,治理環境也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盡管工作千頭萬緒,但理順環保機制、進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是第一步,只有政府重視、環保部門敢于執法,全社會的環保力量才能被有效調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