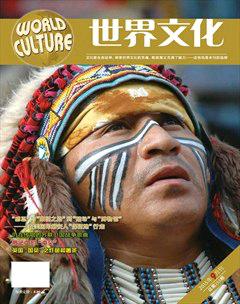弗雷·奧托:不否認自己是理想主義者
李忠東


2015年3月9日,德國著名建筑師弗雷·奧托( Frei Otto)去世,享年89歲。僅一天后,3月10日,普利茲克獎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組委會正式宣布將該獎項頒發給他。按慣例,奧托應在5月去邁阿密接受頒獎。但是普利茲克獎執行董事瑪莎·索恩在他病情危重時趕到他家提前告知了這個消息。奧托很高興,對普利茲克評審團和組委會表示感謝,雖然獲獎并不是他的人生目標。
普利茲克獎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這種情況,但這是奧托對建筑界的研究和貢獻得到廣泛認可的必然結果。
“奧托的職業生涯堪稱世界建筑師學習的范本,他對于國際建筑界的影響也勢必會一直延續下去。”普利茲克基金會主席湯姆·普利茲克表示,“驚悉他去世的消息,我們深感悲痛。評審團能夠在他生前給予他這項榮譽,我們感到非常欣慰。”
普利茲克獎被譽為“建筑學界的諾貝爾獎”,在業內備受關注。它1979年由普利茲克家族的杰伊·普利茲克和他的妻子辛蒂發起,凱悅基金會贊助,是每年一次頒給建筑師個人的獎項,以表彰獲獎者在建筑設計創作中所表現出的才智、洞察力和獻身精神,以及其通過建筑藝術為人類及人工環境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貢獻。每年約有500多名從事建筑設計工作的建筑師被提名,由來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建筑師及學者組成評審團評出一個個人或組合。從1979年至2015年,普利茲克獎已頒給40位建筑師。對于世界上的建筑師而言,獲獎意味著至高無上的終身榮耀。
普利茲克獎評委會主席彼得·帕倫博將奧托稱為“現代建筑的巨人”,解釋說該消息之所以突然提前發布是因為他不幸去世。評審團這樣評價道:“在奧托的一生中,創造了很多非常有創意的、令人驚奇和前所未見的空間和結構。他讓人們開拓了眼界,給世人以深遠的影響:不是留下讓人參考復制的形式,而是通過他的研究和發現帶給人們通往新路徑的方法。奧托對建筑界的貢獻不僅僅在于他的技能和才華,還有他的慷慨。他富有遠見,不斷探索,毫不吝嗇地分享他的知識和創意。他團結協作,致力于資源集約利用。基于此,2015年普利茲克獎頒發給奧托。”
“我的建筑設計理念是希望創造更多可以對窮人進行幫助的新型建筑,尤其是那些遭受了自然災害和重大災難的人們。”奧托去世前曾經表示,“對于我來說,比獲得這項大獎更重要的是竭盡余生繼續去完成我正在做的事情。”
奧托認為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我們應該建造的是和自然界共生的社會。他認為這里指的自然界是廣義的,包括了無生命、有生命和已經死去的,這個觀點和中國“天人合一”的哲學十分相似。奧托對自然的規律非常重視,想方設法從里面尋覓到適用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通理,從形而上的高度來理解和思考建筑。他從20世紀60—70年代開始饒有興趣地研究仿生建筑,并且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整體”的觀點。
這位建筑大師的思想已經超出了單純的建筑范疇,他的理想是用最少的資源和最合理的建筑來構建世界。“世上美的建筑很多,但好的建筑就少多了。”他指出,“一個設計者同時也應該是一個好的人類學家,對人類文明的進步起很好的輔助作用。建造房屋,不僅僅是給人們提供住所,更是在輔助人們找到適合自己的生活重心。”
有一次,為了迎接柏林愛樂樂團在柏林總統府花園3個小時的演出,奧托和他的團隊用了大半年的時間設計舞臺的棚頂。他在演出后對記者說的一段話至今令人記憶猶新——“我對會永久存在的東西不感興趣,我此類作品并不多。同樣的,在那些永久的、可以作為紀念碑存在的建筑上刻自己的名字,我也非常不喜歡,那會讓人很不舒服。我對那些只能短暫存在的設計情有獨鐘,或許我要為之付出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的時間去準備,但在作品呈現的那一刻,我是如此幸運。”
奧托在建筑領域率先提出并運用環保可持續性、節能、設計技術、高效等理念,他的帳篷與皂膜、充氣結構與液體結構、懸掛結構、反向懸掛結構、網殼結構和分子結構等在實際項目中一次次得到實施和驗證。奧托推出的輕型建筑創造了一個新的空間實現形式,為建筑帶來更好的發展。
推崇輕型材料和整體建筑
奧托1925年5月31日出生于德國西格瑪爾,在柏林長大。在父親和祖父都是雕刻家的家庭中,他很小便開始接觸裝飾和結構。據說他的名字“弗雷”是母親參加了一次關于自由的講座后給取的,“弗雷”在德語中意味著自由,她相信這個名字會給孩子帶來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
小奧托心懷當發明家的夢想,對從縫紉機到飛機模型的所有東西都興趣盎然,愛不釋手。15歲那年,他在中學老師的幫助下開始接觸滑翔機并于同年通過滑翔機考試領到執照,在對滑翔機的學習中第一次接觸了空氣動力學原理和拉膜技術。除此之外,他還喜歡制作飛機模型,這對后來的張力結構設計很有影響。
奧托1943年考取柏林工業大學建筑系,但學業因“二戰”爆發被迫中斷。他應召入伍,經過一年的飛行訓練后于1944年成為一名殲擊機飛行員,被送往前線。“二戰”結束前在德國紐倫堡附近被捕,成為戰俘,先后在美國和法國的戰俘營待過。
在戰俘營里,奧托被任命負責規劃整個營區的建筑分布。因為除了帳篷沒有更多的其他建筑材料,所以必須盡可能地對有限的資源加以利用,搭建出所有可能會用到的房屋。它們經濟實用,可拆卸性強,并且隨時都能被移動。他對人生中的這段重要經歷終生難忘,這讓他接觸到很多價格低廉的輕型材料,學會了如何從資源極其匱乏的狀態中無中生有,摒棄陳規,突破創新,認識到山窮水盡其實為柳暗花明提供了重要的機會。
奧托1948年回到柏林工大繼續自己的學業,學習了與現代建筑有關的音樂學、生物學、人類學、歷史學課程和現代藝術史。1950年,他成為戰后第一批獲得資助前往美國留學的德國青年。這位年輕的建筑師在美國結識很多同時代的建筑學家,參觀了弗蘭克?勞埃德?賴特、密斯?凡?德?羅和理查德?努特拉等很多著名的建筑師工作室。他尤其對美國設計師馬修·諾維奇為北卡羅萊納那州設計的多頓競技場印象深刻,馬上被它網狀的屋頂結構所吸引。馬修的這種結構設計正是奧托當時研究的課題,他從中受益非淺。
在美國學習了半年之后,奧托重新回到柏林攻讀博士學位,潛心研究輕型材料和整體建筑。“我那時經常會思考建筑與自然的關系。自然是很容易被摧毀的,不單單是通過戰爭,不和諧的建筑對自然來說也是一種破壞。如何通過比較自然的方式,使建筑的內在與外界環境達到和諧統一,是我要研究的課題。”奧托在接受采訪時說。
他1953年發表博士論文《懸掛的屋頂》,著重探討了如何利用網狀結構和拉膜技術,實現建筑內部構造與外部環境的統一。論文在建筑界迅速引起極大的反響,給很多人帶來了啟發。“奧托帶領我們回到了人類歷史早期,那是一個把帳篷當做居所的年代。”斯圖加特輕型材料研究所的一位教授評論道,“帳篷是最早期的人類房屋形態,它具有恒溫、可移動、靈活性強、牢固、美觀、實用等特點,這種建筑形式是奧托整體建筑理念很重要的一部分。”

奧托1954年獲得柏林工大土木工程學博士學位,在斯圖加特市郊沃姆布昂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直到去世的前一天,這位建筑師和工程師一直在那里為建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工作。他為離工作室不遠的工作車間起了“破爛的小木屋”綽號,在這個自己的“烏托邦”里,各種建筑模型、圖紙、材料以及一些簡易的物理實驗設備隨處可見。奧托喜歡動手做實驗,以便糾錯和尋找平衡,直到發現合適的材料。他不滿足于建造房子,更喜歡從形而上的高度來理解和思考建筑。奧托一生中獨立完成的建筑屈指可數,更多的是給予別人一些設計上的想法,使他們的設計能夠成為現實。
主張人、建筑和自然合一
作為奧托的成名之作,1972年慕尼黑奧林匹克競賽場是他與著名德國建筑師君特·貝尼斯的團隊共同完成的。在他的工作車間,至今還能看到部分當年使用過的模型,其中包括女性絲襪。正是貝尼斯團隊的設計師弗里茨·奧爾用自己夫人的絲襪作為輔助材料制作模型,才使他們的設計方案從一百多份投標書中成功勝出。
組委會開始時對這一方案中提出的“空中纜索網頂棚結構”持懷疑態度,覺得整個設計不現實,數據不完善,預算也不可估計,根本不可能被建造出來。為此,貝尼斯向專攻輕型結構研究的奧托求助。他們通過一次次的物理實驗,重新修訂數據,精心選擇建筑材料。在沒有運用任何高科技運算系統和建筑設計軟件的情況下,使這一方案完美實現,至今仍被人稱頌為建筑史上的“奇跡”。
不同于1936年納粹時期奧林匹克場館以磚石筑成的厚重屋頂,1972年慕尼黑奧林匹克競賽場打破傳統體育場封閉單一的形象,開拓性地使用了輕型拉膜結構的棚頂,創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開放性、輕盈、新型的建筑結構。新型的半透明帳篷式設計詮釋了人們與自然溝通的渴望,場館流線型的線條自然流暢地與奧林匹克公園成為一體,向世人展示了一個民主樂觀的新德國。1972年這里曾舉辦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1974年舉辦世界杯總決賽。1975年,奧托在曼海姆音樂廳創造了輕量構造建筑多功能廳。他利用這些作品,向人們傳達了人、建筑、自然合一的理念。
在此之前,奧托在很多建筑上面嘗試過使用輕型拉膜結構的頂棚設計。例如,20世紀50年代中期為卡塞爾國家園林展設計音樂廳,60年代為不萊梅圣·盧卡教堂設計頂棚,1967年完成的蒙特利爾世博會德國館設計……當時,他的確成為建筑界談論的焦點。然而正是奧托開創的輕體結構,使我們看到人類并不一定需要用臃腫的結構把自己和自然隔離開。
奧托1961年在柏林工大創立了研究方向為“生物學與建筑”的研究機構,以推動輕型材料和拉膜式結構在德國的研究與應用。1964年,他受斯圖加特大學的邀請協助創立輕型材料研究所并擔任所長。奧托時常和學生們一起探討一些有關人類學和建筑學的問題: “建筑到底是什么?”“如何看待那些古建筑?”“它們向我們傳達哪些思想?”“究竟什么樣的房子適合人類居住?”“怎樣用輕型反對野蠻?”他希望通過探討這些問題,使年輕一代的建筑學者認識到一個設計者同時也必須是一個好的人類學家,應該對人類文明的進步起很好的輔助作用。建造房屋不僅僅是給人們提供住所,更是在輔助人們找到適合自己的生活重心。
奧托經常對他的學生開玩笑地說,自己身體里有一種“建筑基因”,這種基因促使他用畢生的時間去實現自己的夢想,直到生命的盡頭。在這位建筑大師心中,始終有一個烏托邦:水源充足干凈,鮮花四季開放,終年綠意盎然,常年氣溫18~28°C。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像《圣經》描述的那樣,過著與大自然相親的生活。
“很多人說我是個理想主義者,對此我并不否認。但是我更關注的是數據和結構這些更為具體的東西,是使用何種節能的材料和采用什么樣的方法才能讓這個未來的城市成為現實。”他批評道,“越來越多的設計者現在將設計重心放在房子的外觀上,我不知道該如何評價。但人類的需求是多種多樣的,不會總停留在膚淺的表面。”
盡管奧托晚年視力急劇下降,但他的工作熱情絲毫不差,用畢生的時間和精力去實現自己的夢想,直到生命的盡頭。“失去了視覺的輔助,反倒能讓我更專注于房屋內部更深層次的東西。”他不無幽默地說,“很多以前沒有看到,或者由于表象被忽略的細節,反倒在腦海中被放大了。失去了視覺,我進入到了一個更為廣闊的建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