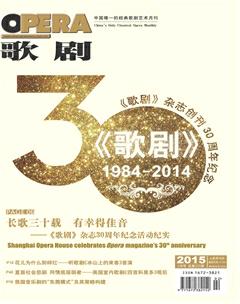溫熱的回眸
崔亞玨



上世紀60年代,被譽為“中國第一部
反特驚險抒情片”的《冰山上的來客)》上映后,片中的插曲《花兒為什么這樣紅》、《懷念戰友》等與電影一道,雙雙成為了中國電影史和音樂史上的經典之作。劇中戰士阿米爾、真假古蘭丹姆和楊排長等人物形象更是家喻戶曉,深入人心。一般說來,歌劇與電影之間的聯系,也多是經由舞臺上的歌劇演出錄制的影片,而后再呈現于影院、大銀幕等放映場所和載體之上。而這次的歌劇《冰山上的來客》卻從經典銀幕中躍然于歌劇舞臺之上,成為一次充滿懷舊味道的“逆向選擇”。
此次首演的歌劇版本,由以往在其他歌劇中通常的“中外組合”變成了“漢疆組合”,由來自新疆的女高音迪里拜爾領銜,且由維、漢兩族歌唱家共同呈現。觀演前對于這次的歌劇版本,在一番期待之余也抱有些許疑問,相對于電影中的蒙太奇或是對于細節的捕捉,歌劇版本如何表現那些深入人心的場景和片段,音樂語言如何表達當中的經典臺詞與唱段,電影中那些外景拍攝的畫面如何在舞臺空間的限制之下呈現?
由現場觀演來看,作曲家的二度創作著力于刪繁就簡,加強音樂的戲劇性、抒情性,電影中的歌曲作為主線,同時還有一些新創作的具有塔吉克民族音樂的旋律。此外,歌劇也充分利用重唱與合唱的“先天之利”,在同一時間和空間展現人物的表現和內心。
序幕首先由一段女聲合唱引入,展現塔吉克人的生存環境和內心期盼。江罕達爾匪幫讓詐死在人群里的古麗巴爾冒名古蘭丹姆留下執行任務。隨著一幕一場的歡慶場面開始后,遼闊寬廣的引子展現了我國西部高原冰峰的雄奇和開闊,當手鼓鮮明的節奏出現,濃濃的塔吉克音樂中,主人公阿米爾和新娘子假古蘭丹姆登場。人們合唱來為尼牙孜老漢的兒子娶親慶賀。當歡樂的人群散去,遠遠傳來的女聲合唱響起了“花兒”的旋律,表達著阿米爾內心的煩惱和獨白:“已經過去了多少年,這熟悉的歌聲啊,還留在我心間……”一班長則問起新娘的來歷,此時五重唱展現了不同人物的內心活動——阿米爾得知她的名字后不禁感嘆命運的殘酷安排,假古蘭丹姆一陣緊張唱道:“心兒已不能平靜。”楊排長則疑惑道:“已經發生的事情是這樣難忘,有多少疑問留在人們心上。”為情節旋律的展開埋下了伏筆。
這邊廂,駐地周圍滿是白楊樹,戰士們唱起了一曲“家鄉進行曲”,楊排長則開始試探假古蘭丹姆,讓阿米爾唱起旋律,但假古蘭丹姆的毫無反應讓楊排長思慮:“本該是她記憶中的樂曲,她究竟是什么人?”而假古蘭丹姆則唱起了內心的掙扎:“……雖然這里也有歡樂,但都不屬于我。男人們的戰斗為什么總要女人做犧牲……”
二幕場景開始后,江達爾汗隱匿在黑暗中與“真神”密謀“先拔掉冰封哨卡”的陰謀。女奴邁瑞烏麗在河邊取水,唱起一曲<帕米爾紅花》。隨后,她與卡拉在此相遇唱起了那曲極盡悠揚的《冰山上的雪蓮》,強烈的抒情性與隨后卡拉犧牲的悲壯場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偽裝的真神請求卡拉幫助少女逃離匪幫,在風雪夜行的路上,四重唱《今夜沒有星光》,四個聲部交織在一起,唱出了四個角色各自的內心活動,真古蘭丹姆抒發著將要回到故鄉的喜悅和憧憬,卡拉鼓勵著她:“只要勇敢追求沒有飛不過的高山。”阿曼巴依則蓄謀著黑暗和死亡,而江達爾汗擔心假古蘭丹姆將會被識破特務身份。卡拉中槍后對真古蘭丹姆唱道:“年輕的姑娘啊,我們還是太年輕!”此時,晌起雄壯的弦外之音,再現“高原之歌”。
在第三幕當中,暴風雪之夜在擊退匪徒之后,趕赴哨卡增援的楊排長、尼牙茲和戰士們,發現了遇難的納烏茹茲,楊排長呼喊“一班長”并向天鳴槍,這場戲也是全劇人物關系發展的關鍵和情感的高潮部分。此時“懷念”的主題晌起,男高音獨唱與混聲合唱歌曲《懷念戰友》增加了聲音的厚重感與情感的濃烈度,16分音符的弱拍起,起始的極度憂傷情緒反襯出最后的情感的爆發與宣泄。
如果說一曲憂傷而浪漫的“花兒”的多次反復出現為全劇增加了不可缺少的風情,那么《懷念戰友》則稱得上是全劇的靈魂。阿曼巴依帶著真古蘭丹姆來到邊防排,真假古蘭丹姆相遇,楊排長看到卡拉托真古蘭丹姆轉交的情報,知道了卡拉的死訊后心中波瀾起伏。電影中的人物刻畫只是通過鏡頭中楊排長看著斷了琴弦的熱瓦普時表情和行為的特寫,來表現他的悲憤和無奈。而在這次的歌劇中,作曲家為楊排長也安排了一首男中音詠嘆調《卡拉,你在哪里》,前奏再現了卡拉臨死前扯斷的熱瓦普琴弦聲。詠嘆調伴奏中再現了“冰山雪蓮”和“懷念戰友”的主題。詠嘆調在原電影歌曲的基礎上充分展開和變化,增強了戲劇表現的張力。
楊排長令阿米你再唱“花兒”,真古蘭丹姆聞聲唱和,瞬間溫情爆棚,楊排長“適時”的一句:“阿米爾,沖!”更是收獲了觀眾們真摯會心的笑聲與熱烈的掌聲。在全劇的尾聲,巴洛托節叼羊比賽開始,塔吉克人歡快地唱著《勇士之歌》,其中的五重唱,五個主要人物各自不同的心理,層層遞進,和大合唱交融在一起。五重唱巧妙地把高原之歌的主題和勇士之歌的主題并行,塔吉克典型的7/8節奏中充滿了活力和動感。敵人最終陰謀破滅,冰山腳下,一班長、卡拉、納烏茹茲的形象再次清晰,雄壯的終曲響起:“祖國的好兒女,光榮啊塔吉克的雄鷹!”
除了歌劇本身的音樂之外,原來的歌詞中,白楊樹、紅花、冰山、雄鷹成為歌劇“象征”意味表現的源泉,導演充分利用舞臺美術對于電影進行一種延伸,將銀幕形象變成了空間審美,“冰山”在燈光和多媒體的配合下閃現光澤,突出了表演藝術的形式感,還有熱鬧的塔吉克族婚禮、巴洛托節叼羊比賽等民俗展現,同時也依靠演員的表演把人物的感情、心理空間表達出來,使得劇情呈現和人物形象更加立體。那朵在歌詞中“象征著純潔友誼與愛情”的紅花,在真古蘭丹姆和阿米爾重逢之時不僅由多媒體在舞臺背景投映鮮艷的紅花,而且在舞臺地面上也有一簇簇嬌艷的紅花從臺側漸漸“生長而出”,一直延伸到舞臺中央,凸顯了從電影到歌劇,從畫面走向空間的象征性的視覺主題。
如今,當我們有幸再次聆聽這些經典的旋律之時,或許最應該追憶與感謝在特殊年代那些堅持創作理想的藝術家們做出的“逆向選擇”。遙憶1961年,《冰山上的來客》在開始投拍之后沒多久就因為多種復雜原因停拍了,大隊人馬返回長春電影制片廠之后,許多導演都不敢接下拍攝任務,而導演趙心水卻在此時勇挑“重擔”,之后他一邊到新疆去收集資料,一邊和編劇白辛重新構思改動劇本,作曲家雷振邦也是幾經輾轉后來到新疆南部塔什庫爾干地區采風,里面的那首優美的“花兒”便是根據當地音樂“古麗碧塔”的旋律創作而成,這首歌曲在劇情的嚴酷背景下顯得分外“小清新”,也因此讓人格外難忘。而就是這樣一部凝結著藝術家智慧與情懷的優秀作品,卻在1963年上映后很快成為被批判的對象,導演、編劇、作曲、攝影都被“打倒”,他們幾人甚至失去了在影片開頭字幕中出現名字的機會,其中編劇白辛更是因創作《冰山上的來客》劇本被江青點名,于1966年在松花江邊自殺身亡。但是,政治與藝術的不同就在于:“拿破侖死了,而貝多芬卻永遠活著。”經典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便矗立在那里,令一代又一代人回眸和仰視。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他們那一代人曾用“青春血液澆灌”的美好情懷依然在人們心中縈繞,影片中的歌曲更是深入人心,成為了經久不衰的“國民金曲”。當今時代,我們早已遠離“偵察與反偵察”、“圍剿與反圍剿”這樣的革命年代,生活的節奏和社會的變化更是日新月異,但是人們所渴盼的精神和美好永遠不會改變,依然在“假亦真,真亦假”的往復中判斷是非、探尋真諦,也同樣努力在“假惡丑”的背后尋求“真善美”。人們仍然向往純潔的愛情,珍視可貴的友情,也依然在以夢為馬,為理想奮斗。就像這些美妙的歌曲,經典的片段,能夠穿越厚重的政治迷霧,刻入記憶的年輪,并且隨著時間的沉淀使得其余香飄逸,浸潤心靈,成為讓人永生難忘的視聽符號。
在今時今日的語境之下,當今的藝術創作早已不再以生命作為犧牲,由銀幕到歌劇看似只是藝術形式轉變的“一步之遙”,但卻需要創作者的勇氣和從觀念、手法開始的把握和領悟,也需要對于表現層次的縱深的掌控。說到此,和歌劇《冰山上的來客》同一天與觀眾見面的另一個取材于經典的作品——電影版《智取威虎山》也同樣說明了“經典”的價值,每一次對它的靠近它會釋放能量,讓人持續不斷地從中汲取靈感,不管變換何種藝術表現方式,都能夠為其注入新的內涵,帶領觀眾進行新的解讀和探尋。藝術思維的展現除了需要情感的表達、方式的鋪陳,更需要“潤物無聲”而非說教式地傳遞一種真正的“智慧”,這種智慧應該是一種正向的或是我們理應秉承或追求的觀念,借由藝術的形式、方法、手段帶著觀眾一起去努力追尋或是反觀自身。人們常常用“深入人心”來定義和形容經典,但說到底,所謂的“深入人心”,就是在滿足人們即聽、即視的感官需求之余,也經得起回昧、思索與沉淀。尤其是在這個“神曲”、“神作”層出不窮的年代,一些作品以“瘋、傻、冏、虐、雷”為噱頭吸引眼球,甚至以瘋狂的炒作與故意裝瘋賣傻對觀眾“洗腦”,一再挑戰觀眾的智商與接受底線,這樣的作品只能引發“吐槽”和“口水”而非感動與回味,最終離藝術創作的根本漸行漸遠。一部向經典致敬的歌劇《冰山上的來客》,在經典臺詞、經典場景的基礎上,用豐富的手段烘托、發展、升華,讓藝術表現的層次更豐富,用純凈的藝術之心來把控創作與呈現,追求精品,呈現精彩,為觀眾的耳朵與眼睛帶來真正的視聽“營養”,讓我們在感動中溫情懷舊。一部作品的價值與生命力不僅要交給時光,更要交給人心——既“悅目”又“賞心”,當是我們在當下及未來藝術創作之時對于作品價值的堅定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