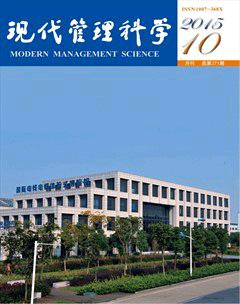去商品化、社會保障與國民儲蓄
摘要:文章從去商品化角度出發,分析了西方福利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對國民儲蓄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社會保障支出對國民儲蓄具有明顯的擠出效應,但社會保障對國民儲蓄的影響程度依賴于各國福利制度的具體安排,在去商品化程度較高的國家,公共福利計劃降低了整體國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行為,因此社會保障制度能有效地提升國民儲蓄水平。最后本文針對該研究結論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啟示,希望能為當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提供經驗支持。
關鍵詞:去商品化;社會保障;國民儲蓄
一、 引言
福利國家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進行了多方面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例如從單一的籌資方式過渡到多支柱社會養老保障的籌資方式。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經濟增長和社會保障支出之間的矛盾,實現了社會公平和效率。而在以往研究社會保障對經濟增長的文獻中,有關社會保障對儲蓄行為的研究一直受到許多學者的關注。那么在福利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的國家,社會保障與國民儲蓄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關系?顯然當前我國處于高儲蓄和經濟增長放緩的發展狀態,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又使得我國未來社會養老保障基金將面臨著巨大的支付壓力,因此針對這些現實問題的探討將有助于我們理解社會保障與國民儲蓄之間復雜的關系,從而為未來我國制定科學合理的公共保障政策提供重要的借鑒。
二、 文獻綜述
關于社會保障與儲蓄行為的研究一直是研究社會保障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研究表明社會保障會對居民儲蓄行為存在顯著影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論是費爾德斯坦(Feldstein,1974)提出了替代效應和引致退休效應,他認為社會保障對儲蓄的影響取決于這兩方面作用的大小,因此他利用美國二戰后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發現社會保障會抑制居民儲蓄。但另外的研究卻對此產生質疑,例如雷蒙、雷斯羅伊(Leimer & Lesnoy, 1982)重新對費爾德斯坦定義的社會保障財富進行了計算,結果發現社會保障反而會提高居民儲蓄。另外,巴羅(Barro,1978)對此提出了中性理論,他認為社會保障對儲蓄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而我國學者也對此進行了相關研究,例如孫永勇(2005)通過對12個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經驗分析,得出社會保障與國民儲蓄存在負相關,但并不顯著;而在國際間比較卻發現社會保障對國民儲蓄的影響為正,因此他認為社會保障對國民儲蓄的影響是不確定的。而彭浩然和申曙光(2007)利用我國3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進行了經驗分析,他們的結論是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制度降低了居民的儲蓄。雖然從目前的文獻來看,國內大部分相關的研究都認為社會保障會抑制儲蓄,但仍有學者的研究得出相反結論,例如謝文和吳慶田(2009)的研究則表明社會保障能提高居民儲蓄的水平。
從以往的文獻來看,目前關于社會保障對儲蓄問題的研究仍存在許多爭議性地方,但需要注意的是,以往研究大都把研究視角放在社會保障支出或者參與覆蓋面上,這難免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為在不同的福利國家中,福利支出往往在性質上有著明顯的差異,例如在在北歐國家,政府主張通過公共保障服務來實現全民保障計劃,因此福利保障支出會明顯體現在社保支出當中,而反觀在北美福利國家,由于國家鼓勵市場化的操作模式,政府會通過稅收優惠來推動私人保障計劃的開展,因而這些稅收支出的減免并沒有在社保支出中列示出來。因此為了能更為全面地考察社會保障對儲蓄行為的影響,本文選取各國福利保障制度的去商品化程度作為研究視角,進一步考察社會保障對國民儲蓄的影響是否會受到各國福利保障制度安排的影響,希望能對現有的相關文獻進行有效補充。
三、 模型設定和數據描述
1. 基本計量模型。為了考察在不同國家的福利體制下,社會保障對國民儲蓄的影響是否依賴于去商品化程度,本文參考賴偉良(2010)做法,選用L.Scrugg 的Comparative Welfare Entilements Dataset 2(CWED2)所計算的綜合指數(Generosity Index)作為去商品化指標加入到計量模型中,目的是通過該指數來衡量各國居民對政府福利的依賴程度。進一步本文參考相關學者的做法,建立以下計量模型:
savingt=?琢+?茁1ssrit+?茁2ssrit*decomit+?茁x■it+fi+?濁t+?灼it(1)
在模型(1)中:saving代表國民儲蓄占GDP比重,ssr代表社會保障支出占GDP比重,decom代表去商品化程度,進一步為了控制其他因素對估計結果產生的影響,本文選取了一組控制變量■,具體如下:
(1)預期壽命(Explife):預期壽命往往反應了一個國家國民健康水平,一般來說,由于國民壽命的延長,居民整體的儲蓄動機都增加,進而會帶動儲蓄率的上升。(Bloom et al. ,2003;Barro and Sala-i-Martin,2003)。因此,為了能有效地表征預期壽命對國民儲蓄的影響,本文選取新生嬰兒整體預期壽命作為控制變量;(2)實際經濟發展水平(rgdp):實際經濟發展水平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社會發展水平,一方面:實際發展水平的提高意味著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從而影響公民的儲蓄行為(孔杏,2015);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意味著科技技術的水平的提高,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居民的經濟行為。因此為了表征經濟發展水平對國民儲蓄的影響,本文選取實際gdp增長率作為控制變量;(3)人口老齡化程度(aging):人口老齡化對國民儲蓄的影響主要有兩方面: 一方面人口老齡化能影響消費服務行業的需求,從而影響到老人自身的消費和儲蓄行為(陳衛民,2014);另一方面,由于父母存在利他主義行為,因此年老的父母在對孩子的消費進行支出,并會以儲蓄形式留給孩子財富。因此為了能表征老年人口對居民消費所帶來的影響,本文選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作為控制變量。
2. 數據來源和描述性統計。本文采用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以下數據庫:世界銀行(WB)、CWED2、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國際勞動組織(ILO)。表1顯示了描述性統計結果。
四、 基本回歸結果及穩健性檢驗
從表2顯示的結果來看,面板設定F檢驗拒絕了原假設,因此本文認為模型中不適合采用混合OLS估計;而從Hausman檢驗的結果可以看出,原假設不成立,因此本文認為模型(1)應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
進一步看回歸估計結果:從社會保障支出(ssr)的系數來看,模型(1)中的三種回歸方法都顯著為負,而且從固定效應模型的結果來看,社會保障支出對國民儲蓄具有明顯的擠出效應。從這估計結果可以看出,強制性的福利保障計劃會導致整體儲蓄水平的下降,因此社會保障支出對國民儲蓄具有負面影響。
本文對各國去商品化程度做進一步的考擦,因此將去商品化指數作為交叉項放進模型(1)中,用來考察去商品化程度是否影響社會保障對國民儲蓄的影響。而從估計結果來看,交叉項系數(ssr*decom)顯著為正,從該估計結果可以看出,去商品化程度會顯著影響社會保障對國民儲蓄的作用效果,在去商品化程度較高的國家,由于政府為大部分公民提供寬廣的福利保障和就業培訓計劃,這些制度上的安排使得福利國家的公民完全依賴于政府的福利大廈,而對私人部門的服務業特別是私人休閑服務業的規模縮減到十分有限的地步(彭華民,2012),導致了邊際消費傾向偏低,消費需求不足等情況。因此從這里看出:去商品化程度越高,居民越依賴于政府提供的各種保障性服務,因而會減少消費支出,從而提高了整體儲蓄水平。
進一步,本文對控制變量進行了考察,發現在固定效應模型中,3個控制變量的系數顯著性都通過了相關檢驗,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對模型(1)進行回歸是比較合適的選擇。
進一步,本文考慮到基本回歸模型(1)中可能會存在內生性等問題,為了避免這些因素對研究結果可能造成影響,本文采用了3種估計方法對基本模型進行了穩健性檢驗,具體方法分別是:剔除極端值、考慮滯后效應和動態估計方法。從具體操作上看:(1)、剔除極端值的做法先對樣本數據中1%以下和99%以上的分位數值進行極端值處理,然后再進一步利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2)滯后效應的做法將模型(1)中所有的解釋變量都替代為各自變量的滯后一期,然后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這種處理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降低當期其他解釋變量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所帶來的影響。(3)動態面板估計,本文對模型(1)的估計方法進行調整,采用糾偏LSDV估計方法進行回歸,具體的估計結果見表3。需要說明的是,在動態面板的估計方法中,由于內生性問題會使得OLS估計結果產生向上偏差,而固定效應(FE)模型產生向下偏差,因此Bond等(2001)提出了一個經驗法則:若系統GMM估計得出的滯后因變量系數比固定效應回歸結果要大,而比OLS估計結果要小時,可以認為該估計結果有效,而且這一經驗法則同樣適用于糾偏LSDV估計。從估計結果來看,滯后一期因變量的系數都處于OLS和FE所估計的系數之間,因此本文認為動態面板估計結果有效。最后從整體上看,表3與表2中的基本回歸模型結果相一致,因此本文認為基本回歸模型所得到結論并沒有受到內生性等問題的影響,因此具有較好的穩健性。
五、 結論及啟示
本文研究結果發現:社會保障對國民儲蓄的作用效果會受到各國福利保障制度的具體制度安排影響。從發達國家的整體福利水平上看,社會保障支出會對國民儲蓄具有明顯的擠出效應。但社會保障對國民儲蓄的影響程度依賴于各國福利制度的具體安排,在去商品化程度較高的國家,由于公民高度依賴于政府的公共服務型,消費型服務行業基本被縮減到最低程度,因而社會保障會提高國民儲蓄水平。因此在去商品化程度較高的國家,社會保障會對國民儲蓄有顯著的正向作用。
從實踐意義上看,國民儲蓄是一個國家長期經濟發展的重要物質保證,而當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面臨著種種難題,如何處理好現實中“保民生”和“穩增長”之間的矛盾成為了目前我國社會保障中的急需突破的重點工程,一方面目前我國仍處于高儲蓄率階段,這種高儲蓄現象進一步會抑制了居民整體的消費需求,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但另外一方面則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仍處于“碎片化”階段,許多服務性的勞動保障和就業安排都沒有被考慮進來。因此對于我國而言,政府應在參考國外改革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完善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一方面,政府應逐步擴大社會保障覆蓋范圍和針對低收入特殊群體的保障力度,確保低收入對象能享受到應有的基本保障性服務安排;但另一方面,政府應著力提升市場管理者角色,在福利保障市場上,應借助市場化手段來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例如開展各類商業保障模式,在職就業培訓和商業養老模式,通過這些方式將有效地提高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從而為我國社會的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參考文獻:
[1] 賈俊雪,郭慶旺,寧靜.傳統文化信念、社會保障與經濟增長[J].世界經濟,2011,(8):3-18.
[2] 彭浩然,申曙光.現收現付養老保險與社會經濟增長:理論模型與中國經驗[J].世界經濟,2007,(10).
[3] 龔六堂,郭凱明.社會保障、家庭養老與經濟增長. 金融研究,2012,379(1):78-89.
[4] 蔣云赟.我國養老保險對國民儲蓄基礎效應實證研究——代際核算體系模擬測算的視角[J].財經研究,2010,(3):14-24.
[5] 孫永勇.社會保障對儲蓄的影響——西方主要理論思想與經驗檢驗研究[D].武漢大學學位論文,2005.
[6] Feldstein,M, Social Security and Private S- aving: Repl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 [J],1982(90):630-652.
[7] Rowena, Pecchenino, Social security, social welfare and the aging population[J]. Population economic,1999,(12):607-623.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發達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政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號:15ARK001)。
作者簡介:馮劍鋒(1987-),男,漢族,廣東省佛山市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社會保障與人口老齡化。
收稿日期:2015-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