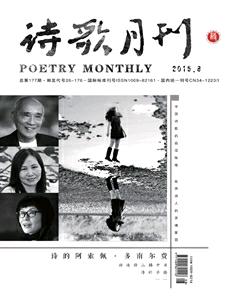楊獻平的詩
洗澡
十歲以前,我帶他洗澡
“你的怎么大,我的為啥這么小?”
我給他擦身子,那股青草香
洗頭發,他哇哇叫
十三歲這年春天,他說:“爸爸,我自己洗。”
我笑笑。水聲響亮啊
我在玩電腦。“爸爸,替我擰一下毛巾吧!”
確實長大了,個子比我還高
我再笑笑,心里想,一個男人
活著,就像這浸滿水的毛巾
越擰越小。“竟然也有了絨毛!”
我怔在當地
忽然想放聲嚎啕
獨自喊媽媽的老男人
我喊:媽媽媽媽媽媽媽媽
我當然有母親,但俺們那兒叫媽媽叫娘
我在外鄉很多年了
很多時候,我喊媽媽
連續喊,自我驚詫,然后放聲哭
我不知道為什么哭
什么又值得我哭。哭在這個時代
沒有根,也沒有樹冠
人人都是枝葉。向天空毀于閃電
向四周敗于同類
媽媽媽媽媽媽……只能無人應聲
這世界多么空曠啊
一個男人,叫媽媽都那么空
一個四十多歲的人
喊媽媽的,他叫楊獻平,他空
他時常用舌尖捉拿悲痛,從外部收集不幸
這么說吧
這么說吧,其實像舌頭
我怎么能割舍?這么說你一定生氣
當年的手指繞到裂石背后
所為不是一朵花
一朵花所想,也不止一顆額頭
這么說我其實后悔
是啊,除了你,還有那種口吻
給我以眩暈
當然還有眩暈之后
濃郁的不是靈魂,肉身的味道真的太好
我們來這世上就是為了相互有個照應
就像那一夜的胸脯
再沒有那么洶涌的絕望了
人活著,難道不是要好好抱抱
好好要要?這么說你不一定能看到
我只想笑笑看
我只想用這些話,把自己暖一下
野外有大安靜
且不說春光。在城市
到處都硬。硬硬的硬,鉆心疼的硬
硬是當代人的宿命
野外遠。即使枇杷樹于窗外咳嗽不停
玉蘭在午夜修煉妖精
鳥鳴總像夢境和它補漏的鐵釘
很久了,這硬,肉身是自己的牢籠
精神困厄,不亞于三十六樓捕風
幾公里的水泥路
幾十年的輪胎與街燈。迎面的綠
還有紅。低到頭頂的草,小花手搖清風
野外之野,在于它敢于不從
與人列疆而治,就像我扎入以后的落葉脆響
野外有大安靜,似乎生命前一刻成形
樹干黑,泥土粘肉
綠葉遮蔽的天空,云朵好像前世胎衣
此生第一次遭遇愛情。頭頂怎么那樣紅
我爬上去,燒灼的紅楓
心有曠野的人當大笑三聲
更應心藏清水與芳草,以野外的大安靜
生日帖
迥然于帝王戲,但肯定是草民史
那一夜橫在黎明
土坑和油燈,一個人的疼
持續我一生。那個婦女,鄉村籠罩
一個男孩哭。這世界照樣文攻武斗
一個國家和她的人民
哪兒會在乎一個人的生與不生
這就是宿命,成長是一筆糊涂賬
兩三個春秋和大雁的陰影
男孩善于恬不知恥。光著的身體掛滿原罪
某天夜里我忽然驚醒
那股腥味至今嗆得人發暈
一個男人由此長成。一個人生至此霧靄纏身
大雪還未及肩,我已經逃逸西北
瀚海之大,數沙子的不是詩人
一定就是醉鬼。天和地,蒼茫的兔死狐悲
多少次我明月磨刀,反轉向自己的靈魂
很多時候我夜不成寐
反復尋找一顆心。所謂的青春
巖石上的水滴和黃塵,還有蝎子的尾針
所幸我此生有幸,所幸另一個女人
她和我母親。一個困厄過的男人心有疆場
一個男人夢想駿馬狂奔
有一天我只身去京,眾人已經不再和他人相親
一個時代好像一塊生鐵
他自身和如我的人,更多的卻是裝飾品
再些年我心有暮年
只是不愿意承認。肉體發皺
如同大多數人的靈魂。每一年我都在這一天
想起自己的母親。每一次生日都不由得心生悲憫
為正在寫詩的這個人
也為我已經去世的父親
一個男人沒有理由。慶祝生日實在愚蠢
如我此一刻,點一支香煙
并用它來瞄準:春天的花草在鳥鳴里成批倒退
日光以人為背景,獵殺洶涌的人群與光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