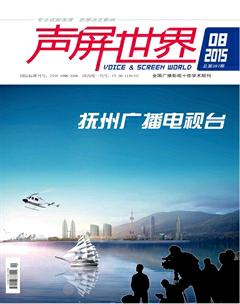中印電影音樂民族化比較
□李 靜
欄目責(zé)編:曾 鳴
一
2009年在國際電影及音樂界有一個熱門的話題,那就是獲得第81 屆奧斯卡8 大獎項的電影 《貧民窟的百萬富翁 (Slumdog Millionaire)》(以下簡稱“貧民”)。該電影描述的是印度孟買一家電視臺舉辦了一個名叫“誰想成為百萬富翁”的節(jié)目,若參賽者能答對十二個問題,就可獲得2000 萬盧布巨獎。18 歲的小伙子杰瑪住在貧民區(qū),為了讓多年不見的幼年時的女朋友拉提卡能在電視上見到自己,他便去參加節(jié)目競猜。就在他答對了十一個問題,馬上就可以得到2000 萬盧比之時,警察懷疑他作假將他逮捕。為證清白,杰瑪向警察講述了自己成長過程中經(jīng)歷的苦難和銘記愛人的情感故事,每段故事當(dāng)中都包含了他獲獎的答案。最后他成功地回答了所有問題,找到了心愛的戀人。
在這部影片中,印度的電影音樂就像是印度的文化血脈,賦予電影強大的生命和感染力。丹尼·鮑爾導(dǎo)演對印度電影的音樂力量非常了解,他選了電影作曲家拉曼(印度當(dāng)今非常偉大的作曲家)為該片配樂,也是該片能夠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貧民》的獲獎歌曲由賈伊作詞,他說:“丹尼導(dǎo)演和拉曼幫助人們捕獲了這個城市的精神”。確實如此,片頭曲《噢,薩亞》從開始就將大家?guī)氲匠錆M印度氣息的場景和氛圍之中。當(dāng)《噢,薩亞》神性般的主題曲旋律在大鼓的節(jié)奏下穿越在孟買貧民區(qū)的大街小巷時,那涌動的節(jié)奏及歌詞與印度社會的真實生活,尤其與孟買這個忙碌而復(fù)雜的貧民生活非常貼切。命運不斷輪回,神靈無處不在,這便是印度,這便是孟買;現(xiàn)實與理想,肉體與心靈,這就是印度的輪回宗教思想。《噢,薩亞》的主題歌雖是空靈的,但是副歌卻天真爛漫,充滿了喜悅和童趣。帶有嘻哈(Hip-Hop)風(fēng)格的音樂,隨性、自由、大膽和不拘一格,將印度貧民“痛并快樂著”的精神狀態(tài)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
整部電影音樂以舞曲風(fēng)格為基調(diào),它從聽覺上向人們展示出了孟買忙碌的現(xiàn)代化城市生活,恰如其分的表現(xiàn)了孟買復(fù)雜的社會生活,對孟買的貧民文化具有認同感。還有就是印度電影音樂的重節(jié)奏、重節(jié)拍也是印度文化的突出特征。電影《貧民》雖沒有大段歌舞表現(xiàn),但觀眾從內(nèi)心深處仍能感受到印度的歌舞氣息。這由印度音樂自身所具備的豐富的節(jié)奏特征所決定。傳統(tǒng)印度電影中通常插入大量歌舞段落,在印度傳統(tǒng)的音樂里,其主要元素包括了節(jié)奏、旋律及持續(xù)音,和聲不是很重要,旋律的主要支撐因素是節(jié)奏節(jié)拍。節(jié)奏節(jié)拍在印度的音樂審美中變得越來越重要,他的節(jié)奏特征是印度音樂歷史的必然發(fā)展,本質(zhì)上是表達印度人民的一種樂觀天性,是印度人民對喜悅的生活本質(zhì)的認同。這來源于印度民間音樂表現(xiàn)出的開朗性格,或許這就是為什么越來越多的電影更傾向于表現(xiàn)印度民間各種各樣喜慶的節(jié)日場面,因為節(jié)日里富于節(jié)奏感的快樂的音樂琳瑯滿目,印度人民奉行的即時行樂的哲理在印度音樂當(dāng)中得到體現(xiàn)。該片的結(jié)尾以一段充滿著印度寶萊塢風(fēng)格的歌舞《勝利》 曲來結(jié)束,的確是水到渠成。《勝利》曲由印度偉大的作曲家拉曼用印度非常典型的歌舞音樂形式創(chuàng)作,將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旋律和西方現(xiàn)代電子音樂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令人心潮澎湃、心曠神怡,不僅與影片主題思想完美結(jié)合,而且將影片的劇情再次推向高潮,可謂是畫龍點睛之作。這段《勝利》曲也最終榮獲第81 屆奧斯卡最佳電影歌曲獎。
二
中國青年導(dǎo)演徐靜蕾自編、自導(dǎo)、自演的電影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以下簡稱《信》),榮獲了第52 屆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電影節(jié)最佳導(dǎo)演“銀貝殼”獎。該片以一名陌生女子的自述信為線索,用淡淡的凄語講述了她一生愛戀的悲涼。影片中輕柔的琵琶聲將主人公孤獨寂寥的內(nèi)心世界,以及愛恨交織的情感生活表現(xiàn)的恰到好處。
影片雖然來源于奧地利文學(xué)家茨威格的同名小說,但徐靜蕾的改編卻賦予了該作品具有中國特性的文化內(nèi)涵。影片從寂靜的黑暗中開始,清冷的琵琶聲伴隨著鋼琴聲緩緩拉開帷幕。整部影片的基調(diào)似乎都是昏黃的色彩,收斂、黯淡、傷感。影片中一個不斷外出的男人從他的旅程中再次回到家里,那天是他的生日,當(dāng)他獨自吃面的時候才記起這個日子,獨自一人默默的吃著面,似乎顯得有些凄涼。此時的他撕開了一封厚厚的信,隨著信封的打開也開啟了他那段封塵了20年的記憶。伴隨著淡淡的獨白,融合著琵琶的彈撥,一段凄美的愛情故事慢慢地展現(xiàn)在銀幕上。電影音樂中琵琶那細膩且婉轉(zhuǎn)的音色為本劇在氣氛渲染和情節(jié)推動上增色不少。
影片里輕柔的琵琶聲總是伴隨著女主人公的獨白出現(xiàn),隱約而幽暗,似乎有一種欲哭無淚、欲說不能的感覺。主題音樂 《琵琶語》 在影片中不時出現(xiàn),每次的出現(xiàn)都帶有略微變化來配合劇情的發(fā)展,對應(yīng)著人物細小的心理變化。第一次主題配樂出現(xiàn)是在片頭,平淡而冷靜的訴說在干凈輕柔的琵琶聲中展現(xiàn)出了她無怨無悔的情感往事。當(dāng)女孩與男人的一次偶然相撞,這時主題音樂第二次適時的在影片中響起,就在那幾秒鐘的眼神對視中,她便決定了她這一生都將屬于這個男人。第三次琵琶聲響起是在女孩要隨母親改嫁山東之前,臨行前夜她難以入眠,冒著嚴(yán)寒癡癡的在作家門前等待。凌晨三點鐘她終于等到了他回來,可是他懷里卻擁著另一個女人,此時淚水浸濕了女孩的眼瞼,琵琶聲越發(fā)的加急加重,女孩心中的傷痛與無奈也越發(fā)的清晰起來。影片結(jié)尾的時候主題音樂第四次完整出現(xiàn),當(dāng)作家看完了女人的來信,癱軟在華麗的沙發(fā)上,久久地低頭,又緩緩地抬起,孤獨地環(huán)視房間四周,此時琵琶聲幽幽出現(xiàn),如泣如訴,跟剛開始的一樣。開放形式的結(jié)尾伴隨著單純的琵琶聲含義雋永。女人對愛情的不悔與執(zhí)著和男人對自己一生的反觀、懷疑和懊悔的心緒都從音樂中汩汩流出。在那沉靜、舒緩的音樂聲中故事走向結(jié)束,但輕柔的琵琶聲依然縈繞在觀眾的耳邊揮之不去。
主題音樂 《琵琶語》 沉郁的鋼琴聲,反復(fù)的前奏,再加上中國民族樂器琵琶所獨有的特點,就這樣感情一步步得到升華,最終使人們沉浸在音樂的畫面里不能自拔。其中,鋼琴、中提琴、小提琴、三角鐵、洞簫時隱時現(xiàn),將和聲效果巧妙地展現(xiàn)出來,不僅彰顯了琵琶如泣如歌的特點,更豐富了樂曲的感情和表現(xiàn)力。
三
從某種角度來講,《信》 中民族音樂的使用有成功之處。然而,通過與《貧民》對比,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兩者的優(yōu)劣。
一、同是對民族音樂的使用,《貧民》的音樂色彩相對豐富許多。節(jié)奏、旋律有變化、有起伏,同時與畫面配合的很默契。而《信》的旋律與變奏單調(diào)得多,使整個影片顯得略微沉悶。
二、在《貧民》這部影片中,印度電影音樂就如同印度文化的血脈一樣,賦予印度電影極強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民族音樂與民族文化相呼應(yīng),《貧民》的成功更加突出了在文化認同上傳統(tǒng)的非凡地位。文化認同若離開傳統(tǒng),就如同無源之水。對比之下,《信》的音樂就缺少這種深度,這種民族文化的認同感。
印度的電影音樂在思想上,承繼了藝術(shù)審美和宗教哲學(xué)思想的傳統(tǒng);在形式上,承載了民間音樂以及古典音樂的傳統(tǒng);在內(nèi)容上,秉承了行為規(guī)范和社會生活等傳統(tǒng),這些傳統(tǒng)就是印度文化的靈魂與精髓,印度電影音樂的文化根源。這些傳統(tǒng)為印度的電影音樂文化發(fā)展與生長提供著豐厚的養(yǎng)料和堅實的基礎(chǔ),使得印度的電影音樂文化成了一種符合時代發(fā)展和適應(yīng)印度社會生活的獨特音樂文化類型。
在“文化全球化”不斷發(fā)展的趨勢下,文化交往在國際間不但變得愈來愈頻繁,而且互動和交融成為如今全球文化基本的“特色”,文化的基礎(chǔ)顯得尤為重要。如何確保文化基礎(chǔ)不動搖,如何才能讓我們的音樂文化面向世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電影《貧民》的音樂以及印度的電影音樂文化發(fā)展道路將給予我們更好的借鑒和啟迪。
1.崔新建:《文化認同及其根源》,《北京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4(4)。
2.王云階:《論電影音樂》,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4。
3.許衫衫:《中國電影民族音樂現(xiàn)狀研究》,西南大學(xué),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