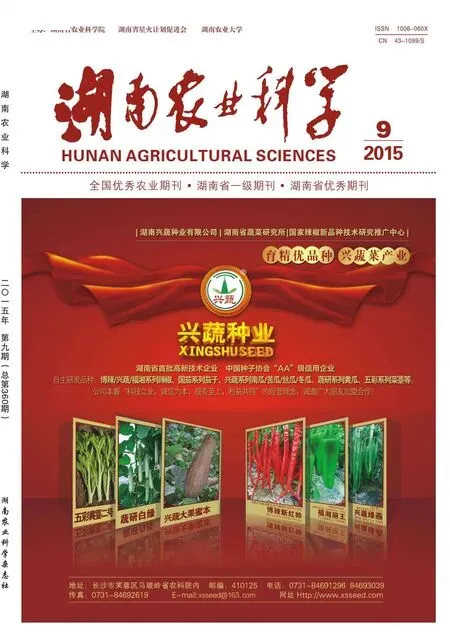中國農(nóng)村勞動力向城鎮(zhèn)二三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的長期性分析
黃寧陽,馬 強,陳武霞
(1.華中農(nóng)業(yè)大學(xué)經(jīng)濟(jì)管理學(xué)院 湖北農(nóng)村發(fā)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0;2.華中農(nóng)業(yè)大學(xué)財務(wù)處,湖北 武漢 430070)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zhèn)化水平不斷提高。據(jù)統(tǒng)計,2011年我國城鎮(zhèn)化水平超過50%,意味著我國城鎮(zhèn)居民已經(jīng)超過農(nóng)村居民,標(biāo)志著數(shù)千年來我國以農(nóng)村人口為主的城鄉(xiāng)人口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逆轉(zhuǎn),中國從一個具有幾千年農(nóng)業(yè)文明歷史的農(nóng)業(yè)大國,進(jìn)入以城市社會為主的新成長階段。但是與發(fā)達(dá)國家相比,我國的城鎮(zhèn)化水平依然很低,發(fā)達(dá)國家的城鎮(zhèn)化率在80%左右[1]。目前,中國大約有1.5 億~2.0 億農(nóng)村富余勞動力,他們合理有序地向城鎮(zhèn)的第二、第三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就業(yè),對于解決三農(nóng)問題,對加快我國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和整個國民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有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2]。
受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的制約,勞動力向城鎮(zhèn)轉(zhuǎn)移以及城市化進(jìn)程本身是一個長期過程。英國城市化由25%提高到50%,用了將近70 a,從50%提高到75%,又用了近40 a[3]。拉丁美洲國家從20 世紀(jì)50年代開始城市化過程,城市化從41.5 %到71.5 %花了40 a時間[4]。中國城市化發(fā)展速度較快,1978年我國城鎮(zhèn)人口只占總?cè)丝诘?7 %左右,到2007年已經(jīng)達(dá)到46.9%,到2014年已經(jīng)達(dá)到54.8%,平均每年以約1%的速度增長。由于人口、經(jīng)濟(jì)和制度等因素的制約,中國的城市化要提高到發(fā)達(dá)國家水平仍需很長一段時間,而限制農(nóng)村勞動力向城市轉(zhuǎn)移就業(y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經(jīng)濟(jì)活動人口多與勞動參與率高導(dǎo)致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就業(yè)任務(wù)艱巨
國際上對經(jīng)濟(jì)活動人口的界定,是指在15 周歲及以上人口,有勞動能力,參加或要求參加社會經(jīng)濟(jì)活動,包括就業(yè)人員和失業(yè)人員。勞動參與率是指一國(或地區(qū))全體就業(yè)人員和失業(yè)人員的總數(shù)占該國(或地區(qū))工作年齡人口的比率,是測度人口參與社會勞動程度的指標(biāo),同時也反映出經(jīng)濟(jì)的活躍程度和發(fā)展?fàn)顩r。通常,勞動參與率越高,投入經(jīng)濟(jì)的勞動力數(shù)量相對就越多,需要就業(yè)的崗位就越多。
與世界各國相比,中國的經(jīng)濟(jì)活動人口多,據(jù)世界銀行數(shù)據(jù)庫數(shù)據(jù)顯示(表1),2012年我國經(jīng)濟(jì)活動人口多達(dá)7.8 億,為世界第一,占世界經(jīng)濟(jì)活動人口24%;印度約4.8 億,占世界經(jīng)濟(jì)活動人口11%;美國約1.6 億,占世界經(jīng)濟(jì)活動人口4.2%;巴西約1.1億,占世界經(jīng)濟(jì)活動人口3.2%。同時,中國經(jīng)濟(jì)活動人口的勞動力參與率高。由表1 可知,2012年中國男性與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分別為78%和64%,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美國(69%和57%)、英國(69%和56%)和日本(70%和48%)等發(fā)達(dá)國家的勞動力參與率,也高于俄羅斯(71%和57%)的平均水平,這無疑增加了就業(yè)壓力。

表1 2012年世界及有關(guān)國家經(jīng)濟(jì)活動人口和勞動參與率
2 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導(dǎo)致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就業(yè)難度加大
我國就業(yè)壓力大不僅體現(xiàn)在總量上,也反映在勞動力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上。人力資本是指勞動者通過教育、培訓(xùn)和實踐經(jīng)驗等獲得的知識和技能的積累。一般,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資本越高,適應(yīng)勞動力市場變化的能力越強,就業(yè)率越高。
從表2 中可以看出,中國經(jīng)濟(jì)活動人口接受過初等教育的比重仍然占主導(dǎo)地位,經(jīng)濟(jì)活動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遠(yuǎn)低于美國、英國、日本、德國和法國等世界發(fā)達(dá)國家。2011年,中國經(jīng)濟(jì)活動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總?cè)雽W(xué)率為24%,美國、英國、日本、德國和法國同期同程度接受高等教育的總?cè)雽W(xué)率分別為95%、61%、60%、57%和57%[5]。人才素質(zhì)與市場需求的結(jié)構(gòu)性矛盾影響了就業(yè)規(guī)模的擴(kuò)大,加劇了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就業(yè)的難度。

表2 不同國家經(jīng)濟(jì)活動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構(gòu)成(總?cè)雽W(xué)率) (%)
3 第三產(chǎn)業(yè)就業(yè)彈性降低導(dǎo)致對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的拉動作用減弱
就業(yè)彈性是指勞動力就業(yè)的增長率與經(jīng)濟(jì)增長率之間的比值,其經(jīng)濟(jì)涵義是經(jīng)濟(jì)每增長1%,就業(yè)增長幾個百分點。通常,就業(yè)彈性不斷減小說明每創(chuàng)造一個增量的產(chǎn)值所需要的勞動增量變小了。
從表3 中可以看出,從1993~2014年,我國第一產(chǎn)業(yè)就業(yè)彈性大多數(shù)年份為負(fù)數(shù),且有趨于減小趨勢,這說明每創(chuàng)造一個增量的產(chǎn)值第一產(chǎn)業(yè)所需要的勞動增量變小了。同期,第二產(chǎn)業(yè)和第三產(chǎn)業(yè)的就業(yè)彈性存在一定波動性[6]。1993~2002年,我國第二產(chǎn)業(yè)的就業(yè)彈性趨于減小,甚至為負(fù)數(shù);這說明這一期間第二產(chǎn)業(yè)對勞動力的需求在減少;2003~2006年第二產(chǎn)業(yè)的就業(yè)彈性出現(xiàn)短期增加,之后2007~2014年第二產(chǎn)業(yè)的就業(yè)彈性穩(wěn)定在0.22 左右。相比較1993年的第三產(chǎn)業(yè)的就業(yè)彈性,除了少數(shù)年份(1995 和1996、2003 和2004)有所增加外,總體趨勢也是趨于減小,到2014年,第三產(chǎn)業(yè)的就業(yè)彈性減小到0.15;這說明第三產(chǎn)業(yè)增長對就業(yè)的拉動作用在減弱。

表3 1993~2014年中國三次產(chǎn)業(yè)就業(yè)增長產(chǎn)值增長及就業(yè)彈性
4 就業(yè)與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偏離度大導(dǎo)致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需要長時間磨合
就業(yè)結(jié)構(gòu)偏離度是指某一產(chǎn)業(yè)的就業(yè)比重與產(chǎn)值比重之差,是衡量經(jīng)濟(jì)中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和勞動力就業(yè)結(jié)構(gòu)匹配程度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一般來說,結(jié)構(gòu)偏離度與勞動生產(chǎn)率成反比。當(dāng)結(jié)構(gòu)偏離度大于零時,結(jié)構(gòu)偏離為正偏離,表明該產(chǎn)業(yè)的就業(yè)比重大于產(chǎn)值比重,意味著該產(chǎn)業(yè)的勞動生產(chǎn)率較低。結(jié)構(gòu)正偏離的產(chǎn)業(yè)存在勞動力轉(zhuǎn)出的可能性,結(jié)構(gòu)負(fù)偏離的產(chǎn)業(yè)存在勞動力轉(zhuǎn)入的可能性。
從表4 中可以看出,我國三次產(chǎn)業(yè)均存在就業(yè)與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偏離,就業(yè)結(jié)構(gòu)與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不匹配。我國第一產(chǎn)業(yè)偏離度大于零,意味著我國第一產(chǎn)業(yè)有大量的勞動力需要轉(zhuǎn)移[7]。隨著農(nóng)村勞動力不斷向城鎮(zhèn)的二三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第一產(chǎn)業(yè)中就業(yè)與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偏離度已從2002年的36.3 降至2013年的24.5。這一數(shù)據(jù)說明,一方面勞動力在第一產(chǎn)業(yè)逐漸減少;另一方面第一產(chǎn)業(yè)仍然存在富余勞動力。第二和第三產(chǎn)業(yè)的就業(yè)偏離度低于零,說明我國第二和第三產(chǎn)業(yè)還有較大的就業(yè)空間。21 世紀(jì)以來,第二和第三產(chǎn)業(yè)的就業(yè)與產(chǎn)業(yè)偏離度都有所降低。其中,第二產(chǎn)業(yè)的偏離度從2002年的23.4 降至2013年的14.5,第三產(chǎn)業(yè)的偏離度從2002年的12.9 降至2013年的7.9。這說明第二和第三產(chǎn)業(yè)在吸收第一產(chǎn)業(yè)富余勞動力方面發(fā)揮了積極作用。第二產(chǎn)業(yè)偏離度大于第三產(chǎn)業(yè),說明第二產(chǎn)業(yè)還有較大的就業(yè)空間[8]。我國就業(yè)結(jié)構(gòu)與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嚴(yán)重不對稱性,意味著中國農(nóng)村勞動力向城鎮(zhèn)的二三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需要長時間磨合,轉(zhuǎn)移過程不可避免地具有長期性。

表4 2002~2013年中國三次產(chǎn)業(yè)產(chǎn)值構(gòu)成、就業(yè)構(gòu)成及就業(yè)偏離度
5 戶籍制度延緩了農(nóng)村勞動力向城市轉(zhuǎn)移就業(yè)進(jìn)程
勞動力的非自由流動將大量的農(nóng)村人口滯留于農(nóng)村,延緩了我國農(nóng)村人口城市化的進(jìn)程。我國現(xiàn)行的戶籍管理制度是計劃經(jīng)濟(jì)的產(chǎn)物,目前的戶籍管理法將人口劃分為農(nóng)業(yè)人口和非農(nóng)業(yè)人口,分別持有農(nóng)業(yè)戶口和非農(nóng)業(yè)戶口,并以此作為政府對農(nóng)村人口涌入城市進(jìn)行行政調(diào)控的最重要手段,從而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動。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嚴(yán)格控制農(nóng)村人口進(jìn)入城市。改革開放以后,對農(nóng)村人口進(jìn)入城市雖然不再嚴(yán)格控制,但是城鄉(xiāng)分割的戶籍制度,導(dǎo)致農(nóng)民工既是城市居民,也不完全是城市居民;既是農(nóng)村居民,也不完全是農(nóng)村居民。由于戶籍的限制,“農(nóng)民工”這個群體實際上處在社會底層,受到很多不公平待遇[9]。比如養(yǎng)老險、醫(yī)療、住房、子女就學(xué)、就業(yè)等方面都不能夠享受與城市居民一樣的待遇,甚至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人口流動的成本,尤其是農(nóng)村居民要擁有城市戶口所需付出的成本巨大。近年來,一些大城市相繼進(jìn)行了戶籍制度改革,適當(dāng)降低了外來人員落戶門檻,但對一般的勞動者還是進(jìn)行了嚴(yán)格的轉(zhuǎn)入限制,由于他們?nèi)狈W(xué)歷、技能、資金,被剝奪了自由遷徙的權(quán)利[10]。最典型的就是農(nóng)民工,雖然他們對城市建設(shè)做出了很大貢獻(xiàn),但是難以在城市定居,無法得到城市人的身份。
[1]鄧大松. 對我國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流動趨勢的預(yù)測[J]. 統(tǒng)計與決策,2008,(15):94-96.
[2]鄭 列. Markov 鏈在預(yù)測農(nóng)村勞動力流動趨勢中的應(yīng)用[J]. 湖北工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2007,22(1):45-47.
[3]王愛華. 英國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 世界農(nóng)業(yè),2015,(1):52-57.
[4]張宏麗,郭 英.國外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轉(zhuǎn)移理論研究綜述[J]. 經(jīng)濟(jì)研究導(dǎo)刊,2010,(34):124-125.
[5]史麗萍. 美國城鎮(zhèn)化發(fā)展的啟示[J]. 產(chǎn)業(yè)與科技論壇,2015,(4):18-19.
[6]唐曉芬,趙秉新. 基于支持向量的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預(yù)測[J]. 安徽農(nóng)業(yè)科學(xué),2011,39(11):6837-6838.
[7]關(guān)海玲,丁晶珂,趙 靜. 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對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吸納效率的實證分析[J]. 經(jīng)濟(jì)問題,2015,(2):81-85.
[8]張在金. 湖北省農(nóng)村勞動力就業(yè)及轉(zhuǎn)移的預(yù)測與政策建議[EB/OL]. http://www.sannong.gov.cn/fxyc/ldlzy/200510261204.htm.
[9]李定洪,宋山梅. 我國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與城市化問題研究[J]. 天津農(nóng)業(yè)科學(xué),2015,21(1):65-69.
[10]杜永紅,宋建新. 我國農(nóng)村城鎮(zhèn)化發(fā)展的對策研究[J]. 當(dāng)代經(jīng)濟(jì),2015,(1):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