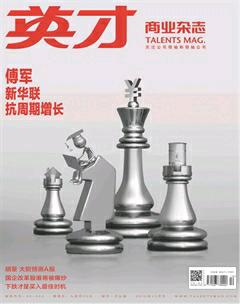安好
姜蘇鵬

再熱鬧的場景,也隱含著游絲般的荒涼;再美妙的歡樂,也行將結束;再永恒的愛情,也終將逝去。
華多的《舟發(fā)西苔島》,被爭議了300年,西苔島是傳說中的愛之島。到底年輕情侶們正準備前往愛之島經(jīng)歷一次愛的冒險,還是剛剛在愛之島完成海誓山盟?但這并不關鍵,真正刺痛我的是華多找不到安身立命的那份感傷。
37歲病逝,終生未娶,死亡似乎一直籠罩著華多。這或許就是為什么,畫面中扭身回眸的女子,眼神里看不見任何興奮,只有無限的眷戀。
套用王爾德的一句話:把人生的某個時刻分成好和壞是荒謬的。它要么迷人,要么乏味。我覺得某些重要的時刻,被慢慢遺忘,是時間的絕情。若一切安好,便是時間的溫情。
9月15日,豐子愷先生40周年祭日,朋友圈里頻刷先生的《不寵無驚過一生》:不亂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將來,不念過往。如此,安好。“像一個人”便是先生的全部追尋,在大多數(shù)人惶惑、焦躁的年代,重讀先生的舊詩,真的能有微許的豁然開朗:既然無處可逃,不如喜悅。既然沒有凈土,不如靜心。既然沒有如愿,不如釋然。
十幾年前跟京城無所不玩的大玩家王世襄老先生攀談,老先生不急不迫的樣貌記憶猶新。尤其當我問他,“文革”時期,在他最好的年華,大把的歲月蹬著三輪車走街串巷地搜集舊家具,是否真的值得。老先生說,到了我這個年齡,都是值得的,只要活得明白,玩得其所,玩物得志。
偶讀契訶夫臨死前寫給所愛的人的信:“愿你安好如初。最重要的是你能快樂地生活,不要把人生想得太復雜,因為人生的真實面目恐怕是再簡單不過的東西。”邊看邊想,或許不合時宜,但內(nèi)心的真實就是不要活得那么赤裸裸的真實,固執(zhí)地以為,活回陶淵明時代,會更有趣味。
“只有存在的東西才會消失,不管是城市、愛情、還是父母。”意大利小說家伊塔洛·卡爾維諾的這句話很殘忍,但看懂了,才知道存在感沒那么重要,才領悟能夠存在有多么不易。
人總是在現(xiàn)世里,掙扎,苦痛;在糾結中,迷失,不安;然后在唯一的生命里,跌宕,承受。所以當翻閱法國記者泰松隱居原始森林的思考——《在西伯利亞的森林中》,觸動你的是最淺顯的道理:心若安,生活哪里都身安。
泰松在西伯利亞小木屋里居住了六個月。“沒有鄰居,不通道路,偶爾有人造訪。冬季,氣溫降至零下三十攝氏度,夏季,熊在湖岸陡坡出沒。”他帶去了書籍、雪茄和伏特加。“至于其他——天地,靜寂,孤獨——已在那里。在這片荒原中,我自創(chuàng)了一種樸素而美好的生活,度過的這段生命緊縮為幾個簡單的行為。面朝湖泊和森林,注視著日子流逝。砍柴,釣魚做飯,大量閱讀,在山間行走,在窗前喝伏特加。……我經(jīng)歷了冬春,感受了幸福、絕望,以及最終的平和。”
身處越來越不傳統(tǒng)的世界,像米蘭·昆德拉一樣懷戀慢生活的消失:“速度是出神的形式,這是技術革命送給人的禮物。當人把速度性能托付給一臺機器時,一切都變了:從這時候起,身體已置之度外,交給了一種無形的非物質(zhì)化的速度,純粹的速度,實實在在的速度,令人出神的速度。”
當從事傳統(tǒng)實業(yè)25年的新華聯(lián)董事長傅軍,面對不斷萎縮的傳統(tǒng)市場,不斷加劇的經(jīng)營風險,坦言要活下來,就要調(diào)整自己“未來不走產(chǎn)融結合的路,有些坎兒,有些瓶頸,你跨不過去。”
走過,安好,就是最完滿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