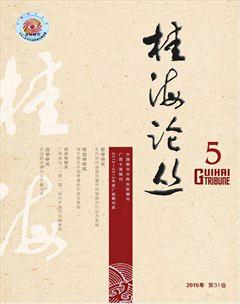推進(jìn)我國(guó)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發(fā)展的機(jī)制研究
彭金玉
摘 要:由于我國(guó)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供給主體單一、職責(zé)不明,需求表達(dá)渠道不暢、機(jī)制不完善,呈現(xiàn)“碎片化”和不可及性傾向,導(dǎo)致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存在著設(shè)施單一、使用效率低,醫(yī)療護(hù)理資源不足、服務(wù)人員專業(yè)水平低,精神慰藉服務(wù)缺失、老年人的社會(huì)價(jià)值難以實(shí)現(xiàn)等問(wèn)題。要解決以上問(wèn)題,必須明晰各類主體職責(zé)、構(gòu)建“共擔(dān)、互補(bǔ)、共享”機(jī)制,暢通需求表達(dá)渠道、構(gòu)建老年人積極參與的激勵(lì)機(jī)制,祛除“碎片化、構(gòu)建養(yǎng)老服務(wù)無(wú)縫隙供給機(jī)制。
關(guān)鍵詞:中國(guó)城市社區(qū);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滿意;耦合機(jī)制
中圖分類號(hào):D669.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4-1494(2015)05-0103-0
據(jù)國(guó)家統(tǒng)計(jì)局發(fā)布的《2014年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發(fā)展統(tǒng)計(jì)公報(bào)》顯示:到2014年底,我國(guó)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12億人,占全國(guó)總?cè)丝诘?5.5%,其中65周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dá)1.38億人,占全國(guó)總?cè)丝诘?0.1%;據(jù)預(yù)測(cè),到2020年,我國(guó)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dá)到2.43億,約占全國(guó)人口總數(shù)的18%,2025年將達(dá)到3億,2034年將突破4億。同時(shí),我國(guó)人口老年化呈現(xiàn)“快速化、高齡化、失能化、空巢化”等現(xiàn)象疊加的特點(diǎn)。快速增長(zhǎng)的老年人口,特別是高齡獨(dú)居老年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空巢困難老年人等特殊老年群體人數(shù)的增加,使得各類老年人對(duì)生活照料、康復(fù)護(hù)理、醫(yī)療保健、精神文化等多方面、多層次、多樣化的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日益增加,完善養(yǎng)老服務(wù)體系建設(shè)日趨迫切。
1982年聯(lián)合國(guó)《維也納老年問(wèn)題國(guó)際行動(dòng)計(jì)劃》中提出“養(yǎng)老服務(wù)應(yīng)以社區(qū)為基礎(chǔ)向老年人提供各方面的服務(wù)”;1992年聯(lián)合國(guó)《老齡問(wèn)題宣言》中強(qiáng)調(diào)要“以社區(qū)為單位,讓老年人盡可能在家中居住”,提出了不同于家庭養(yǎng)老和機(jī)構(gòu)養(yǎng)老的新型養(yǎng)老方式——社區(qū)養(yǎng)老,即以家庭養(yǎng)老為核心、社區(qū)服務(wù)為依托,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醫(yī)療保健和精神文化等養(yǎng)老服務(wù),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現(xiàn)已成為世界各國(guó)應(yīng)對(duì)越來(lái)越嚴(yán)重的人口老齡化發(fā)展趨勢(shì)的重要方式。
從20世紀(jì)80年代開始,我國(guó)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就開始得到政府的關(guān)注和重視;1993年民政部等13部委聯(lián)合頒布了《關(guān)于加快發(fā)展社區(qū)服務(wù)業(yè)的意見》,提出85%以上街道興辦一所老年公寓(托老所),正式將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納入國(guó)家發(fā)展規(guī)劃和年度計(jì)劃中;2001年民政部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推行“社區(qū)老年服務(wù)星光計(jì)劃”;2006年民政部《關(guān)于開展“全國(guó)養(yǎng)老服務(wù)社會(huì)化示范單位”創(chuàng)建活動(dòng)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城市至少要有一所相當(dāng)面積的具有指導(dǎo)、示范、輻射、培訓(xùn)等多功能的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中心;2011年國(guó)務(wù)院印發(fā)的《社會(huì)養(yǎng)老服務(wù)體系建設(shè)規(guī)劃(2011—2015)》提出:在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層面,重點(diǎn)建設(shè)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托老所、老年人活動(dòng)中心、互助式養(yǎng)老服務(wù)中心等社區(qū)養(yǎng)老設(shè)施,推進(jìn)社區(qū)綜合服務(wù)設(shè)施,增強(qiáng)養(yǎng)老服務(wù)功能,使日間照料服務(wù)基本覆蓋城市社區(qū)。2013年9月國(guó)務(wù)院印發(fā)了《關(guān)于加快發(fā)展養(yǎng)老服務(wù)業(yè)的若干意見》,提出:為了更加積極地應(yīng)對(duì)人口老齡化,滿足老年人多樣化、多層次的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到2020年生活照料、醫(yī)療護(hù)理、精神慰藉、緊急救援等養(yǎng)老服務(wù)覆蓋所有居家老年人,社區(qū)服務(wù)設(shè)施覆蓋所有城市社區(qū)。
為了落實(shí)黨和國(guó)家的各項(xiàng)養(yǎng)老服務(wù)政策,全國(guó)各地都開展了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建設(shè)的探索實(shí)踐,也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是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發(fā)展整體上還是處于起步階段,仍然難以滿足日益增長(zhǎng)的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亟需探索創(chuàng)新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的供給模式,提高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度與滿意度的耦合,真正實(shí)現(xiàn)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的公平可及[1],促進(jìn)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的持續(xù)健康發(fā)展。
一、我國(guó)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發(fā)展中存在的主要問(wèn)題
(一)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設(shè)施單一、使用效率低
隨著我國(guó)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老年群體和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的差異性與多樣性進(jìn)一步加大,政府主導(dǎo)的標(biāo)準(zhǔn)化、機(jī)構(gòu)化的養(yǎng)老服務(wù)模式已無(wú)法滿足多樣性與差異性的服務(wù)需求,同時(shí)政府養(yǎng)老服務(wù)供給組織鏈條加長(zhǎng),服務(wù)難度也大大增加[2];我國(guó)城市社區(qū)公共服務(wù)設(shè)施大多是以戶籍人口為依據(jù)來(lái)配置的,在人口流動(dòng)加快、老齡化越來(lái)越嚴(yán)重的背景下,這一配置標(biāo)準(zhǔn)造成社區(qū)公共服務(wù)設(shè)施供給中老年服務(wù)類產(chǎn)品偏少,而且設(shè)施的配置與老年群體的空間分布不相匹配;目前,城市社區(qū)在娛樂(lè)文化設(shè)施和日常生活照料上的養(yǎng)老服務(wù)供給是最多的,但是依然存在著數(shù)量和質(zhì)量方面與實(shí)際需求相脫節(jié)的現(xiàn)象,有的城市社區(qū)建立了(居家)養(yǎng)老服務(wù)中心(站),內(nèi)設(shè)棋牌室、娛樂(lè)室、圖書室,老年人可以在此看電視,打牌下棋、喝茶聊天、看書讀報(bào),有的城市社區(qū)還有老年食堂,為60歲及以上老年人提供無(wú)償、低償、有償?shù)牟惋嫹?wù),許多城市社區(qū)還有戶外健身場(chǎng)地,設(shè)有一些簡(jiǎn)單的健身器材,但是很多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設(shè)施的數(shù)量偏少、樣式單一,而且長(zhǎng)時(shí)間不維修、存在安全隱患。有些活動(dòng)場(chǎng)所,由于不符合老年人的身體健康情況或與老年人的興趣不符而無(wú)法使用,造成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設(shè)施使用率低,迫切需要對(duì)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設(shè)施進(jìn)行適老性改造。
(二)醫(yī)療護(hù)理資源不足,服務(wù)人員專業(yè)水平低
醫(yī)療護(hù)理服務(wù)是老年人最迫切需要的養(yǎng)老需求,但是我國(guó)有的城市社區(qū)并沒(méi)有相應(yīng)的醫(yī)療護(hù)理設(shè)施與資源,有的社區(qū)雖然設(shè)立了社區(qū)衛(wèi)生服務(wù)室(站、所),但是還存在著醫(yī)療護(hù)理人員數(shù)量少、學(xué)歷職稱偏低、醫(yī)護(hù)場(chǎng)地狹窄、醫(yī)療設(shè)備簡(jiǎn)陋等問(wèn)題,醫(yī)護(hù)人員大多是中專和專科學(xué)歷、初級(jí)職稱,全科醫(yī)生嚴(yán)重偏少,專業(yè)水平與能力無(wú)法滿足社區(qū)老年人特別是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醫(yī)養(yǎng)需求。我們?cè)趯?shí)地調(diào)研中發(fā)現(xiàn),多數(shù)城市老年人對(duì)社區(qū)衛(wèi)生服務(wù)室(站、所)的印象是“技術(shù)水平不強(qiáng)、專業(yè)水平不足、醫(yī)療設(shè)備不夠”,老年人到社區(qū)衛(wèi)生服務(wù)室主要是量量血壓或一般感冒去開點(diǎn)藥,重病、大病、急病就會(huì)去到市里的大醫(yī)院看病,城市社區(qū)醫(yī)療護(hù)理水平不利于老年人在社區(qū)獲得及時(shí)有效的醫(yī)療服務(wù)。目前,城市社區(qū)的養(yǎng)老服務(wù)人力資源極度匱乏,一個(gè)社區(qū)的養(yǎng)老管理員一般只有一個(gè)人,而且大多數(shù)是身兼數(shù)職、極少有專職人員;養(yǎng)老服務(wù)人員大多是50歲以上的女性或低齡健康老年人,他們的文化水平、專業(yè)技能、工資水平都不高,工作的積極性不強(qiáng)、隊(duì)伍不穩(wěn)定,服務(wù)能力有限。endprint
(三)精神慰藉服務(wù)缺失,老年人的社會(huì)價(jià)值難以實(shí)現(xiàn)
隨著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發(fā)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城市社區(qū)老年人對(duì)精神慰藉、社會(huì)參與等精神層面的需求日趨迫切,需求呈現(xiàn)出多樣化與高層次的趨勢(shì)[3]。但目前我國(guó)社區(qū)為老年人提供的精神養(yǎng)老服務(wù)大多局限在休閑娛樂(lè)活動(dòng)上,忽視了老年人的親情需求和再就業(yè)需求。城市社區(qū)老年人在退休后,隨著社會(huì)地位的變化、自身的社會(huì)價(jià)值無(wú)法體現(xiàn),心理會(huì)有落差感,特別是空巢獨(dú)居老年人更容易產(chǎn)生壓抑感和空虛感,易發(fā)心理疾病,新聞報(bào)道中發(fā)生的老年人自殺事件從某個(gè)側(cè)面驗(yàn)證了老年人精神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的急迫性。據(jù)統(tǒng)計(jì),目前全國(guó)城市社區(qū)4000多萬(wàn)離退休老年人口中有500多萬(wàn)各種類型人才,僅有不到20%的人得以繼續(xù)發(fā)揮“余熱”[4],如果可以合理適當(dāng)?shù)貙?duì)老年人的社會(huì)價(jià)值進(jìn)行再開發(fā),不僅可以減少社區(qū)、家庭和政府的養(yǎng)老壓力,還能滿足城市社區(qū)老年人在精神上的需求,提升城市社區(qū)老年人的幸福指數(shù)。但目前我國(guó)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中老人群體的主體性問(wèn)題還沒(méi)有得到充分重視,在現(xiàn)實(shí)中面臨著老年人參與意愿強(qiáng)烈而缺乏參與機(jī)會(huì)的矛盾和困境。
二、我國(guó)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發(fā)展困境的主要原因
(一)供給主體單一、職責(zé)不明
目前,我國(guó)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的供給已開始呈現(xiàn)多元化的態(tài)勢(shì),其供給主體包括政府、市場(chǎng)、社區(qū)、社會(huì)組織、家庭等等,但政府仍然是最主要的推動(dòng)者與供給者,供給主體單一、職責(zé)不明,多元主體之間并沒(méi)有形成有效的合作供給機(jī)制。
在我國(guó)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的供給中,出現(xiàn)了政府職能的錯(cuò)位、越位;而參與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的市場(chǎng)主體不到位甚至缺失,市場(chǎng)的作用沒(méi)能得到應(yīng)有的發(fā)揮;現(xiàn)行的城市養(yǎng)老政策一直都倡導(dǎo)以社區(qū)為依托,但長(zhǎng)期以來(lái)我國(guó)城市社區(qū)在資金、制度、管理、人才等多方面對(duì)政府有著極大的依賴性,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行政化現(xiàn)象嚴(yán)重,無(wú)法完全獨(dú)立自主地根據(jù)社區(qū)老年人的需求來(lái)提供養(yǎng)老服務(wù);由于政府權(quán)力讓渡的空間有限、加上社會(huì)組織自身的問(wèn)題以及文化和制度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國(guó)社會(huì)組織的發(fā)展一直相對(duì)滯后、力量薄弱,在數(shù)量、資金、規(guī)模、專業(yè)化和社會(huì)公信力等方面都存在較大的問(wèn)題[5],社會(huì)組織參與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的深度和廣度都非常有限;隨著我國(guó)城市化、工業(yè)化的快速發(fā)展,城市家庭結(jié)構(gòu)日趨“核心化”“空巢化”,傳統(tǒng)的家庭養(yǎng)老服務(wù)功能正在弱化。
(二)需求表達(dá)渠道不暢、機(jī)制不完善
目前,我國(guó)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的供給是直接由社區(qū)居委會(huì)來(lái)具體實(shí)施的,而社區(qū)在我國(guó)現(xiàn)行的組織體制下,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政府的“附屬品”,導(dǎo)致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供給主體的行政化現(xiàn)象嚴(yán)重;由于政府權(quán)力下放的不徹底,基層政府依然承載了大量的社區(qū)公共服務(wù),實(shí)質(zhì)上成為了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的直接提供者和生產(chǎn)者。這樣就導(dǎo)致了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缺乏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力,也使得政府容易產(chǎn)生權(quán)力尋租現(xiàn)象;而政府主導(dǎo)的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資源是有限的,無(wú)法滿足社區(qū)老年人日益多樣化和個(gè)性化的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6]。與此同時(shí),我國(guó)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供給體制,把社區(qū)老年人排除在決策之外,決策主體的缺位導(dǎo)致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信息不完全、不對(duì)稱,需求表達(dá)渠道不暢、機(jī)制不完善,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的供給者和需求者之間缺少直接互動(dòng),這是導(dǎo)致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供需失衡的重要因素;在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的供給中還存在著老年人“搭便車”的心理,社區(qū)老年人參與的積極性不高,同時(shí),現(xiàn)有的城市社區(qū)不同于以往的單位制社區(qū),組織化程度低,甚至鄰里之間都互不相識(shí),難以形成有效的組織化表達(dá)機(jī)制,使得社區(qū)老年人難以真正獲得所需要的養(yǎng)老服務(wù)。
(三)呈現(xiàn)“碎片化”和不可及傾向
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供給的碎片化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gè)方面:一是管理部門的“碎片化”。目前,我國(guó)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供給是以民政部門為主,同時(shí)涉及到醫(yī)療衛(wèi)生、社會(huì)保障、財(cái)政、國(guó)土等多個(gè)政府部門,這些政府部門都掌握著一定的養(yǎng)老服務(wù)資源,但往往各自為政、互不干涉也難以協(xié)調(diào),實(shí)際上不但造成了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設(shè)施的重復(fù)建設(shè),導(dǎo)致養(yǎng)老服務(wù)資源不能有效配置,甚至存在著資源的嚴(yán)重浪費(fèi)。二是養(yǎng)老保障制度的“碎片化”。城市社區(qū)居民中存在著企業(yè)職工、城市居民、公務(wù)員與事業(yè)單位人員等不同群體的養(yǎng)老保障制度,他們的養(yǎng)老保障水平差異懸殊,甚至還有少數(shù)非就業(yè)的城市居民沒(méi)有任何的養(yǎng)老服務(wù)制度保障[7]。三是養(yǎng)老服務(wù)政策的“碎片化”。目前,民政、衛(wèi)生、國(guó)土等十多個(gè)部委都可以出臺(tái)與養(yǎng)老相關(guān)的政策,不同的養(yǎng)老保障和服務(wù)政策之間出現(xiàn)了斷裂,如不同城市的社區(qū)、企業(yè)與事業(yè)單位之間的養(yǎng)老政策存在著差異性、不同政府部門制定的養(yǎng)老政策分離甚至相互矛盾。
由于我國(guó)現(xiàn)有的養(yǎng)老服務(wù)有效供給不足,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重點(diǎn)保障的是“三無(wú)”、困難老年群體,沒(méi)能惠及城市社區(qū)所有老年人,而那些迫切需要養(yǎng)老服務(wù)、但卻沒(méi)在養(yǎng)老政策保障范圍之內(nèi)的其他老年人的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就難以得到滿足;絕大多數(shù)城市建設(shè)忽略了老年人的需求,如:老年人住老房子的較多,這些老房子有七成多沒(méi)有電梯,以致失能、高齡、患病老人的行動(dòng)非常不便;大多數(shù)城市基礎(chǔ)公共設(shè)施和建筑,象城市中的過(guò)街天橋、地下通道、公交車站、過(guò)馬路的信號(hào)燈,社區(qū)里的健身場(chǎng)所與器材等等都是針對(duì)健康、無(wú)殘疾的中青年群體而建造,忽視了老年人群體的生活、出行要求[8],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不可及傾向嚴(yán)重。
三、推進(jìn)我國(guó)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發(fā)展的機(jī)制
(一)明晰各類主體職責(zé),構(gòu)建“共擔(dān)、互補(bǔ)、共享”機(jī)制
要緩解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的困境,就必須明確界定政府、市場(chǎng)、社區(qū)、家庭等供給主體的職責(zé),構(gòu)建各主體在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中的“責(zé)任共擔(dān)、功能互補(bǔ)、利益共享”的機(jī)制。
政府首先要轉(zhuǎn)變職能。在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的供給中,應(yīng)該扮演的是政策的制定者、財(cái)政資金的提供者、服務(wù)輸送的監(jiān)督者,并對(duì)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承擔(dān)兜底責(zé)任,而不是不明職責(zé)的大包大攬,更何況僅憑政府一己力量根本無(wú)法滿足城市老年人日益增長(zhǎng)的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正如登哈特夫婦所言:“政府的作用在于:與私營(yíng)及非盈利組織一起,為社區(qū)所面臨的問(wèn)題尋找解決方法”,“其角色越來(lái)越不是服務(wù)的直接供給者,而是調(diào)停者、中介人甚至裁判員”,政府“有責(zé)任通過(guò)擔(dān)當(dāng)公共資源的管理員,公共組織的監(jiān)督者,公民權(quán)利和民主對(duì)話的促進(jìn)者,社會(huì)參與的催化劑等角色來(lái)為公民服務(wù)”[9]。endprint
社區(qū)在有效滿足城市老年人養(yǎng)老服務(wù)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僅最了解社區(qū)老年人的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而且也是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直接供給的平臺(tái)。為了更好地發(fā)揮社區(qū)的依托作用,政府必須分權(quán)于社區(qū),將更多的權(quán)力下放到社區(qū),實(shí)現(xiàn)社區(qū)組織的真正自治,應(yīng)使其“由政府的腿轉(zhuǎn)變成居民的頭”[10]。社區(qū)應(yīng)依據(jù)政府養(yǎng)老的相關(guān)政策要求,從城市社區(qū)老年人的實(shí)際需求出發(fā),結(jié)合社區(qū)的實(shí)際情況,協(xié)調(diào)整合政府和市場(chǎng)等其他主體提供的養(yǎng)老服務(wù)資源,充分發(fā)揮好社區(qū)作為養(yǎng)老服務(wù)供給的平臺(tái)作用,開展適合城市社區(qū)老年人的各項(xiàng)養(yǎng)老服務(wù)活動(dòng)。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的市場(chǎng)化供給,不僅能比較及時(shí)和準(zhǔn)確地把握城市社區(qū)老年人的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而且可以減輕政府在財(cái)政資金支持和養(yǎng)老服務(wù)供給上的負(fù)擔(dān),還可以推動(dòng)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向多樣化、專業(yè)化、個(gè)性化、高層次方向發(fā)展。政府要積極培育和發(fā)展非營(yíng)利性的社區(qū)服務(wù)機(jī)構(gòu)或中介服務(wù)組織,采用“購(gòu)買服務(wù)”“合同外包”“委托服務(wù)”等多種形式,鼓勵(lì)和支持資助多種社會(huì)力量開展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11]。
家庭養(yǎng)老在我國(guó)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的供給中有著不可替代的優(yōu)勢(shì),不僅有利于家庭關(guān)系的和諧穩(wěn)定、也符合老年人養(yǎng)老心理,還能節(jié)約公共財(cái)政和社會(huì)資源。正如習(xí)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春節(jié)團(tuán)拜會(huì)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我們要重視家庭建設(shè),發(fā)揚(yáng)光大中華民族傳統(tǒng)家庭美德,促進(jìn)家庭和睦,促進(jìn)老年人老有所養(yǎng)[12]。在我國(guó)未富先老的國(guó)情背景下,政府應(yīng)加大對(duì)家庭養(yǎng)老的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家庭養(yǎng)老服務(wù)的相關(guān)制度,增強(qiáng)家庭養(yǎng)老的能力,加大孝道文化的宣傳與教育,弘揚(yáng)中華傳統(tǒng)美德,充分發(fā)揮家庭在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中的基礎(chǔ)作用[13]。
(二)暢通需求表達(dá)渠道,構(gòu)建老年人積極參與的激勵(lì)機(jī)制
當(dāng)前,我國(guó)社區(qū)行政化的問(wèn)題嚴(yán)重影響和制約了我國(guó)城市社區(qū)自治的良性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到了社區(qū)作為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與供給交流溝通平臺(tái)作用的充分發(fā)揮,因此,需要政府進(jìn)一步發(fā)展和完善社區(qū)自治相關(guān)法律政策,實(shí)現(xiàn)行政化社區(qū)向自治型社區(qū)的強(qiáng)制性制度變遷,正確處理政府行政權(quán)力和社區(qū)居民自治權(quán)利之間的關(guān)系,充分發(fā)揮城市社區(qū)作為自治組織渠道的需求表達(dá)功能;同時(shí)更需要社區(qū)居民的自治精神,實(shí)現(xiàn)制度的誘致性變遷[14]。
2002年聯(lián)合國(guó)《馬德里老齡問(wèn)題國(guó)際行動(dòng)計(jì)劃》,確立“獨(dú)立、參與、照顧、自我實(shí)現(xiàn)、尊嚴(yán)”為21世紀(jì)老齡問(wèn)題行動(dòng)計(jì)劃的基本原則,將老年社會(huì)參與正式納入“積極老齡化”發(fā)展戰(zhàn)略,成為應(yīng)對(duì)21世紀(jì)人口老齡化的政策框架。因此,城市社區(qū)老年人養(yǎng)老服務(wù)供給中,必須強(qiáng)化城市社區(qū)老年人在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供給決策中的主體地位,鼓勵(lì)社區(qū)老年人積極表達(dá)意愿,提高社區(qū)老年人需求表達(dá)的權(quán)利意識(shí)和能力,創(chuàng)造條件讓老年人參與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事務(wù)的管理;完善社區(qū)老年人現(xiàn)有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表達(dá)渠道的制度安排,充分發(fā)揮城市社區(qū)的人大、政協(xié)等表達(dá)渠道的功能,將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履職責(zé)任與社區(qū)老年人的需求表達(dá)和利益維護(hù)直接掛鉤,通過(guò)影響政府養(yǎng)老服務(wù)政策的制定,保障社區(qū)老年人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表達(dá)權(quán)利的實(shí)現(xiàn);提高社區(qū)老年人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表達(dá)的組織化程度,社區(qū)老年人要能有效將自己的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和權(quán)利訴求表達(dá)輸入到民主社會(huì)的政治制度中,就只能靠社會(huì)化的組織而不是“原子化”的個(gè)人。為提高社區(qū)老年人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表達(dá)的有效性,增強(qiáng)社區(qū)老年人整體利益表達(dá)和博弈的能力,就必須建立和培育能代表社區(qū)老年人養(yǎng)老服務(wù)利益的各種社區(qū)組織,包括基層老年協(xié)會(huì)以及各種非營(yíng)利性組織,建立“上下結(jié)合”的需求表達(dá)機(jī)制,拓寬表達(dá)渠道,實(shí)現(xiàn)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供給與需求的動(dòng)態(tài)平衡。
(三)祛除“碎片化,構(gòu)建養(yǎng)老服務(wù)無(wú)縫隙供給機(jī)制
為了提高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的滿意度,實(shí)現(xiàn)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的需求與滿意的耦合,必須祛除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供給中的“碎片化”和“不可及性”,構(gòu)建以政府、市場(chǎng)、社區(qū)、家庭等各方多元主體合作供給的新格局。
首先是政府各部門之間的相互協(xié)調(diào)與合作。在實(shí)地調(diào)研中我們發(fā)現(xiàn),醫(yī)療保健服務(wù)是城市社區(qū)老年人特別是高齡、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但單憑民政部門的力量是無(wú)法滿足這一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的;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供給中存在的最大的問(wèn)題是資金的短缺、土地的審批等最需要民政、財(cái)政、國(guó)土資源等各部門相互配合才能解決的問(wèn)題;城市養(yǎng)老服務(wù)的基礎(chǔ)設(shè)施的改造與建設(shè)需要,民政、城建、國(guó)土等多部門間的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等等。
其次是各類養(yǎng)老政策與制度的協(xié)議與統(tǒng)一。現(xiàn)有的城市社區(qū)不同于原有的單位社區(qū),在我國(guó)現(xiàn)有的社區(qū)老年人口中,有離退休人員、企業(yè)職工、失地農(nóng)民等老年群體,這三類老年人他們一般都有養(yǎng)老保險(xiǎn)和醫(yī)療保險(xiǎn),但享有的醫(yī)療保障與服務(wù)的待遇是有差異的。隨著人口流動(dòng)和城市化進(jìn)程的加快,在城市社區(qū)老年人中還有一部分老年人,為了子女照顧孫輩遠(yuǎn)離家鄉(xiāng)來(lái)到了陌生的城市,這一部分老年人被稱為老漂族,這一部分被稱為老漂族的老年人因?yàn)閼艏辉谒幼〉某鞘猩鐓^(qū),根本無(wú)法享受城市社區(qū)所提供的養(yǎng)老服務(wù),在我國(guó)現(xiàn)有的養(yǎng)老政策與制度中還是空白。因此,應(yīng)從戰(zhàn)略的高度制定針對(duì)不同老年群體分類、分層次為城市社區(qū)所有老年人提供無(wú)償、低償、有償?shù)酿B(yǎng)老服務(wù),出臺(tái)相關(guān)政策,做出制度安排。
最后是構(gòu)建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多元主體合作供給的格局。在我國(guó)城市社區(qū)老齡化快速發(fā)展的現(xiàn)實(shí)情況下,單憑政府、市場(chǎng)、社區(qū)、家庭等其中的一個(gè)主體是無(wú)法滿足日益增長(zhǎng)的多樣化、個(gè)性化的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需要在全社會(huì)合理調(diào)配養(yǎng)老服務(wù)的資源,促進(jìn)養(yǎng)老服務(wù)信息資源的共享,加強(qiáng)養(yǎng)老服務(wù)內(nèi)容、方式、渠道的整合。
總之,要實(shí)現(xiàn)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與滿意的耦合,需要打破“碎片化”供給模式下的管理組織的壁壘、政策制度的藩籬和各供給主體的自我封閉狀態(tài)。既要強(qiáng)化政府各部門之間,民政部門內(nèi)部各科(室)之間的職能協(xié)調(diào)與資源整合,更要促進(jìn)政府、市場(chǎng)、社會(huì)、家庭等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供給主體之間的信任與合作,構(gòu)建無(wú)縫隙、一體化的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wù)模式,已成為當(dāng)前解決我國(guó)越來(lái)越嚴(yán)重的城市老年化問(wèn)題的發(fā)展方向[15]。endprint
參考文獻(xiàn)
[1]席 恒.分層分類:提高養(yǎng)老服務(wù)目標(biāo)瞄準(zhǔn)率[J].學(xué)海,2015(1):80-87.
[2]湯艷文.養(yǎng)老服務(wù)的社會(huì)組織與管理:上海經(jīng)驗(yàn)[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4:9-19.
[3]耿亞男,宋言奇.城市老齡化時(shí)代社區(qū)養(yǎng)老的新路徑——基于蘇州地區(qū)的實(shí)地調(diào)研[J].上海城市管理,2011(1):69.
[4]齊連青.老齡人口需求與供給狀況分析——以山東省為例[J].中國(guó)集體經(jīng)濟(jì),2013(15):95.
[5]胡 薇.政府購(gòu)買社會(huì)組織服務(wù)的理論邏輯與制度現(xiàn)實(shí)[J].2012(6):129-136.
[6]錢 林.中國(guó)城市社區(qū)公共服務(wù)的轉(zhuǎn)型:從供給導(dǎo)向走向需求導(dǎo)向[J].安徽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3(4):50.
[7]俞 琪.省民進(jìn)團(tuán)體提案認(rèn)為應(yīng)該解決養(yǎng)老保障“碎片化”的問(wèn)題[N].浙江老年報(bào),2013-02-01(0001).
[8]王亦君,關(guān)爾佳.老齡政策碎片化不能只當(dāng)滅火隊(duì)[N].中國(guó)青年報(bào),2013-02-28(02).
[9]珍妮特·V·登哈特,羅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務(wù):服務(wù),而不是掌舵[M].丁煌,譯.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1:5-7.
[10]雷玉明,曹博,李靜.公共服務(wù)型政府視野中城市社區(qū)養(yǎng)老合作共治模式——以南京市玄武區(qū)為例[J].華中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3(4):113-118.
[11]董紅亞.中國(guó)社會(huì)養(yǎng)老服務(wù)體系建設(shè)研究[M].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11:99.
[12]習(xí)近平.在2015年春節(jié)團(tuán)拜會(huì)上的講話(全文)[EB/OL].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50218/19315928.html.
[13]葛啟慧,班曉娜.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回歸家庭養(yǎng)老的路徑選擇[J].商業(yè)經(jīng)濟(jì),2014(6):19-21.
[14]陳 斌.論城市社區(qū)行政化的路徑依賴與制度變遷[J].廣西社會(huì)主義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1(5):78-81.
[15]譚海波,蔡立輝.論“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路徑——“整體型政府”的分析視角[J].社會(huì)科學(xué),2010(8):12-18.
責(zé)任編輯 陸 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