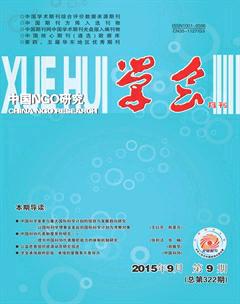中國科學家參與重大國際科學計劃的現狀與發展趨向研究
王以芳+ 韓晉芳
[摘 要]我國科學家自上世紀80年代起就開始參與國際科學理事會發起的一系列重大國際科學計劃。本文在對我國科學家參與國際科學計劃的歷史、現狀與參與模式進行梳理的基礎上,探尋我國科學家未來參與國際科學計劃的發展趨向,以期為我國科學家參與民間國際科技合作,不斷提升我國國際科學地位提供借鑒經驗。
[關鍵詞] 國際科學理事會 國際科學計劃 國際科技合作
國際科學計劃作為一種跨區域、跨學科,由國際非政府組織發起的全球性科學計劃,“以其科學上的先進性和權威性吸引世界各國科學家的參與,并通過各種途徑獲得經費支持開展合作研究,從而引起科學領域的飛躍發展”[1]。自上世紀80年代起,我國科學家開始參與各種國際科學計劃,它為我國科學家參與民間國際科技合作,促進我國科技快速發展,擴大國際科技話語權提供了重要平臺。本文以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簡稱ICSU)發起①的重大國際科學計劃為考察對象,對中國科學家參與其國際科學計劃的現狀、模式和影響進行梳理,以期為我國科學家積極參與民間國際科技合作,努力提升我國國際科學地位提供借鑒經驗。
一、 ICSU發起的國際科學計劃
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組織及國際學術組織之一,成立于1931年,前身為國際研究理事會(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98年4月改名為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會員網絡遍布全球,目前擁有31個科學聯合會會員,23個國際科學協會和121個國家會員。ICSU作為全球性的國際學術組織,致力于促進科學的國際交流,協調各個國際性科學協會及國家科學組織的活動,尤為關注自然科學中各學科和各國科學界共同關心的問題。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ICSU利用廣泛的會員網絡,以跨學科、跨機構、跨區域合作的形式,發起了一系列重大的國際科學計劃,在國際研究和政策評估方面做出了許多重要貢獻。
其中,全球環境變化研究(簡稱GEC)是ICSU最為關注的領域,該研究旨在推動全球科學家在全球變化科學領域的整體性、交叉性研究,由世界氣候研究計劃(WCRP)、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IGBP)、國際生物多樣性計劃(DIVERSITAS)和國際全球環境變化人文因素計劃(IHDP)4個國際科學計劃組成。世界氣候研究計劃(WCRP)是4大計劃中最早發起的一個國際科學計劃,于1980年正式確立,ICSU、世界氣象組織(WMO)和后來加入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政府間海洋委員會(IOC)成為WCPR的共同發起人,該計劃的主要目標是增強人類對氣候的認識,探索氣候的可預報性及人類對氣候的影響程度,包括對全球大氣、海洋、海冰與陸冰以及地表的研究,包括熱帶海洋和全球大氣計劃(TOGA)、世界海洋環流試驗計劃(WOCE)、氣候與冰凍圈計劃(CLIC)、氣候變動與可預報性研究計劃(CLIVAR)、地球系統的協同觀測和預報計劃(COPES)等子計劃[2]。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IGBP)是1986年ICSU發起的一個計劃,主要從地球的系統結構出發,對整個地球系統的維持機制和變化規律,物理過程、化學過程和生物過程的相互作用,人類干預和影響地球的變化,以及預測地球系統變化的能力等問題進行研究。2004~2013年,IGBP進入到第二研究階段,主要針對地球系統的三個主要結構——海洋、陸地和大氣、針對海氣、陸氣和海陸界面,以及針對地球系統的整體動態進行研究, 先后形成了國際全球大氣化學計劃(AIMES)、全球土地計劃(GLP)、國際全球大氣化學計劃(IGAC)等8個核心研究計劃[3]。隨著全球環境變化研究的深入,1996年ICSU又加入了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IUBS)和環境問題科學委員會(SCOPE)共同發起的國際生物多樣性計劃(DIVERSITAS),并于同年正式形成了國際生物多樣性計劃。該計劃是生物多樣性方面最具影響力的國際計劃,包括生物多樣性的發現 、生態服務功能、生物多樣性的可持續利用三大核心科學計劃,以及生物健康、農業與生物多樣性、淡水生物多樣性等組成的跨學科交叉網絡計劃[4]。與國際生物多樣性計劃同年,ICSU在國際科學聯盟理事會(ISSC)發起的人文因素計劃(HDP)基礎上,形成了國際全球環境變化人文因素計劃(IHDP)②。IHDP主要研究闡明人類-自然耦合系統,探索個體與社會群體如何驅動局地、區域和全球尺度上發生的環境變化、影響,以及如何減緩和響應這些變化,先后發起了地球系統治理計劃(ESGP)、土地利用/土地覆蓋變化(LUCC)、全球環境變化的制度因素(IDGEC)等10個核心科學計劃[5]。
2012年,在4大計劃研究成果的支撐下,催生了一個全新的、綜合性的如何應對全球可持續性地球系統研究的總體計劃——未來地球計劃(Future Earth)。未來地球計劃是在2012年6月召開的“里約+20”峰會上由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國際社會科學理事會(ISSC)發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聯合國環境署(UNEP)、聯合國大學(UNU)、貝爾蒙特論壇(Belmont Forum)和國際全球變化研究資助機構(IGFA)等共同組織的一個為期10年的國際科學計劃(2014~2023)[6]。該計劃致力于研究解決糧食、水資源、能源、健康和人類安全等可持續發展領域的關鍵問題及他們之間的關系,以滿足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的需求[7],為各國政府制定、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提供理論知識和行動依據。目前,未來地球計劃設置了動態的地球、全球發展和向可持續發展的轉變3個研究方向。未來地球計劃是在全球環境變化項目(GEC)的基礎上提出的,它為21世紀的全球環境變化研究提供一個全新的、全方位的框架。
21世紀初,ICSU還發起了災害風險綜合研究計劃(IRDR)和城市環境與健康福祉計劃。災害風險綜合研究計劃是2008年由ISCU與國際社會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ISSC)共同發起的一項為期10年的國際科學計劃。該項目的總體目標是聯合各國自然科學、社會經濟、衛生和工程技術等領域的專家共同應對自然和人類引發的環境災害的挑戰,提高各國應對災害的能力,減輕災害的影響,改進決策機制[8]。目前,IRDR共啟動了4個核心項目:災害風險綜合研究評估(AIRDR)、災情數據項目(DATA)、災害風險典型案例研究項目(FORIN)、風險詮釋與行動研究項目(RIA),以及亞洲減災合作項目(IAP)、社會和經濟研究與應用工作小組(WG-SERA)兩個合作項目[8]。 2011年,ISCU又發起一項為期10年的城市環境與健康福祉計劃,旨在應對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及復雜城市環境所帶來的健康問題,通過各國際科學組織的聯系,利用實際獲得的數據促進多學科的合作研究,建立揭示城市變化與健康的復雜性,提出減緩健康風險的政策措施[9]。endprint
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ICSU充分利用國際非政府學術組織的優勢,吸引全世界自然科學界各個領域的科學家對與人類社會息息相關的科學問題進行研究。其開展的國際研究與合作不僅引領了環境變化科學研究的方向,對于各國政策的制定和評估也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我國科學家參與ICSU發起的國際科學計劃的模式
我國科學家自上世紀80年代起就開始參與了ICSU發起的全球環境科學研究系列的科學計劃。特別是在1982年后,中國科協代表我國成為ICSU的團體會員單位,為我國科學家參與國際民間科技合作搭建了合作的橋梁。我國科學家主要通過建立國際科學計劃國家委員會和承辦國際項目辦公室等模式參與到ICSU發起的國際科學計劃中。
上世紀80年代,隨著全球變化科學研究的逐步興起,氣候變化研究在我國科學界得到重視。ICSU發起的世界氣候研究計劃成立后,我國科學家積極組織參與該計劃,于1985年成立了世界氣候研究計劃中國國家委員會(Chines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WCRP ,簡稱CNC-WCRP),成為世界上最早成立的WCRP國家委員會之一。WCRP中國委員會主要負責組織協調中國科學家參與WCRP工作,促進中國氣候和環境研究與國際相關領域的合作與交流。1988年,我國成立了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中國全國委員會(CNC-IGBP)。2004年以來,相繼成立了國際生物多樣性計劃中國國家委員會(CNC-DIVERSITAS)、國際全球環境變化人文因素計劃中國國家委員會(CNC-IHDP)、災害風險綜合研究計劃中國委員會(IRDR-CHINA)、未來地球計劃中國國家委員會(CNC-FE)加入到DIVERSITAS、IHDP、IRDR和FE當中。國際科學計劃中國國家委員會(簡稱“中委會”)在各自領域發起了一系列研究項目,組織我國科學家在關鍵領域開展研究。如FE中委會根據FE計劃的總體框架制定了環境污染及健康,城鎮化與社會和諧發展,季風區氣候變異與人類活動,全球變化及關鍵區響應,食品、能源供給與未來發展,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產業轉型與綠色生產,變化環境下的災害預警,東亞傳統文化與可持續發展,極區可持續發展,地球系統觀測和知識服務,地球系統模式,氣候經濟模式與氣候變化科學決策等12個關鍵領域,引領我國科學家開展相關研究[10]。IRDR中委會面向我國科學家發布了中國災害損失數據的組織模式研究、中國災害風險典型案例研究(FORIN-CHINA)、中國自然災害的全球交互影響機制研究等項目[11]。
隨著合作的不斷深入,我國科學家還通過承辦國際項目辦公室的方式參與到國際科學計劃的管理和執行層面。2009年11月和2011年11月,我國組建了災害風險綜合研究計劃國際項目辦公室(International Program Office,簡稱IPO)和城市環境與健康福祉計劃國際項目辦公室,辦公室分別設在中科院對地觀測與數字地球科學中心和在廈門的中國科學院城市環境研究所。國際項目辦公室在國際科學計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按照國際科學計劃的整體規劃,國際項目辦公室一般設在科學委員會下,主要負責調動全球資源為科學委員會提供支撐,協助項目及相關活動在全球開展和實施,并負責對外宣傳和推廣項目。承辦國際項目辦公室,一方面加大了我國科學家參與國際科學計劃的管理和執行;另一方面也為我國構建和運作高水平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平臺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總的來看,國際科學計劃中國國家委員會主要是作為中國科學家與國際科學計劃的橋梁,主要目標在于鼓勵我國科研人員、研究機構參與國際科學計劃的總體設計,在國家層面設立我國科學家參與該項目的總體目標、策略和規劃,幫助協調國家研究戰略,協調我國科學研究團體、決策者、非政府組織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參與計劃,充分利用國際計劃取得的成果,提高我國在該領域的科研水平,推動我國科學家有組織、有計劃地參與相關學術交流活動。而承辦國際項目辦公室則是參與國際科學計劃的管理,作為國際科學項目的執行機構,為國際科學計劃科學委員會提供支撐,協助項目及相關活動在全球開展,并負責對外宣傳和推廣項目,推動實現國際項目的既定目標。
通過多種方式,我國科學家廣泛參與到國際科學計劃的學術交流、科學研究和項目管理工作,在很多領域發揮了積極作用,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提升了我國在國際科技領域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我國科學家主導的項目陸續成為WCRP支持的科學項目,如“南海季風試驗研究”成為CLIVAR計劃和GEWEX計劃的重要內容和科學項目;“淮河流域能量和水分循環的觀測研究”成為 WCRP/GEWEX計劃的科學項目; “中國重大氣候災害的形成機理及預測理論研究”成為CLIVAR科學項目[2]。 在IGBP計劃中,我國科學家開展的中國東北樣帶(NECT)、國際環球環境大斷面(PEP-II)、淮河流域能量和水分循環試驗、國際上第一個陸架海洋通量項目——東海陸架邊緣海洋通量實驗與近海海洋生態系統動力學研究[12]等成為IGBP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科學家結合IGBP研究計劃,在古環境、陸地生態系統、生物圈在水循環中的作用、全球大氣化學、全球海洋通量、全球能量與水分循環試驗、全球氣候變異與預測以及海洋生態系統動力學等方面做出了具有國際影響的研究,其中我國科學家在世界上開展的一系列大型全球性科學實驗受到關注,被譽為世界上對國際“海洋大氣耦合響應實驗”(TOGA-COARE)貢獻最大的兩個國家之一[12]。在DIVERSITAS計劃中,我國科學家與全球森林生物多樣性監測網絡于2004 年進行合作,建立了中國大型樣地的森林生物多樣性監測網絡(CForBio),對森林生物多樣性監測在溫帶的發展有重要的推動意義[13]。
我國科學家還積極在國際科學計劃的組織機構中任職,充分發揮主導作用。秦大河院士曾擔任IGBP科學指導委員會成員,現擔任FE計劃科學委員會委員;陳宜瑜院士曾擔任DIVERSITAS計劃科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姚檀棟院士擔任FE計劃籌劃小組成員;郭華東曾擔任IRDR科學家科學委員會委員;朱永官研究員擔任城市環境與健康福祉計劃科學委員會委員。另據不完全統計,20多位中國科學家在WCRP及子科學計劃中任職主席、委員或協調員,10多位中國科學家在IGBP或子科學計劃中任職主席、委員或中國區大使。endprint
與此同時,我國還承辦了一系列國際科學計劃的重要國際會議。如IRDR中國國家委員會分別于2011年10月和2014年6 月,在北京舉辦了第一屆(IRDR 2011)和第二屆災害風險綜合研究國際會議(IRDR 2014);FE中國國家委員會分別于2013年9月和2014年6月在北京舉辦了“未來地球計劃在中國”國際研討會、未來地球計劃與未來地球計劃中國國家委員會聯合研討會。這些國際會議一方面,加深了國際科學計劃中委會與國際層面的深層次溝通與合作;另一方面,促進了國際科學計劃在中國的開展和實施。
三、 中國科學家參與國際科學計劃的發展趨向
我國科學家積極參與國際科學計劃,在多個領域取得了很大進展,但從整體來看,我國科學家在國際科學計劃中仍不占主導地位。大部分國際科學計劃往往由歐美發達國家的科學家主導提出,我國科學家在科學計劃研究方向的確定、計劃的制定以及計劃的決策執行層面并不掌握實質性的話語權。為改變這一狀況,我國科學家正從多層面進行謀劃,爭取在國際科學計劃中發揮主導作用。總的來看,我國科學家參與國際科學計劃呈現出以下幾大發展趨向。
(一)積極發揮主導作用,自主倡導以我國科學家為主的子計劃
在以往的實踐中,中國委員會多以國際科學計劃的核心項目為框架,形成相對應的中國項目研究小組,如IGBP中國委員會根據IGBP的核心計劃,設立了GAIM工作組、PAGES工作組、LUCC 工作組、RS/DIS工作組、JGOFS/LOICZ工作組、BAHC工作組、GCTE工作組、TPGC工作組、GLOBEC工作組、SOLAS工作組等10個工作組和IC-GCS信息中心開展工作[14]。就整體情況來看,中委會在國際計劃的框架內積極參與相關領域的研究,但并未主導研究方向。但就我國科技發展的現狀來看,我國科學家在很多領域已經做出了相當出色的科研成果,如我國科學家成功研制出全球首套30米分辨率地表覆蓋數據集GlobeLand30,這套數據集涵蓋了全球陸域范圍和2000年和2010年2個基準年,包括水體、耕地和林地等10大類地表覆蓋信息,提供了全球地表覆蓋空間分布與變化的詳盡信息,為全球變化研究和可持續發展規劃等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數據,目前已有80多個國家上千名用戶下載了6萬多幅數據。與美國和歐盟研發的分辨率為1000米和300米的全球地表覆蓋數據產品相比,我國研發的30米分辨率地表覆蓋數據集領先國際水平。我國科學家正以此為契機,籌劃打造未來地球的科學數據平臺,計劃發起由中國科學家起支撐作用的科學計劃,與國際社會共同分享、共同深化數據成果,以期做出國際科技貢獻。
(二)深入參與國際科學計劃的管理組織工作,在國際科技組織中不斷發出我國科學家的聲音,提升我國在國際科技界的話語權
在國際科學計劃中,管理機構一般由科學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等組成,這些管理機構,尤其是科學委員會決定著科學計劃的研究方向,在現有項目的評審、建立新的科學主題、發起學術活動等方面起決定作用。在過去幾年中,我國非常重視中國科學家在國際科技組織中擔任職務,發揮我國科學家的主導作用。參與國際科學計劃的核心管理工作,有助于提升我國在國際科技界的話語權。目前,姚檀棟院士、秦大河院士、郭華東院士、朱永官研究員等分別在FE、IRDR和城市環境與健康福祉計劃科學委員會或籌備委員會中擔任委員。除爭取我國科學家在國際計劃中任職外,還應充分發揮國際項目辦公室的作用,它是保障國際科學計劃的實施運行的組織機構,在研究方向和實施方案的確定和管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國際項目辦公室,可以將本國科學家的思想同國際科學計劃更緊密地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我國在科學計劃中的主導作用[1]。
(三) 以我國為主發起重大國際科學計劃
早在2006年,中國科學院院士葉篤正、符淙斌曾發文呼吁建立和實施交叉科學的重大國際計劃已經成為推動科學技術發展的一項重要舉措,我國應提出并主持幾項國際科技計劃,提升我國在國際科學領域的地位[1]。從全球化的角度來看,科學研究正日益趨向國際化,全球范圍的合作越來越緊密;從國際科學計劃自身的特點來看,它提供了一個綜合性、跨學科的國際交流平臺,通過這個國際化平臺,不僅可以吸引全世界的優秀科學家開展相關領域的研究,而且可以吸引政府、企業、資助機構、用戶等利益攸關者協同設計、協同實施、協同推廣科研成果和解決方案,將科學成果最大限度地用于改善人類社會。回顧歷史,歐美主要國家從上世紀就開始通過各種非政府組織推出國際科學計劃,以科學上的先進性和權威性引領世界各國科學家參與,引領相關領域科學研究的方向。日本也曾于上世紀80年代通過通產省工業科學技術局總監的咨詢機構技術與國際交流委員會提出了一項國際科學計劃——人類新領域科學計劃(HFSP)[15],多次將計劃提交西方首腦會議,將該計劃推向國際社會,以期加強日本的國際科學地位。
隨著我國整體國力顯著增強,我國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一些科學研究領域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同時,我國當前整體科研隊伍國際化水平日益增強,在國際科研領域較為活躍的科學家和科研機構層出不窮,在此背景下,選擇我國科研優勢領域,瞄準對人類可能產生重大影響的前沿科學領域,以我國為主,提出并主持幾項國際科學計劃,搭建高水平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平臺,對于我國吸收國際一流科學力量,推動我國科技“走出去”戰略,在更廣泛的范圍做出國際科學貢獻,提升我國的國際科學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①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國際科學計劃一般由一個或多個非政府組織共同發起,但ICSU是唯一的共同發起組織,中國科協是ICSU的組織會員,中國科學家通過ICSU參與這些國際科學計劃。
②2006年,聯合國大學(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也成為IHDP的組織者之一。
參考文獻
[1]葉篤正,符淙斌.中國應有重大國際科學計劃[N].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6-01-10.
[2]世界氣候研究計劃中國委員會 [EB/OL]. WCRP中國委員會成立二十周年慶祝暨學術研討會.http://www.cnc-wcrp.org.
[3]IGBP-Project. http://www.igbp.net.
[4]DIVERSITAS. http://www.diversitas-international.org/.
[5]IHDP. http://www.ihdp.unu.edu/organigramme/?cat=cp.
[6]Future Earth. http://www.futureearth.org/who-we-are.
[7]未來地球計劃過度小組.未來地球計劃初步設計[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8]IRDR. http://www.irdrinternational.org/.
[9]http://www.icsu.org/what-we-do/interdisciplinary-b
odies/health-and-wellbeing-in-the-changing-urban-environment/.
[10]FE中國國家委員會[EB/OL].http://cnc-fe.cast.org.cn/article/273.html.
[11]災害風險綜合研究計劃中國委員會[EB/OL].http://
www.irdrchina.cn/cn/.
[12]陳宜瑜,陳泮勤,葛全勝,等.全球變化研究進展與展望[J].地學前緣,2002, 9( 1):11-18.
[13]孫鴻烈,陳宜瑜,于貴瑞,等.國際重大研究計劃與中國生態系統研究展望[J].地理科學進展,2014,33(7): 865-873.
[14]IGBP中國委員會[EB/OL] .http://www.igbp-cnc.org.cn.
[15]方志鵬.日本的人類新領域國際科學計劃[J].世界研究與發展,1992(3):16-1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