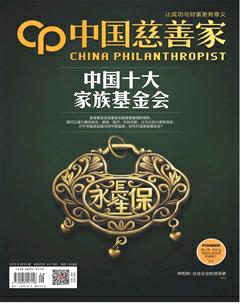戰時難民所并非天堂,但它閃耀人性光輝
白筱
難民收容所—這一詞匯無疑有著難以一語道盡的悲憤與凄苦,但它也同時閃耀著人性的良善光芒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自此,中國開始14年抗戰。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中國進入全面抗戰。隨著戰事擴大,中華大地處處創痕。大量難民流離失所,為避戰火四處遷逃,饑無食,渴無飲,呼兒喚女,處處哀嚎。他們要得到的,不過是一個容許他們活下去的居所。
歷史的車輪總是向前滾動,正義毫無懸念地終將戰勝邪惡,而時代的厄運卻只能由時代中的個體來承受。
難民收容所—這一詞匯無疑有著難以一語道盡的悲憤與凄苦,但它也同時閃耀著人性的良善光芒。
官民協力
2015年8月11日,兩張抗戰相關電子地圖在滬發布,分別是《上海淞滬抗戰分布圖》《上海抗戰慈善救助分布圖》,制圖者是上海師范大學傳播學院院長、教授蘇智良和他的幾位學生。此前,蘇智良已發布一張《上海抗日救亡分布圖》,8月末,他還將再發兩張。這一套五張地圖從年初開始制作,但準備時間已有8年之久。
“我們做上海抗戰數據庫已經做了8年。制圖過程當然必須要很嚴謹,一個點一個點逐個考證。”蘇智良告訴《中國慈善家》。
在《慈善救助分布圖》中共有89個數據點,每個數據點對應一個難民所。其中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設立的難民所超過20處,而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期間則有60多個。
整個抗戰期間,中國戰區及后方共出現難民所多達數千個,這些難民所的設立過程很難找到明顯規律。從數量上看,除了1937年前出現少量難民所之外,自全面抗戰爆發到抗戰結束的八年中,難民所總體呈突然爆發、隨后由多漸少的態勢發展。從分布情況來看,難民所大致隨難民流向而出現。
1932年初,日軍入侵上海,上海民間團體、同鄉會等力量便已自發設立難民所收救難民。1937年上半年,官民合辦組織“上海市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成立。8月14日,該會開始在滬設置收容所,此后,該會又下設“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統籌辦理難民的收容、救濟工作。至1940年,該會先后設置收容所50多處。
1937年八·一三槍聲打響后,上海附近聚集難民超過百萬,有70萬人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避難。上海國際救濟會在淞滬會戰爆發之日成立,緊急籌辦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上海也隨之形成了上海市救濟委員會、上海市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和上海國際救濟會三大難民救濟體系。一些廟宇、祠堂、會館、寺廟、教堂及一些私人場所亦紛紛設立難民所,雖設備簡陋,但應急及時。
與此同時,北平佛教急振會也在城內開辦難民所十余處。隨著華北、華東大片國土淪陷,戰區難民大量逃往武漢地區。
據國民政府1938年4月統計,武漢三鎮設立難民所超過百所,占全國同期總數的十分之一以上。其中,武漢振濟委員會主辦的難民所近20所,且其規模較大,最大的難民所可容納近8000人,收容總量占武漢地區60%以上,其余難民則由數量眾多的民辦難民所收容救助。武漢保衛戰開始后,難民又向大后方涌動。
除上述城市,廣東、廣西、福建等省份也陸續出現難民所。
1937年9月,國民政府頒布《非常時期救濟難民辦法大綱》,規定收容機構招收“無工作能力者”,并要求“各級地方政府分別建立收容難民的救濟院所”,對難民“施以臨時的給予食宿暫時安頓辦法”,開辦經費則“首為地方救災準備金及動用積谷、并募集之捐款,不足之處由中央補撥”。自此,收容所成為政府救濟機關的必備機構而迅速廣布全國。
從難民所設立方來看,主要為政府救濟機構、民間組織和社會團體等,并形成了官民協力救援的整體態勢。這其中,民間力量無疑是最為重要的部分,而在華外籍慈善人士為中國難民提供的庇護尤為關鍵。
1937年11月,在法國神父饒家駒的推動下,上海租界外設立南市難民區,世界現代史上第一個戰爭時期的平民安全區—“饒家駒區”在滬誕生。自1937年創立到1940年6月停辦,南市難民區收容難民逾30萬人。
1937年12月,南京金陵大學董事會董事長杭立武、歷史學系教授貝德士等中西方人士,參照上海南市難民區模式,建立南京安全區,主席即是如今為世界所熟知的拉貝。該安全區存在僅半年時間,收容難民達25萬人。
1938年10月26日,武昌淪陷,2萬難民逃入東湖衛生療養院,美國人鮑因頓為他們提供庇護,并組織施粥及衛生防疫。
世界的上海模式
饒家駒被稱為“難民之父”“中國之友”,因為只有一只手臂,他也常被稱為“獨臂神父”。他開創的難民救助上海模式推動了《日內瓦第四公約》的訂立,使得戰時保護平民成為各國的共識。
更重要的是,他在上海創立的難民區庇護了至少30萬中國難民,而這一模式被南京、漢口、廣州乃至法國、德國效仿,使更多人得以在殘酷的戰爭中保存生命。這無疑為人類歷史的發展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淞滬會戰爆發,中日兩國先后投入近百萬兵力,這一幾近于互賭國運的大戰異常慘烈,人稱“絞肉機”,給上海這一國際都市造成重大傷害。難民紛紛逃往沒有硝煙的租界,但租界難以接納。因南市為上海老城區,空房較多,很多難民聚集于此。
這年11月,饒家駒先是說服上海市市長俞鴻鈞,在南市劃出一塊區域接納難民,接著又與日軍斡旋,說明情由,日軍也表示同意。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準設立南市難民區。
南市難民區南以方浜路為界,北臨民國路(今人民路),呈半圓形。11月9日正式成立當天便在城隍廟、豫園、小世界等場所建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2萬人。大量難民隨之遷入,很快人數便超過10萬。
為加強難民區管理,難民區建立監察委員會,饒家駒任主席。南市難民區被分為九個區,每個區各設區長一名。
難民生活開銷全都壓在饒家駒肩上。他到處募款,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支持和上海慈善機構及企業的捐贈,甚至跟日本方面也募到了錢。1938年,饒家駒開始到海外募款,先去日本,再去加拿大,又到美國。“去美國募款,他帶了一本提前設計好的英文版募款小冊子。”參與制作《慈善救助分布圖》的王海鷗說。endprint
王海鷗做研究時曾輾轉找到一本饒家駒的法文小冊子,她不懂法文,依樣畫葫蘆抄寫下來請學法語的師兄翻譯。這本小冊子內容與英文小冊子相近,都是募款手冊,但較英文版多出一些內容。
法文小冊子里記錄了饒家駒赴美見美國總統羅斯福,并成功募集到70萬美元和數量可觀的小麥等事情。
“當時美國紅十字會把小麥運到難民區,中國的難民因為大多是南方人,并不喜歡小麥做的食物。饒家駒的這個小冊子里邊,還把這個細節寫進去了。”據相關資料記載,南市難民區內共開辦了20多個糧食分發中心和食堂,向難民分發票券,難民再憑票券購買。
同時,難民區內還設立臨時醫院,婦產醫院,此后又開設災童醫院等醫療衛生場所。
王海鷗找到的那本法文小冊子中有這樣一段話:“令人敬佩的上海,這座以其無法估量的慈善捐助的城市,它是如此之慷慨,這似乎是不能再期望更多的了。”可見,當時上海民間的慈善力量是南市難民區存在的重要支柱。
依靠饒家駒的智慧,以及中外慈善力量的合力支撐,上海難民區存在長達3年之久。一面是歌舞升平戰時畸形繁榮的租界,另一面是戰火連天生靈涂炭的戰場,南市難民區尷尬地存活在二者中間,護佑了超過30萬中國難民。饒家駒說,“中國就是我的故鄉,我熱愛中國”。回到歐洲后,他將自己的中文名改為饒家華,以此為念。
遺憾的是,時至今日,知道饒家駒名字的中國人也并不算多。
“中國后來都遺忘他了。我們一直在努力推動,去年我們開了一個會,去回顧總結,希望更多人能了解饒家駒對中國、對世界做出的貢獻。”蘇智良告訴《中國慈善家》。
多年以來,蘇智良持續深入研究饒家駒對難民保護做出的貢獻。今年,他出版了《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一書,已被列入中國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百種圖書之一。
不只是收容
抗戰時期,各地難民所為使難民轉化為有生力量,除了為難民提供生活所需外,還對他們進行教育、訓練,鼓勵難民生產自救,為年輕力壯和有一定知識的人介紹職業。一些難民收容所逐漸轉型為復合型救濟型機構。例如,他們開辦以工代賑的小型難民工廠、農場、習藝所,以及兼顧救濟與教育的難童收容所。還會按職業、年齡等類別開辦有針對性的特殊收容機構。
在難民習藝所,年富力強具有生活技能的男女會被組織起來,從事縫紉、刺繡、木工、扎花等生產,難民不僅可以解決吃穿住等問題,還能得到一定的工資。上海國際救濟會收容所內設立了多處難民習藝所,參加的人均會獲得工作報酬。
廣西桂林難民收容所屬政府救濟機關,設立于1938年末,在桂林城外設立7個難民棚,收容戰區難民近萬人。所內難民不僅有生活費,而且有建房費。此外,還組織難民成立互助社,難民入股滿100元即可開辦合作社,供應所內難民的柴米油鹽等生活消費品,以商業模式促動難民高效自救。
1938年初,江蘇同鄉會在武漢創立,其開辦宗旨是集中教育人才救亡祖國。該收容所內難民依職業類別分為工、商、學、農等各種小組,開展多樣文化培訓。在當時消極悲觀的環境中,這無疑是一種提振精神,以謀自強的出色模式。
1938年3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施行戰區兒童教養院暫行辦法15條,要求各省市教育部門收容戰區兒童。因此,戰時兒童保育會與戰時兒童救濟協會分別設立兒童保育院和兒童教養院。
兒童教養院以收容教育難童為宗旨,重慶、西康等地均有設立,收容難童萬人。是年10月,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將孤兒院擴改為教養院,所需經費由各省市政府自籌,不足者由中央撥發。此后近5年時間里,全國兒童教養院已超過百所,官方主辦不到三分之一,其余教養院均為民間主辦,中央撥款支持超過30萬元。在教養院,難童入學費用全免,課業注重生產教育,培養難童獨立生活能力。
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于1938年5月在漢口設立兒童保育院,此后,川、粵、湘、浙、閩乃至香港地區等地也紛紛設立兒童保育院。各院均以“教養并重”為理念,凡入學兒童,視其經濟能力,按全、半、四分之一等不同等級交納費用。
1942年,振濟委員會在重慶設立的戰區內遷婦女輔導院正式收容婦女。其開辦經費來自于振濟委員會撥款。入院者每人每月享有超過百元的生活費用。院方對學員進行管理、培訓,促使難民婦女就業。
難民收容所是戰爭促生的畸形產物,并非難民的理想去處。設備設施缺乏,食宿條件低劣,缺醫少藥,管理混亂,遭受不合理待遇甚至經受肉體與心靈的折磨的情況都難免發生,但它為飄零于硝煙中的難民提供了一個暫時的存身之所,讓生命得以保存,也讓惡劣環境中人性的善良得以彰顯。
(本文參考《抗戰時期難民收容所的設立及特點》,作者王春英;《抗戰時期難民群體初探》《戰時兒童保育會的難童救濟工作初探》,作者孫艷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