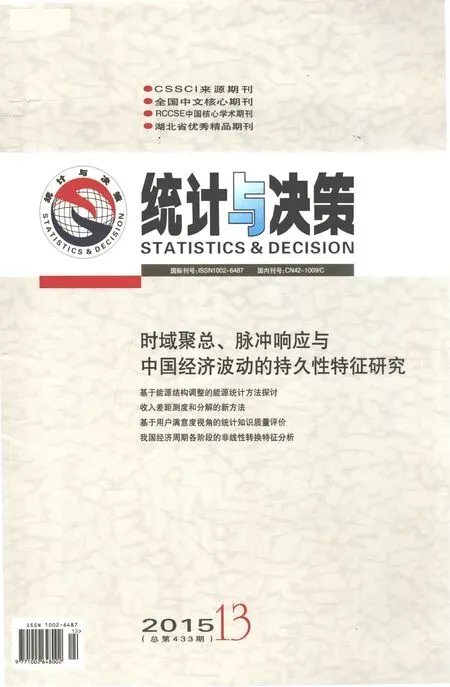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中美貿易差額的動態影響
張陸洋,葛加國,錢東平
(1.復旦大學a.中國風險投資研究中心;b.經濟學院,上海 200433;2.江蘇省人民政府 金融辦公室,南京 210024)
0 引言
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維持了較長時期經常賬戶順差,國外要求人民幣升值以平衡我國經常賬戶的呼聲越來越高。在國內,人民幣升值壓力使國際資本市場形成了人民幣將持續升值的預期,大量套利資本流入我國,再加上本來就看好中國市場潛力而大舉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資,我國的資本與金融賬戶也出現順差,從而形成國際收支的雙順差格局,更加劇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并使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運行受到很大挑戰。
因此扭轉貿易收支持續大量順差的局面,實現國際收支基本平衡,成為緩解我國經濟政策運行承受的外部壓力的基本思路之一。理論上,根據傳統的貿易收支彈性理論,當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時,人民幣對外升值有助于扭轉我國貿易收支持續順差的局面,而實際上,貿易收支彈性理論在我國的適用性一直存在爭議,人民幣匯率變動是否及如何對我國貿易差額產生影響一直是國內外學者爭論的焦點。換言之,是否應該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改善我國貿易收支失衡現象,仍然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1]。
本文從一個更為全面的角度來分析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中美貿易收支的影響。由于貿易收支與人民幣匯率可能受到共同因素的影響,這可能導致將人民幣匯率與中美貿易收支受共同因素影響而造成的相關性誤認為因果關系。本文的創新之處是將人民幣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整體影響分解成兩部分:一是純粹的匯率變動的影響,反映了匯率變動本身所引起的直接的貿易差額變化,主要體現為匯率變動的支出轉換效應;二是其他的因素通過相關的宏觀經濟變量對貿易差額的影響。這樣就可以在最直接、最本質的層面上分析人民幣匯率變化對中美貿易差額的影響,回答貿易收支彈性理論在我國的適用性問題,為政府的政策調整提供理論依據。
1 數據說明
本文選取1999~2013年的季度數據,其中BAL代表中美貿易差額。RGDP表示國內的實際收入,采用以1990年1季度為基期的不變價格調整。URGDP表示美國的實際收入。RER表示中美雙邊實際匯率,以雙邊名義匯率與中美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之比的乘積來計算,公式為:

其中,ER為人民幣兌美元的名義匯率。PA和P分別表示美國和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圖1 實證變量趨勢圖
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要求各個變量是平穩的隨機過程,因此,要對每個變量的平穩性進行檢驗。由于我國的實際GDP、中美貿易差額、實際匯率表現出很強的季節性變化(如圖1),因此應對其進行季節性調整。而美國經濟分析局對美國實際GDP進行了季節性調整,因此本文未對此變量進行季節性調整。
為進一步消除數據異方差,對數據取自然對數,以使序列趨勢線性化,且能分析各個宏觀變量之間的彈性大小。分別用LBAL、LRGDP、LURGDP、LRER表示對數的中美貿易收支、中國實際收入、美國實際收入、中美實際匯率。對這四個變量的水平值和一階差分的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表1中結果顯示,我國的實際GDP、人民幣實際匯率、中美貿易差額、美國實際GDP的對數值的一階差分是平穩的時間序列,記為I(0),因此可以進一步進行向量自回歸分析,同時也可對其水平值作協整分析。

表1 單位根檢驗
2 模型說明
用向量Xt表示其一階差分向量,即:

按照word分解定理,Xt可以寫成如下表達式:

其中ut即為三種結構性沖擊構成的結構性沖擊向量,且有var(u)=I,u代表式(2)中ut的總體。而為了找出式(2)中每個時間t的ut值,可先對 Xt進行VAR分析,然后轉換為下述的向量移動平均(Vector Moving Average,VMA)過程:

其中var(v)=Ω,v代表式(3)中vt的總體。比較式(2)和(3),如果對于任何的j(j=0,1,2,…),都有一個矩陣D(0)使得vt+j=D(0)ut+j成立,則有vt+j=D(0)ut+jDt+j=Ct+jD(0)成立。因此,首先需要找到D(0),隨后就可由vt分解出每個時期的結構性沖擊ut,這個過程即為沖擊分解(Shock decomposition),且這樣分解出來的三種結構性沖擊相互間是正交化的。矩陣D(0)有16個元素,所以需要16個約束條件才能將其求解出來。首先由上述條件易知:

而對稱矩陣Ω可以通過上述的VAR估計出來,因此,由式(4)可以得到關于D(0)的16個元素的10個約束方程,所以還需要另外的6個約束條件。
本文在做這6個約束時,采用長期約束的方法來識別模型。長期約束的概念最早由Banchard等[1]在1989年提出。最常見的長期約束的形式是對的第i行第j列元素施加約束,典型的0約束形式,表示第i個變量對第j個變量的累積乘數影響為0。
本文在對沖擊的影響進行長期約束時,首先必須對ut中的四個結構性沖擊賦予明確的經濟含義。與文獻[2]約束方法一致,本文認為GDP同時受到供給沖擊()和需求沖擊()的影響。由于Xt中有四個變量,因此還可以分解出其他兩種結構性沖擊。本文將第三種結構性沖擊定義為國內外相對價格沖擊,理由有二:一是Xt中包含了人民幣實際匯率(EER),目的是研究其變化造成的影響,而實際匯率(EER)反應的就是國內外相對價格;二是無論GDP還是貿易差額,均受到國內外相對價格變化的影響。由于國內外相對價格沖擊首先直接影響人民幣實際匯率(EER),進而才影響GDP和貿易差額,因此可以將國內外相對價格沖擊成為匯率沖擊,記作()。同理,美國的GDP也受攻擊沖擊和需求沖擊影響,由于匯率沖擊和進出口差額沖擊可以看成是需求,因此可從中分出國外的供給沖擊。此時就能真正考慮到由人民幣匯率變化引起的沖擊的影響。在規定好四種結構性沖擊之后,可將(4)式中的ut寫作采用Blanchard&Quah提出的對結構沖擊影響進行長期約束的方法[2],需求沖擊對GDP長期影響為0,則按照(4)可得到如下四個約束方程:

上述約束方程的下標“i”“j”分別表示該矩陣的第i行、第j列元素。根據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原理,本文認為影響人民幣實際匯率(EER)長期變化的因素主要來自國內各部門技術改進與生產率增長,而需求沖擊對于人民幣REER沒有長期影響,因此可得:

在做最后一個約束時,考慮建立兩國對數實際GDP向量自回歸(VAR)模型,通過方差分解分析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如表2所示,美國實際GDP對中國GDP的方差貢獻率達到44.70%,而中國GDP對美國GDP的貢獻率卻只有0.35%。因此,本文認為有如下約束表達式:

通過式(5)~(10),將ut從εt中分解出來,此時能分析ut中各種結構性沖擊對Xt中各變量的動態影響,進而就能分析這些結構性沖擊對我國GDP、人民幣實際匯率(EER)及我國貿易差額的動態影響。

表2 中美兩國實際GDP的方差分解
3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中美貿易差額影響的實證分析
借助上文對沖擊的分解,就可以分析各種沖擊對我國實際GDP、貿易差額的動態影響了。
3.1 脈沖響應分析

圖2 我國實際GDP對四種結構性沖擊的累積脈沖響應
首先給出我國實際GDP對四種結構性沖擊的累積脈沖響應圖。圖2中,對四種結構性沖擊,我國實際GDP的脈沖累積響應是不同的。其中,對本國供給沖擊和對外國供給沖擊的累積脈沖響應是持久的,且對前者的脈沖累積響應要遠大于后者,在五個季度和九個季度后分別達到了1.08%和0.629%的累積實際GDP增長率,而對匯率沖擊和需求沖擊的累積脈沖響應則不能持續,在七個季度和九個季度后累積實際GDP增長率幾乎變為零。累積脈沖響應具體數值見表3。
圖2及表3的結果與Blanchard&Quah(1989)[22]一文中對美國GDP的動態特征相反,但由于Blanchard&Quah(1989)[22]文中匯率變量數值上升表示升值,而本文采用的匯率標量數值上升表示貶值,因此,本文的結論與該文高度一致。

表3 我國實際GDP對四種結構性沖擊的累積脈沖響應
3.2 中美貿易差額對人民幣實際匯率脈沖響應分析
接著分析人民幣實際匯率(RER)的變化對中美貿易差額的影響,以判定貿易收支彈性理論對我國對美貿易是否成立。圖3給出了中美貿易差額對匯率結構性沖擊的脈沖響應。根據上文的結構性沖擊分解,此處的匯率結構性沖擊是純粹由人民幣實際匯率(RER)變動帶來的沖擊,即,因此考察的是中美貿易差額對這種純粹的匯率結構性沖擊的動態反應。圖3的脈沖響應的結果如表4。
圖3引入的匯率結構性沖擊為一個標準差,即人民幣升值(此處采用人民幣直接匯率),以檢查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差額產生的影響。由圖3可知,人民幣實際匯率一個標準差的貶值在當期使中美貿易差額上升了0.67個百分點,但在隨后兩個季度,中美貿易差額出現了下降2.0個百分點和1.53個百分點的響應,當滯后四個季度后,中美貿易差額又上升了0.476個百分點,在滯后4年后,匯率結構性沖擊的脈沖響應幾乎為零。這說明,我國的經濟體系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市場具有吸納各種沖擊的能力。這也從某個側面說明模型的合理性。

圖3 中美貿易差額對匯率結構性沖擊的脈沖響應

表4 中美貿易差額對匯率結構性沖擊的脈沖響應
為進一步分析匯率結構性沖擊對中美貿易差額的影響,本文也給出了四種結構性脈沖響應對中美貿易差額的累積脈沖響應(如圖4),詳細數據見表5。
圖4中的四幅圖,分別是中美貿易差額對本國供給結構性沖擊(dlrgdp)、匯率結構性沖擊(dlbal)、需求結構性沖擊(dlbal)和外國供給結構性沖擊(dlurgdp)的脈沖累積響應圖。
在本國供給結構性沖擊對中美貿易差額的累積脈沖響應圖中,當滯后一個季度時,中美貿易差額增加了5個百分點,當經過一段時間的波動,在滯后四個季度后開始逐漸下降,到滯后三年后,中美貿易差額累積下降到3.3個百分點。

圖4 四種結構性脈沖響應對中美貿易差額的累積脈沖響應圖
在匯率結構性沖擊對中美貿易差額的累積脈沖響應圖中,當滯后一個季度時,中美貿易差額上升了0.06個百分點,但在滯后兩個季度時,中美貿易差額累積減少了1.32個百分點,在滯后三個季度后達到了最低的增長率,為-2.86個百分點,隨后增長率逐漸增加,在滯后3年后,中美貿易差額增長率增加到1.59%,并穩定在這一點附近。在匯率的脈沖累積響應圖中,當匯率貶值時,中美貿易差額在滯后一期時增加了,但隨后出現了減少,再又有所增加,這一反應非常類似于J曲線,因此可以說人民幣實際匯率RER對中美貿易差額影響具有“修正的”J曲線效應,也即中美貿易收支彈性理論在我國基本上是成立的。

表5 中美貿易差額對四種結構性沖擊的累積脈沖響應
通過對需求結構性沖擊對中美貿易差額的脈沖累積響應圖的分析,可知在滯后一個季度時,中美貿易差額增長了12.8個百分點,隨后出現了一定的小幅波動,在滯后五年后,中美貿易差額的累積增長率穩定在7.15個百分點左右。
在外國供給結構性沖擊對中美貿易差額的脈沖累積響應圖中,中美貿易差額累積增長率是持續增加的,在滯后五年后,中美貿易差額累積增長率穩定在10.12個百分點左右。
通過上述對圖4的分析,可以得出:(1)這些變量的脈沖累積響應分析符合傳統的經濟理論,本國GDP增加會對本國的貿易差額產生不利影響,而外國GDP增加則對本國的貿易差額產生正影響。本文的需求沖擊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稱為市場沖擊,即排除了匯率因素的國外市場需求變化所引起的沖擊。因此,此處的總需求必然對兩國間的貿易差額產生正效應。(2)四種結構性沖擊的脈沖響應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滯后后,均達到了穩定值,這說明四種結構性沖擊的脈沖響應,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滯后以后,影響消失。(3)通過對匯率結構性沖擊的脈沖累積響應圖的分析,得到了修正的“J曲線”,說明彈性理論對于中美貿易差額是成立的。(4)匯率結構性沖擊對中美貿易差額的脈沖累積響應最小,在經過三年的滯后后,中美貿易差額的增長率僅為1.59%,遠低于本國供給結構性沖擊、需求結構性沖擊和外國供給結構性沖擊的影響;而外國供給結構性沖擊對中美貿易差額的影響是最大的,穩定時的增長率達到了10.2個百分點,這也從側面證明了我國是一個外向型經濟國家,對外依賴性很強。
3.3 中美貿易差額與結構性沖擊的比較分析
中美貿易差額與結構性沖擊的比較分析圖中的數據來源于本文中根據SVAR模型計算得出的結構性沖擊數據,為方便對比,本文將模型中的對數的貿易差額數值放大了10倍。通過分析中美貿易差額及其結構性沖擊的對比分析圖,發現中美貿易差額的需求沖擊成分最能擬合樣本時段內我國貿易的差額的具體波動,而中美兩國供給沖擊和匯率沖擊也能對中美貿易差額做出一般的擬合,其中美國供給沖擊的擬合程度優于中國供給沖擊的擬合程度。這表明我國的貿易收支最容易受到需求沖擊、尤其是外部沖擊的影響,從而與我國經濟增長過分依賴對美出口的結論是一致的。由于本文側重分析匯率對中美貿易差額的作用,因此著重分析匯率沖擊對中美貿易差額的擬合情況。通過對中美貿易差額的分析得知,從2007年4季度到2008年2季度,2010年2季度到2011年2季度以及2012年1季度到2013年1季度,中美貿易差額的變動幅度較大,圖5中,匯率同時也做出了相應的變動,至少在趨勢上做出了相應反應。這說明,如果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將有助于中美貿易差額的改善。再結合上文圖3與圖4的相關分析,本文認為中美貿易差額對人民幣實際匯率比較敏感。因此,當前在制定匯率政策時,我國應進一步完善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增加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彈性,以充分發揮人民幣匯率對中美貿易差額的調整作用。

圖5 中美貿易差額及其結構性沖擊的對比分析圖
4 結論
針對已有的關于人民幣匯率對我國貿易差額影響的研究文獻的不足,本文通過構造一個包括我國實際GDP增長率、人民幣實際匯率RER變化、中美貿易差額變動和美國實際GDP增長率四個變量的SVAR系統,分析了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化對中美貿易差額的動態的影響。首先,通過對上述SVAR模型脈沖響應的分析,本文發現一個標準差的實際匯率貶值沖擊使得中美當前的貿易差額增加了0.675%,但是在隨后的第二季度中美貿易差額增加了-0.2%,并在之后四個季度后,中美貿易差額又出現了正增長,增長率為0.476%,隨后逐漸向零增長率的方向收斂,因此,可以從圖3和圖4中看到明顯的修正的“J曲線”。其次,在中美貿易差額的變動中,匯率的作用不可或缺。這進一步說明貿易收支彈性理論在我國是成立的,人民幣匯率是影響中美雙邊貿易的重要因素。
[1]劉堯成,周繼忠,徐曉萍.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差額的動態影響[J].經濟研究,2010,(5).
[2]Blanchard O,Quah D.The Dynamic Effects of Aggregate Demand and Supply Disturbanc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