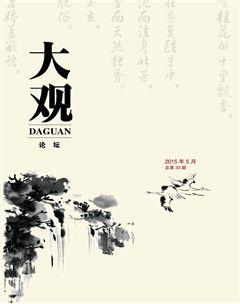從自覺到自信的魏晉之歌
王燕燕
摘要:“文學的自覺”不會突變,而是慢慢積累生成的。“自覺”是一種無意識,作為非職業作家的古代文人么來說,并沒有形成抽象文藝理論的意識和職責,當有人將感性的文字上升為理性的結晶時,值得注意的是,這時發現的不僅僅是文字背后的意義,更是文字背后的人。
關鍵詞:自覺;自信
文字的發明,讓人類的活動不再如雁過無聲般毫無蹤跡,透過那厚重的文章,先輩的一切如畫卷般展開,當文字不只是被動地記錄歷史,而且也能為人主動地滲透思想,表達情感時,那么這種自覺見證的必然是文字所創造的文學輝煌。
“文學的自覺”到底始于何時?1927年,魯迅先生提出,曹丕的一個朝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日本學者鈴木虎雄先生也與此觀點不謀而合。在隨后的六十余年中,這個足以蓋棺定論的說法一代又一代地被延續。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關于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文學的自覺時代”始于何時的問題,再度引起很多學者的關注,甚至一度出現了論爭比較激烈的情形。概略言之,大體上有三種觀點。一是認為中國文學的自覺,早在漢代就開始了;二是認為文學自覺發生在魏晉之后的六朝時期;三是在部分修改魯迅和鈴木虎雄說法的基礎之上,持“魏晉說”立場。同一個“文學自覺”的命題,為什么會出現如此眾說紛紜的解說呢?個中原因可能很多,但最主要的,可能還是在“文學自覺”的概念界定上標準不一。
那么究竟什么叫做“自覺的文學”呢?拋棄繁重的教科式講解,自覺的文學應該是獨立于政教之外的藝術地表現人和人生的文學。只要把這個“人”理解為哲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具體的人,就可以比較真實而具體地反映文學本質的。當然,文學所藝術地認識和表現的人,除了人的外部特征外,更為重要的是指人的命運、心靈以及個性。因此,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或者自覺的文學應該是藝術地表現人和人生的文學。
讓我們首先以這個定義來衡量一下漢代的大賦,那浩浩蕩蕩,虛偽矯情的贊歌和奏鳴曲中,又怎么會存在人的氣息!《七發》中的太子和吳客,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中的子虛、烏有、無是公等大賦中的代表人物,都是虛擬的。大賦作家設計他們,不過是讓他們做一個傳聲筒,講出一番“好山好水好風光”的話語來,并不是真正的文學意義上的人。他們就像音樂符號,經過組合后所形成的是旋律優美的樂章,不過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因此,大賦不可稱之為“自覺的文學”,即便是命名為文學,也是要打引號的。說其始于漢代的說法不攻自破。
文學的發展過程是動態而非靜態的,只有前期量的積累才能實現后期質的飛躍,所以不應該也不可能將“自覺”僵硬化和固定化,就像河流一樣,無數的水滴聚合成水流,數以億計的水流匯成小溪,所以要明確的概念是,“文學的自覺”不會突變,而是慢慢積累生成的。“自覺”是一種無意識,作為非職業作家的古代文人么來說,并沒有形成抽象文藝理論的意識和職責,當有人將感性的文字上升為理性的結晶時,值得注意的是,這時發現的不僅僅是文字背后的意義,更是文字背后的人。
西漢文人是倡優般的存在,沒有知識分子的傲骨和自守,缺乏一種精神與人格上的獨立性,這與當時的社會現狀是有必然關系的。而這種問題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沒有創作主體的自覺,那么文學本身的自覺就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了。沿著歷史的河流,我們不難發現,東漢中后期,大一統思想和政治的雙重式微,使文人在長期的禁錮和壓抑后,目光逐漸內斂,并因此而真正發現了自我,實現了文學自覺的重要前提——人的自覺。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自覺地表現人和人生的文學有哪些內涵呢?主要是人的覺醒,即人發現了自己,并有意識的替自己代言,文學的社會責任感減弱了。文學創作不再只是迎合君主和權力,而更多的是為了抒一己之情懷,獲得心靈上的快感和自由。我們認為這種情形在東漢中后期的文學創作中已經出現。
這種變化的標志之一是張衡《歸田賦》的出現。張衡十年磨一劍,寫成《二京賦》。該賦的主旨是諷諫帝王公侯節儉,但可悲的是,這篇讓張衡花費巨大精力所作的大賦,卻絲毫未得到君主的重視。面對著國力衰退的現狀,他知識分子的責任與使命感逐漸破滅了,取而代之的是道家的無為思想。《歸田賦》中描寫了隱居生活的恬淡情趣,景物清新和美,生活自由逍遙,詩人借此“娛情”、“縱心”。很明顯,一個抒情主人公的形成和樹立,以張衡為代表的一批詩人開始了艱難的自我發現之旅。此后,抒情小賦不斷出現并逐漸取代大賦,一片繁榮之景。從此,辭賦成了文人抒情寫意的工具,實現了文學的自覺。應該說,張衡的《歸田賦》是文學自覺的一枝報春花。
鑒于此,我們可以明白“文學的自覺”并非突然產生,沒有量的積累,不然不會發生質的飛躍。不可否認的是,文學與政治具有悖論性,魏晉時代,社會的動蕩卻給于了文學瘋狂生長的機會和空間。這個時期吸收了前期的文學精華,揭開了唐代文學的浩蕩大幕。漢末動亂的時代迫使作家們面對嚴酷的社會現實,因而他們能夠自覺地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發現文學,發現自己只能稱之為一種對舊有體系的破壞,真正的建設并形成規模的自信則需要歷經幾個世紀,終于在漫長的動蕩與平靜過后,陶淵明的出現,創造了了中國文學走向大唐盛世的自信。
陶淵明的偉大之處就在于當殘酷的現實與蒼白的夢想發生碰撞時,他能夠做到寧固窮而不易其志,處貧賤而能曠達釋懷,于田園中找到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他成為后人難以企及的范型。朱熹曾說:“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淡,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晉宋人物。”陶淵明的這一點確實超越了眾人,后代文人也很少像他那樣能超越仕與隱的矛盾。正由于后代文人很難真正擺脫名利的束縛,所以陶淵明才成了后人心中高風亮節的象征。
評價一個人,評價一個時代的標準都應該是它和他是否給了未來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從東漢中后期的突變,再到陶淵明的遺世獨立,我們看到的是文人作為個體的意識覺醒,從情感的放縱表達,再到皈依平靜后的娓娓道來,跨越的不是時間,而是中國文人意識高度的變化。自覺與自信只有一字之差,但卻是幾代文人用發展的觀點疊加并置換的,或許盛唐之音會讓中國文學在世界舞臺上名留史冊,但沒有東漢末年,沒有魏晉,沒有陶淵明,就必然沒有其大放異彩的空間和舞臺。
【參考文獻】
[1]李澤厚.美的歷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2]袁行霈.中國文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3]游國恩.中國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