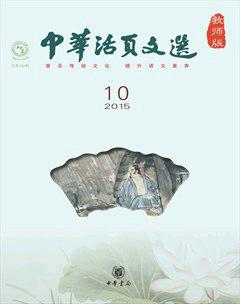漫話茱萸
郭鵬
一
茱萸,見之典籍甚早。史料及醫學著述中,有藙、樧、棗皮、藥棗、蜀棗、蜀酸棗、魁實、石棗、鼠矢、雞足、湯主、山萸肉、萸肉、肉棗等名稱,多指果實、果核而言。木本茱萸有山茱萸、吳茱萸、食茱萸之別,還有草茱萸,為草本植物。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就有記載:“茱萸,屬,從草,朱聲。”“樧,似茱萸,出淮南。”清代學者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對“茱萸”作注說:“《內則》:‘三牲用。注,,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樧。《本草經》入木類。鄭君曰:‘茱萸即樧也。而《廣韻》椒樧在釋木,許君則茱萸與樧為二物,《木》部曰:‘揚州有茱萸樹。正以見茱萸之本為草類也。”段玉裁所引之《爾雅》,傳為周代周公所撰,也有傳為孔子門人解釋《六藝》之作,秦漢間經師輯錄舊文,遞相增益而成,不出一時一人之手。《內則》即為《周禮》中篇名。《本草經》,亦名《神農本草經》,多記載各地草本、木本藥物,傳為上古時神農作著,但據其中多東漢地名看,疑為東漢人所作。《廣雅》為三國時學者張輯作著。唐初《藝文類聚》中轉引《洞林》載:“(晉)郭璞避難至新息(今河南省息縣),有以茱萸令璞射(即猜)之,璞曰:‘子如赤鈴,含元珠,案文言之,是茱萸。”晉代周處《風土記》亦載:“茱萸,樧也。九月九日熟,色赤,可采時也。”從以上記載可見,茱萸之見于典籍,始于周代,最遲也當于漢代,且當時的人們已認識到了它的藥用價值,并把它作為祭祀之物,被列為地方向朝廷的貢品。
我國人工種植茱萸也很早。西晉時大文學家左思在《蜀都賦》中記載:“其園則有蒟蒻、茱萸、瓜疇于區,甘蔗、辛姜。”晉代馮翊太守、梁州令孫楚《茱萸賦》言:“有茱萸之嘉木,植茅茨之前庭,歷漢女而始育,關百載而長生。”由上可見,我國在漢代及魏晉南北朝時,就已經將茱萸栽植于園圃、庭院。
二
史籍中,關于茱萸的作用,大致有:
一是用于祭祀。《周禮·內則》載:“三牲用。”清段玉裁釋:“煎茱萸。”據《周禮·祭統》言:“三牲之俎,八簋之食,美味備矣。”從此記載可知,周代祭祀之時,把三牲(牛、羊、豬)放在祭板上,把煎過的茱萸等八種美果放在八個祭盤中。可見早自周代,人們就視茱萸為非凡之物了。
二是作佩戴用的飾物。屈原《離騷》中言:“椒專佞以謾諂兮,樧又充其佩幃。”古代王妃所居之宮殿,以椒和泥涂壁,取溫香、多子之義,故歷代以椒房代指王后。這里之“椒”,指專佞而謾諂的楚王之妃,她身上佩戴著樧(茱萸)作的飾物。歷代人們皆在九月九日重陽節時,頭插茱萸,登高游興。
三是藥用。西晉初,馮翊(今陜西關中西部)太守孫楚曾作《茱萸賦》一文,其中言:“有茱萸之嘉木,植茅茨之前庭,歷漢女而始育,關百載而長生。森蔓延以盛興,布綠葉于紫莖。鶉火西阻,白藏授節,零露既凝,鷹隼飄厲。攀紫房于纖枝,綴朱實之酷烈。應神農之本草,療生民之疹疾。”這里已明確地記述茱萸能“療生民之疹疾。”古代許多醫學名著,如晉《神農本草經》、唐孫思邈《千金翼方》,以及《吳晉本草》《健康記》《圖經本草》等,均記有茱萸的藥用價值。山茱萸之果實山萸肉,味酸澀,性微溫。臨床實踐有補肝腎、澀精氣、固虛脫、健胃壯陽等功能,中醫常用以治療腰膝酸痛、眩暈、耳鳴、遺精、尿頻、肝虛寒熱、虛汗不止、心搖脈散、神經衰弱、月經不調等癥。茱萸還是中成藥知柏地黃丸、益明地黃丸、愛味地黃丸、十全大補丸、六味地黃丸的主藥。根據現代醫學分析化驗,山萸肉中含有生理活性較強的山茱萸甙,即馬鞭草甙、皂甙、鞣甙,以及極豐富的維生素C等營養成分。能抑制痢疾桿菌、傷寒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及某些皮膚真菌,有利尿、降壓、防癌作用。茱萸的多種藥物用途,大概正是自漢以來人們重視、培育栽植茱萸的直接原因。
四是辟邪。南北朝時南梁吳均所撰《續齊諧記》中記載了一則故事:“東漢時,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其言,舉家上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之。今世人九月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始于此。”辟邪,自是迷信之說,但從茱萸的藥用價值來看,值得深思。古人患病,不知病因,常謂之遇邪氣所致。佩戴茱萸囊,飲菊花酒,正是茱萸、菊花的藥味藥性對某些疾病發生了作用,而使疾病得以痊愈,或起到了預防疾病的作用。古人不知此故,故謂該物能辟邪。
五是釀酒。古代詩文中,詠述茱萸酒者屢屢見之。而以唐初所撰《藝文類聚》中轉引《異苑》的一則故事更有趣:“庾紹為湘東郡,亡,宗協與紹中表。且服茱萸酒,忽見紹來,但求酒。執酒杯,還置,云有茱萸氣。協云:‘惡之乎?紹云:‘上官皆畏之,況我乎?”這里的“上官”,即鬼中的大官。《異苑》乃南朝劉宋時劉敬叔所撰。而宋代巨著《太平廣記》轉引《冥祥記》,記載此事較詳,言庾紹為庾紹之,晉新埜(野)人,字道覆,為湘東太守。宗協為南陽人。庾紹于元興末(404)病亡。義熙年間(405—418)忽現形訪宗協,宗協與之飲茱萸酒。歷代文人詠頌茱萸酒的詩詞較多,如唐代著名隱士寒山詩曰:“縱爾居犀角,饒角帶虎睛。桃枝將辟穢,蒜殼取為纓。暖腹茱萸酒,空心枸杞羹。終歸不免死,浪自覓長生。”這里,把茱萸灑與犀角、虎睛、桃枝、蒜殼、枸杞等作為驅鬼辟邪、長生不死之物。茱萸酒很長一段時期(明清以后)未見記載,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漢中地區山茱萸主產縣佛坪縣利用當地資源,生產山茱萸系列果酒、飲料,其味醇美,藥效顯著。
三
由于歷代把茱萸作為祭祀、佩飾、藥用、辟邪之物,因之,古代人們對茱萸情有獨鐘,以至形成饒有興味的茱萸風俗。這種風俗,最早見于晉代葛洪(有的史料記載為東漢劉歆)所撰《西京雜記》,言漢高祖劉邦時,其寵妃戚夫人之宮女賈佩蘭回憶在宮中之日,戚夫人于每年九月九日,頭插茱萸,飲菊花酒,食蓬餌,出游歡宴。晉周處《風土記》亦載: “九月九日,……俗于此日,折茱萸以插頭,言避惡氣,以御初寒。”“以重陽相會,登高飲菊花酒,謂之登高會,又云茱萸會。”南梁時宗懔撰《荊楚歲時記》載:“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飲宴。按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近代皆設宴于臺榭。”宋朝《太平御覽》等典籍亦載有重陽日登高插茱萸風俗。《遼史·禮志》載:“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少者為負,罰重九宴。射畢,擇高地卓帳,賜蕃,漢臣僚飲菊花酒。兔肝為臡,鹿舌為,又研茱萸酒,灑門戶以礻會禳。”于此可見,茱萸酒避邪之風俗,不獨漢族有,少數民族亦然。
據清康熙《陜西通志·風俗》轉載《臨潼》云:“重陽,上驪山,飲茱萸酒,所親以棗糕相饋。”該志還轉載《西鄉縣志》重陽采茱萸之俗。清嘉慶《續修漢南郡志》(即《漢中府志》)載:該地區因產茱萸,故屬內城固、洋縣、西鄉等縣有重陽茱萸風俗:“城固縣……九月九日,食米糍,登高,飲茱菊酒,兒童競放風鳶。”“洋縣……重陽采菊拾萸,登高泛酒。”“西鄉縣……(九月)九日,親友以菊花、米糕饋送,登高,飲茱萸之酒,或上云臺之山,或在午子山之峰,酌酒賦詩,瀏覽丹楓、黃菊;婦人則摘采茱萸,曰可治心疼也。”
重陽之日,秋高氣爽,正是茱萸成熟之時,黃菊遍地,丹楓滿山,紅果熠熠,萸肉清香,既然茱萸能祛病驅邪,故古之人珍愛有加,遂于此佳節之時,登高暢游,攜茱萸女,插茱萸枝,佩茱萸囊,飲茱萸酒,吟茱萸詩,極盡歡娛之樂。久而久之,相沿成習。故古人又把九月九日重陽節稱為登高節、茱萸節、茱萸會,可見茱萸自古已廣泛被人們所寶愛。茱萸風俗在全國大部地區均有,歷時悠久,只是到民國以后,茱萸風俗漸衰,唯登高之俗猶殘存。
四
歷代文人筆下,記述茱萸的詩賦甚多。晉孫楚有專文《茱萸賦》。詩文多以茱萸寄言親友歡娛之情。宋代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言:“子美《九日藍田崔氏莊》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王摩詰《九日憶山東兄弟》云:‘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九日與楊凝、崔淑期登江上山,有故不往》云:‘哪得更將頭上發,學他年少插茱萸。此三人各有所感而作,用事則一,命意不同。后人用此為九日詩,自當隨事分別用之,方得為善用故事也。”茱萸因其本身的價值及歷代賦予其傳奇色彩,故文人們多喜用它作詩料,并從不同角度表達作者的不同心境。除本文中已摘錄的詩賦文句外,歷代還有不少詠茱萸的詩句:
魏曹植《蒲生行浮萍篇》:“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南梁吳均《行路難》:“茱萸錦衣玉作匣,安念昔日枯樹枝。”《贈柳真陽》:“朝衣茱萸錦,夜覆葡萄卮。”(茱萸錦,錦緞名。晉陸翙《鄴中記》載:“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葡桃錦、玫瑰錦。”)
唐代詠茱萸句甚多。宋代洪邁在《容齋隨筆》中有《詩中用茱萸字》一文,指出劉禹錫言唐代三位詩人詠茱萸句,未盡,洪又列出十人。而據筆者所見,猶未盡數。略舉數詩如次。
白居易《九日宴集醉題郡樓兼呈周、殷二判官》:“觥醆艷翻菡萏葉,舞鬢擺落茱萸房。”《九月九日登巴臺》:“閑聽竹葉曲,淺酌茱萸杯。”《九日寄微之》:“蟋蟀聲高初過雨,茱萸色淺未經霜。”
戴叔倫《登高乘月尋僧》:“插鬢茱萸來未盡,共隨明月下沙灘。”
盧綸《九日奉陪侍郎》:“睥睨三層連步障,茱萸一朵映華簪。”
張鄂《九日晏》:“歸來得問茱萸女,今日登高醉幾人?”(茱萸女:指茱萸宴會上,頭插茱萸的侍女。)《九日》:“城遠登高并九日,茱萸凡作幾年春?”
耿諱《九日》:“步蹇強令避藻井,發稀哪敢插茱萸?”
王昌齡《九日登高》:“茱萸插鬢花宜春,翡翠橫釵舞作愁。”
權德輿《酬九日》:“他時頭似雪,還對插茱萸。”《九日北樓宴集》:“風吹蟋蟀寒偏急,酒冷茱萸晚易醺。”
楊衡《九日》:“不堪今日望鄉急,強插茱萸隨眾人。”
唐代以后,也有不少寫到茱萸的詩作。近代革命女俠秋瑾在《九日感賦》中也寫有:“思親堂上茱初插,憶妹窗前句乍裁。”
從上述引文中可見古人對茱萸愛之甚切,并賦予了它極濃郁的傳說色彩。
(選自《文史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