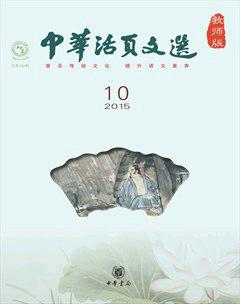年華入詩卷 心事付筇竹
李善奎
陸游《劍南詩稿》收詩9100多首,其中寫到拄杖的約460首,占整個詩作的百分之五。這個數(shù)字較酒詩、夢詩雖相對少些,但與其他意象相比,則明顯可以看出詩人對拄杖的偏愛。
陸游曾說自己有拄杖癖。他的喜愛拄杖,有高標(biāo)人格、助老扶衰的原因,更有把拄杖當(dāng)作朋友的深層因素。從他三十歲左右第一次把拄杖寫入詩中開始,在以后五十年的歲月中,他都與拄杖思想上共語,情感上共鳴,行為上共步。其《梅花》之五詩云:“江上梅花吐,山頭霜月明。摩挲古藤杖,三友可同盟。”《仲秋書事》其九云:“杖得輕堅馀可略,酒能醇勁更何求。二君最是平生舊,白首相從萬事休。”不論是“三友”還是“二舊”,拄杖皆在其中。《劍南詩稿》中直接點明拄杖為友的詩有15首之多。除上引二詩外,另如《言懷》:“論交尚喜笻枝在,白鹿泉邊溯晚風(fēng)。”《寓嘆》:“眼底誰為耐久朋,倚肩按膝一烏藤。”《九月十八日至山園是日頗有春意》:“烏藤真好友,伴我出荊扉。”可以說,詩人與拄杖同憂同愁,同喜同樂,同沐春風(fēng),同聽秋雨,同踏征途,同歷戰(zhàn)火。其《拄杖歌》詩中說:“畏途九折歷欲盡,世上誰如君耐久?老矣更踏千山云,何可一日無此君!”陸游的朋友大都是抗金愛國之士,“放翁論友尚千載,不取梁鴻即管寧”(《夜興》)。在那個以屈辱求和為基本國策的時代,這些人自然不會有好的命運好的結(jié)局。即使有人保住了性命,也往往因擔(dān)心受到陸游的牽累而不敢再與他往來。詩人不止一次地發(fā)出“紹興人物嗟誰在,空記當(dāng)年接俊游”的悲嘆。加之詩人“畏途九折”,或調(diào)任,或罷職,行蹤無定,故而身邊常常無人共語。詩人對“胡塵”的一腔不平氣和無人理解的千行愛國淚,只有拄杖最為了解。一句“世上誰如君耐久”,真讓人生千古之悲。在《大雪歌》中詩人寫道:“放翁憑閣喜欲顛,摩挲拄杖向渠說。”說什么呢?原來是說“報國寸心堅似鐵”之事。詩人有時干脆把心事付與拄杖,讓拄杖為自己分憂解愁:“年華入詩卷,心事付筇竹。”(《平水》)“提起短筇成一笑,每煩座上為分憂。”(《出游》其二)“傴僂溪頭白發(fā)翁,暮年心事一枝筇。”(《溪上作》之二)。在《春雨偶賦》詩中,詩人深情地對拄杖說:“舊交只有烏藤在,且伴禪床莫化龍。”據(jù)《神仙傳》載,費長房從壺公學(xué)道,將歸,壺公贈以竹杖,費騎之回到家中。他把竹杖丟在葛陂,遂化作一條青龍升天而去。這里用此典,是詩人勸請拄杖不要變化為龍離他而去,而要繼續(xù)留在身邊與之為伴。在陸游一生中,真是“何可一日無此君”了。既然拄杖成為陸游生活的一部分,與他心相通,情相連,行相關(guān),那么,拄杖大量地進入其詩歌創(chuàng)作中就是很自然的了。
陸游有關(guān)拄杖的詩,記錄了他一生的生活軌跡,浸潤著真實的思想感情,蘊含著深刻的社會文化內(nèi)涵。
首先,這類詩記下了詩人的愛國情操和對時政的關(guān)注。
南渡之后,士大夫文人中基本有兩種人生態(tài)度,一是或以求和換取享樂、或以逃世麻痹自己的利己主義,一是挺身而出主張抗戰(zhàn)的愛國主義。陸游自然屬于這后一種人。在宋金對峙、國難當(dāng)頭之際,他的身上凝聚著深厚的愛國情和強烈的使命感。這不但可以從其事功方面看出來,從其詩歌作品中亦可見到抗戰(zhàn)志士的奮斗和吶喊。陸游年輕時就立下了“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觀大散關(guān)圖有感》)的志向。“入蜀后,在宣撫使王炎幕下,經(jīng)臨南鄭,瞻望鄠杜,志盛氣銳,真有唾手燕云之意,其詩之言恢復(fù)者十之五六。出蜀以后,猶十之三四,至七十以后……是固無復(fù)有功名之志矣,然其《感中原舊事》云:‘乞傾東海洗胡沙,《老馬行》云:‘中原旱蝗胡運衰,王師北伐方傳詔。一聞戰(zhàn)鼓意氣生,猶能為國平燕趙,則此心耿耿不忘也。臨歿猶有‘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之句,則放翁之素志可見矣。”可知,陸游的恢復(fù)之志是貫徹一生的。況且,這種志向不是偏狹地忠于一姓一朝,而是有社稷和民族的概念在里頭,也就是忠于國家。這種以國家民族為重的愛國思想,正是后人特別推重陸詩的原因。“情以物興”,陸游的愛國之詩,可以借助任何物象來寫,“漁舟樵徑,茶碗爐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歌詠以寄此意”。陸游既然那么喜愛拄杖,所以拄杖便成為他經(jīng)常用以抒發(fā)愛國感情的審美意象。如《南樓》:“登臨壯士興懷地,忠義孤臣許國心。倚杖黯然斜照晚,秦吳萬里入長吟。”寫對關(guān)中失地的懷念。《溪上作》其一:“落日溪邊杖白頭,破裘不補冷颼颼。戇愚酷信紙上語,老病猶先天下憂。”寫憂恢復(fù)、憂天下的情懷。除了在南鄭時期,陸游有短短八個月的“鐵衣臥枕戈,睡覺身滿霜”的快意的從軍生涯之外,即使在川蜀時期,其恢復(fù)之志也是難以實現(xiàn)的。孝宗淳熙四年(1177)九月,詩人幅巾藜杖登上成都城北門樓,遠眺晚秋蕭條景象,不禁激起滿懷愁緒,于是寫下了《秋晚登城北門》一詩:
幅巾藜杖北城頭,卷地西風(fēng)滿眼愁。
一點烽傳散關(guān)信,兩行雁帶杜陵秋。
山河興廢供騷首,身世安危入倚樓。
橫槊賦詩非復(fù)昔,夢魂猶繞古梁州。
“滿眼愁”者正是“滿懷愁”之謂也。詩人所愁者,有對關(guān)塞之地烽煙不息的憂慮,有對淪陷故都的思念,有對山河興廢難料的關(guān)切,有對身世安危未卜的不安。此時詩人離開南鄭前線已五年之久,那金戈鐵馬、橫槊賦詩的戰(zhàn)斗生活雖然已成往事,但至今魂繞夢縈。這后兩句,將其報國無門、壯志難酬之悲畢呈紙上,令人感嘆不已。
陸游晚年,對個人前程考慮比較少了,但對于國家的命運卻沒有一刻放松。大概在80歲上,閑居山陰的詩人寫了一首題為《拄杖》的詩:
吾嘗評拄杖,妙處在輕堅。
何日提攜汝,同登入峽船。
此時離他入峽西戍已三十年之久了。“昔嘗西戍八千里,今復(fù)東歸三十年。”(《一編》)年老體衰的詩人面對心愛的拄杖,仍然發(fā)出與之一起同赴川陜前線的宏愿,希望再次投人到鐵馬秋風(fēng)的戰(zhàn)斗之中。
其次,表現(xiàn)了詩人強烈的生命意識和對抗金事業(yè)的高度責(zé)任感。
古語云:“志士愁日短。”陸游一生投閑置散,無法實現(xiàn)抗金理想,所以面對匆匆歲月,常有歲華搖落芳意難成之慨。在其盛壯之年便時有白發(fā)之嘆。如35歲時在福州決曹任上所寫“白發(fā)未除豪氣在,醉吹橫笛坐榕陰”(《度浮橋至南臺》),45歲西行入蜀時所寫“萬里羈愁添白發(fā),一帆寒日過黃州”(《黃州》)等等,皆為歲月蹉跎、壯志未酬而發(fā)。但是,詩人并未就此不思振作,恰恰相反,在無可奈何之際,詩人總是積極地尋求生命的長度和密度,其時間意識和生命意識異常強烈。這種心態(tài)在其有關(guān)拄杖的詩中表現(xiàn)得非常充分,正如陸游自己所說:“悠然扶杖處,歲月嘆匆匆。”(《小壘》)詩人常扶杖去尋春、探春,其詩云:“春風(fēng)常在短筇前”,“短筇到處即春風(fēng)”,“杖藜到處即春風(fēng)”,“春風(fēng)爭來拄杖前”,“倚杖來觀浩蕩春”,“要識春風(fēng)處,先生拄杖前”等。“春風(fēng)”“春色”是眼前所見之景,更是時間概念,同時,還是詩人對其政治生活前景的隱喻之詞。詩人要尋找的,正是珍貴的光陰和理想的政治機遇。到了秋天,扶策散步,也往往興發(fā)傷時之嘆。如《東村散步有懷張漢州》:“扶杖村東路,秋來始此回。寒鴉盤陣起,野菊臥枝開。憂國丹心折,懷人雪鬢催。房湖八千里,那得尺書來。”憂國心折,雙鬢成雪,無不與歲月流逝有關(guān)。詩人雖有驍騰之志,可一生伏櫪,難以馳驅(qū),既不能圖名青史,也不能長留青絲,怎不讓人怵然而驚,喟然而嘆!每當(dāng)日落時分,詩人常倚杖而立,目送夕陽,感慨萬千。“老嘆朋儕盡,閑知歲月長。柴門偶一出,倚杖立斜陽。”(《雜賦》)“我亦倚筇桑竹下,白髯蕭颯滿斜暉。”(《倚筇》)“春如人易老,愁與漏俱長。……誰見龜堂叟,搘藤送夕陽。”(《春晴》)夕陽西下,時光奄忽,想到“丈夫無成忽老大,箭羽凋零劍鋒澀”,詩人自會魂悸魄動。其《山園晚興》云:
病骨初輕野興濃,閑扶拄杖夕陽中。
草枯陂澤涓涓水,木落園林淅淅風(fēng)。
揚子凄涼老天祿,馬周憔悴客新豐。
壯心未與朱顏改,一笑憑高送斷鴻。
寫此詩時,詩人60歲,正退居山陰。詩中的揚子,即漢代揚雄,他一生郁郁不得志,在天祿閣著書,“三世不徙官”而文名益振。馬周,唐初名臣,未顯時,困厄非常,曾宿于新豐逆旅,不為主人所禮,后代替中郎將常何寫條陳,得太宗知遇,予以破格提拔。詩人對“諸公尚守和親策,志士虛捐少壯年”的社會現(xiàn)實極為不滿,但仍希望能騁恢復(fù)之志,故而在詩中以揚雄、馬周自比,說暫時的凄涼和憔悴沒有什么,應(yīng)該等待時機,以圖將來。“壯心未與朱顏改,一笑憑高送斷鴻”,該是多么高邁與灑脫,又是多么悲壯與雄豪!歲月如流,時不我待,烈士暮年,壯心不改,這種心境正是靠詩人扶拄杖踏夕陽所引發(fā)。
陸游還常以探梅尋梅的方式表達惜時奮發(fā)之情。詩人一生對梅花情有獨鐘。他的喜歡梅花與林逋不同。林逋是以隱者的眼光寫梅花的清神逸韻,陸游則多詠梅的高格,視梅的清風(fēng)亮節(jié)為同氣,同時,“梅花真強項,不肯落春后”的生命意識亦為陸游所激賞。他的有關(guān)拄杖的詩,多有尋梅賞梅之作。詩中借梅花所傳達的正是其強烈的惜時之情和頑強的生命意識。如《探梅至東村》:
乞得殘骸已累年,柴車破弊不堪懸。
閑愁正要供詩思,小疾何妨省酒錢。
忍事漸多心混混,貯書雖少腹便便。
今朝偶有尋梅興,春色爭來拄杖前。
前四句寫自己的老、窮、愁、病,五、六句作自我調(diào)侃,反說自己讀書少又能忍事,實為心明如鏡、喜論恢復(fù)之謂也。最后兩句,說自己尋梅興發(fā),亦實為生命激情勃發(fā)而然也。詩人垂暮之年,要把“閑愁”寫入詩篇,要迎春色于拄杖之前,足見其壯心未泯,愁懷難釋,充溢著把抗金事業(yè)進行到底的希冀。一年之后,詩人以78歲高齡奉詔進京,參加修撰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并打算“預(yù)大議論”,參預(yù)北伐大計,他似乎又看到了抗金救國的希望,所以在《午晴試筆》中充滿自信地宣布:“此去得非窮李廣,向來元是老馮唐。”準(zhǔn)備在政治上再展身手。這正是陸游一生中由拄杖陪伴苦苦追尋的“春色”。
再次,陸游把拄杖作為身心的寄托,以之抒發(fā)人生感悟。
在拄杖這位朋友面前,陸游可以表白自己的愛國情懷,可以宣泄難騁其志的憤郁不平,也可以尋求精神慰藉,獲得心理的安適。光宗紹熙元年(1190),詩人65歲,因所謂“嘲詠風(fēng)月”的罪名被罷歸家鄉(xiāng)山陰。對于朝中惡勢力的深文周納,無理取鬧,詩人不但沒有低頭,反而把書室名之曰“風(fēng)月”來表達抗?fàn)帲汛舜瘟T官稱之為“放逐”以發(fā)泄不滿。在題為《予十年間兩坐斥,罪雖擢發(fā)莫數(shù),而詩為首,謂之嘲詠風(fēng)月。既還山,遂以風(fēng)月名小軒,且作絕句》詩中,寫道:“扁舟又向鏡中行,小草清詩取次成。放逐尚非余事比,清風(fēng)明月入臺評。”“放逐”一詞,在后來的有關(guān)拄杖的詩中多次使用。如《放逐》:“放逐雖慚處士高,笑譚未減少年豪。……正得筇枝為老伴,盡將書帙付兒曹。”《龜堂獨坐遣悶》其二:“放逐還山八見春,枯顱槁項雪霜新。……北窗坐臥君無笑,拈起烏藤捷有神。”“正得笻枝為老伴”“拈起烏藤捷有神”者,正為排遣“放逐”之憤郁,尋求心理之慰安也。不斷遭受壓制迫害的詩人,有時會認為“游宦惡”:“行飯獨相羊,扶藜過野塘。……深知游宦惡,窮死勿離鄉(xiāng)。”(《山家暮春》之二)這種想法,面對拄杖一吐為快。陸游在為官之時也曾有歸隱之想。《自詠示客》詩中說“歸裝漸理君知否?笑指廬山古澗藤”。詩人寫此詩時56歲,在撫州擔(dān)任管理茶鹽公事的佐僚。詩末自注:“廬山僧近寄藤杖,甚奇。”可知,詩人是打算與藤杖一道踏上歸隱之路了。話雖如此說,一旦面對抱負不能實現(xiàn)、功名一無所成的現(xiàn)實,詩人就難免悲觀惆悵:“平生不到三公府,晚歲歸來五老庵。……笑語床隅拄杖子,即今惟汝是同參。”(《十月二十四日夜夢中送廬山道人歸山》)“勛業(yè)文章謝不能,生涯分付一枝藤。”(《晨起》)他要把這種痛苦和失落告訴給拄杖,甚至把整個不適意的生活托付給拄杖。
不論為官還是賦閑,生活給予陸游的只有挫折和打擊。幾十年的歲月就在無數(shù)次希望、無數(shù)次努力和無數(shù)次幻滅中流逝了。年老之后,貧病交加,僵臥孤村,“既不能挺長劍以抉九天之云,又不能持斗魁以回萬物之春”(《寒夜歌》),撫今追昔,便常常想起伴隨自己一生的拄杖。詩人八十多歲時所寫的《拄杖示子遹》說:“拄杖相從四十年,交情耐久獨依然。西窮巫峽崛江路,北抵岐山渭水邊。早已歸休弄泉石,老猶緩步歷風(fēng)煙。會同缽袋并禪版,付與兒孫世世傳。”詩人要把拄杖和缽袋禪版付與兒孫世代相傳。拄杖是詩人戰(zhàn)斗經(jīng)歷的見證者,也是寂寞無助時的共語人。拄杖最了解詩人的愛國憂民心,也最清楚詩人壯志未酬的滿腔悲憤以及“報國欲死無戰(zhàn)場”的無可奈何,而拄杖的“交情耐久”,更令詩人感動。把拄杖作為傳家之寶傳與后人,其意義不言自明。至于缽袋禪版,那只是詩人不能對外實現(xiàn)參與而不得不回縮內(nèi)心的一種平衡方式。《劍南詩稿》中寫到佛道的詩不算少,其中有“拄杖”字樣的就有26首之多。尋繹詩人本意,并不是真的在皈依佛道,而是如同說歸隱一樣,只是一種憤世嫉俗的牢騷而已。所以詩人的這兩樣傳家寶,其真正的意義便是參與和憤世。參與在于實現(xiàn)抗金壯志,憤世在于獲得心理安適。詩人臨終前的某一天,還寫了一首《贈拄杖》詩,把與拄杖共同生活的經(jīng)歷以及對拄杖的深厚感情,作了一個總結(jié)。
此外,拄杖還記錄了陸游與農(nóng)民和友人之間的交往,以及對自然風(fēng)光的喜愛。如“從今若許閑乘月,拄杖無時夜叩門”(《游山西村》),寫熱愛家鄉(xiāng),與農(nóng)民親密無間;“放翁老憊扶藜杖,也逐鄉(xiāng)人禱歲豐”(《初夏》之九),寫關(guān)心民生疾苦,為求豐收而虔誠祈禱;“今旦微霜好風(fēng)日,短筇且領(lǐng)鏡湖秋”(《曠懷》),寫欣賞鏡湖秋景;“欲尋梅花作一笑,數(shù)枝忽到拄杖邊”(《探梅》),寫探梅迎春,其樂融融。這些詩歌,反映了詩人生活和性格的另一方面,讓人讀之,會“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帖出當(dāng)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狀”(錢鐘書《宋詩選注》)。陸游在《倚杖》詩中說:“年來詩料別,滿眼是桑麻。”生活環(huán)境和生活內(nèi)容的變化,自然會讓詩的題材和詩人情感發(fā)生一些變化。
不可否認,陸游有關(guān)拄杖的詩中也有較為消極的思想內(nèi)容,如前引《拄杖示子遹》中把缽袋禪版?zhèn)髋c子孫的說法,已可看出佛道對詩人的影響。不過,總的來說,詩人并未走上逃世一路,他在《長歌行》中曾說:“不羨騎鶴上青天,不羨峨冠明主前,但愿少賒死,得見平胡年。”無論仙佛、富貴,他都不在意,他所耿耿于心的只是驅(qū)逐敵人、光復(fù)祖國的偉大事業(yè)。愛國主義始終是他一生的主導(dǎo)思想。
陸游的生活道路是曲折坎坷的,生活內(nèi)容是豐富厚重的。這一切,都在其拄杖身上留下鮮明的印記。我們讀讀他的這類描寫拄杖的詩,無疑會對其心路歷程和思想個性有一個更為全面的了解,也會對當(dāng)時的社會文化狀況有一個更為清楚的認識。
(選自《古典文學(xué)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