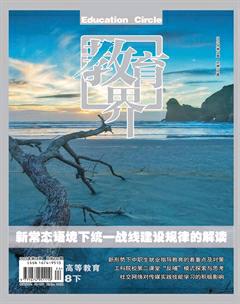沈宗騫畫論對當代繪畫教學與創作的啟示
韋秀玉
【摘 要】本文通過將沈宗騫畫論中的藝術教育理念與中國當代藝術院校繪畫教學及繪畫創作中存在的問題相對照,探析藝術教學改革的方法與習藝者提高個人藝術修養及品格的途徑,闡述古代畫論中精深的義理,為當代藝術教學與藝術創作提供資鑒作用,從而持續發展具有民族氣質的繪畫藝術。
【關鍵詞】沈宗騫畫論 ? ? 當代繪畫教學 ? ? 創作
清代繪畫理論集前代之大成,數量、篇幅與系統性都勝過前代。書畫家沈宗騫(1736—1820)離群索居,以書畫遍游吳越,致力于復古,功力深厚,雅負盛名,著有《芥舟學畫編》(成于1781年)四卷,痛斥文人畫和宮廷繪畫都日漸衰微而俗學日益風行的現象,詳細地論述了繪畫之正法,尋源溯流,旨在為畫道指南。中國現當代繪畫,經歷西風東漸之后,在藝術教育與藝術創作方面形成了由于仿效蘇聯藝術教育模式,出現了過于傾向于現實主義再現的種種弊端,致使中國源遠流長的藝術傳統受到忽視。“惟能學則咸歸于正,不學則日流于偏”,如何在東西方文化融合與碰撞中發展中國傳統的藝術精神,是當代藝術教育者及創作者面臨的重要課題。讀史使人明智,讀沈氏之《芥舟學畫編》,使人由迷而悟,若東方之欲曙。
一、立超絕人格
德國偉大詩人歌德曾說:“一個作家的風格是他的內心生活的準確標志。”“如果想寫出雄偉的風格,他也首先要有雄偉的人格。”文學與繪畫是藝術的不同形式,二者相融通,雄偉的人格對作家如此重要,畫家亦如此。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也同樣強調人格在藝術創作上的決定性作用,認為藝術家在表現方式和筆調曲折等方面完全顯現出他(她)的人格特點。畫格高下亦如人品,如何提高個人藝術修養與品格,是每個習藝者面臨的問題。沈氏在卷二“山水”篇“立格”中有言:“夫求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曰清心地以消俗慮,二曰善讀書以明理鏡,三曰卻早譽以幾遠道,四曰親風雅以正體裁。具此四格者,格不求高而自高矣”。首先要求習藝者清心以體驗藝術之道,不似一些畫者有意揣摩相關展覽評委的喜好而蓄意迎合,導致題材與形式的過度相似、千人一面的非正常現象,究其原因就是俗慮過多,致使本末倒置,忘卻藝術創作的本質。以至于英國學者Julian Stallabrass在其著作《當代藝術》中如此評價中國的當代藝術:
“在參觀了2002年在香港舉辦的‘第九屆全國美術展覽中的部分作品后,……這個展覽的油畫部分展出了大量讓人印象深刻、描繪中國當代生活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它們的創作風格是多種多樣的,而且在技法上往往顯示出高超的造詣……一些作品……(在我眼里)似乎是庸俗得不可求藥——《凡心已熾》不是一個你能期望在倫敦或紐約出現且毫無諷刺意味的標題。由于缺乏應有的西方參照對象(實際上有很多這樣的對象,但包括印象主義在內,都是較為陳舊的風格)和非功利的追求,他們全都帶有某種宣傳功能,這樣的作品與西方作品迥然不同,因而難以在全球化的藝術系統中脫穎而出。”
因此,善讀書以明畫理與畫道,通曉中西古今的藝術發展史,應是美術教師與藝術創作者必備的常識,如此方能明確當下個人所處的時空位置,才可能有效地進行創新性藝術指導或實踐。否則便是重復藝術史上某個階段的覆轍,失去藝術創作的意義,也喪失了與國際藝術界對話的可能。誠然,畫論、美學、哲學以及相關文化的研讀也是構成個人藝術品格必備的養料,如此培養與體驗藝術的精神,使繪畫藝術的教學與實踐由表象的描摹升華至精神的表達,提高藝術作品的精神內涵,創造清新雅逸的繪畫作品,從而使藝術悅己亦悅人。至于“卻早譽以幾遠道”,談及的是那些藝術創作者過早涉足沽名釣譽之事,其作品與隱忍數年而厚積薄發之士所造相比則多了些媚俗,少了些風雅。四是“親風雅以正體裁”。何為風雅?沈氏在卷二“山水”篇中就“避俗”問題做了詳盡的論述:
雅之大略亦有五:古淡天真,不著一點色相者,高雅也;布局有法,行筆有本,變化之至,而不離乎矩矱者,典雅也;平原疏木,遠岫寒沙,隱隱遙岑,盈盈秋水,筆墨無多,愈玩之而愈無窮者,雋雅也;神恬氣靜,令人頓消躁妄之氣者,和雅也;能集前古各家之長,而自成一種風度,且不失名貴卷軸之氣者,大雅也。
沈氏之風雅可以理解為,藝術表現上發揚古人的詩性表達,重墨輕色,行筆線條多變又能整體有序而不凌亂,構圖別致,蘊含詩性意味,強調于繪畫中表達精神,使觀者能消除躁妄之氣。另外,重視博采眾長的同時亦強調個人的創造性,從諸多方面進行藝術的修習與實踐,培養個人超絕之品格。
二、習自古人
沈氏在《芥舟學畫編》卷二“山水”中討論“摹古”時有言:“學畫者必須臨摹舊跡,猶學文之必揣摩傳作,能于精神意象之間,如我意之所欲出,方為學之有獲。”主張向古人學習,注重體驗前輩藝術的精神意象,如此進行個人藝術的修習。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山水訓”篇中就摹古亦作精辟論述:
人之學畫,無異學書。今取鐘、王、柳,久必入其仿佛。至于大人通士,不局于一家,必兼收并攬,廣議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后為得。今齊魯之士惟摹營丘,關陜之士惟摹范寬。一己之學,尤為蹈襲,況齊魯、關陜,幅員數千里,州州縣縣,人人作之哉?專門之學,自古為病,正謂出于一律。……人之耳目喜新厭故,天下之通情。余以謂大人通士不拘于一家者此也。
沈宗騫與郭熙對于學習先輩的方法持相同的論調,反對蹈襲一家之技藝,而主張博采眾長,兼收并攬,然后通達而自成一家,自出精意。尤其注重創新的清代畫家石濤也倡導“借古以開今”,同時又強調自我的創造精神,主張變通,“我之為我,自有我在。……縱有時觸著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于古何師而不化之有?”當代學者應深入掌握古今中外之藝學,方能變通于古今中外之法理,表達自我內心的感受與情愫,縱使借用某家之筆法與構想,亦是為我所用,描寫天地萬物而陶詠自我。
然而,我國眾多藝術院校的繪畫教學以寫生為主的教學模式,造成當今中國畫壇多以寫實再現的創作模式,歷屆畫展中作品的題材與藝術形式都過度相似,當然這也包括其他各種原因所致。而襲自蘇聯的現實主義的招生、教學、評價模式,導致許多習藝者傾力于自西方文藝復興時期至19世紀末期再現手法的練習,這應是構成中國畫壇現狀的主要因素。現今藝術教學與創作中由于過于傾向客觀的再現,中國傳統藝術的法則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而沉積于歷史長河,這真是莫大的遺憾;而對于西方現當代藝術大師所創造的表現手法亦未駐足。長此以往,株守一法而規摹之,必生習氣,甚至于對藝術產生厭倦之意(許多業內人士已怠于藝術創新實踐,流于程式化藝術創作當中,以至于國內美術大展時業內人士都缺乏觀看熱情)。在高度信息化的當代社會,只有研習東西方各大家之長,才能將自己置于當代藝術語境中,發展自我,成就英才。近現代出現了一批融中西文化于一體、揚中國藝術精神、于國際藝術之林中脫穎而出的華人藝術家,如林風眠、朱德群、趙無極、吳冠中、徐冰等等,吸納中國傳統文化內涵,巧妙結合西方現當代藝術表現語言及形式,創造了獨特的藝術作品,為中國美術史乃至世界藝術譜寫了重要的篇章。正如沈氏所言:“茍能知其弊之不可長,于是自出精意,自辟性靈,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不襲不蹈,而天然入彀[ 入彀:與古法相合],可以揆古人而同符。即可以傳后世而無愧,而后成其為我而立門戶矣。”博采中西方大家之眾長,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方能創作出具有民族特色、時代氣息與個性特質的藝術作品。
三、避俗就雅
沈氏認為,畫與詩皆為士人陶寫性情之事,雅者能陶冶人的情操,畫俗則如詩之惡,是應去除。如何避俗,沈氏如是說:
“……夫畫俗約有五,曰格俗、韻俗、氣俗、筆俗、圖俗。其人既不喜臨摹古人,又不能自出精意,平鋪直敘,千篇一律者,謂之格俗。純用水墨渲染,但見片白片黑,無從尋其筆墨之趣者,謂之韻俗。格局無異于人,而筆意窒滯,墨氣昏暗,謂之氣俗。狃于俗師指授,不識古人用筆之道,或燥筆如弸,或呆筆如刷,本自平庸無奇,而故欲出奇以駭俗,或妄生圭角,故作狂態者,謂之筆俗。非古名賢事跡及風雅名目,而專取諛頌繁華,與一切不入詩料之事者,謂之圖俗。能去此五俗,而后可幾于雅矣。”
如何在藝術教學與藝術創作中宣揚中國優良的藝術傳統,避俗而就雅,是當前藝術界面臨的重要問題。首先,在藝術教學方面,藝術教師應當把自己作為一個教師而不是作為一個藝術家傳授個人的技藝,致使學生的繪畫題材、藝術語言過度趨于同一。筆者曾譯西班牙現代繪畫教程,著者為西班牙巴塞羅那藝術研究院教授與視覺藝術家,在教程中,他們首先根據繪畫語言的分類——形、線、色彩與空間將教程分為四冊,然后再根據語言呈現的風格類型組織單元教學,先闡釋語言的藝術特性,再列舉運用此種語言的代表藝術家的經典作品進行深入分析,進而激勵學生學習大師的表現手法,組織學生開展不同題材內容的創作,并注重不同材料的嘗試,非常淺顯地引導習藝者理解藝術,從而嘗試藝術的表達與創造。筆者在藝術教學中曾采用同樣的教學方式,激發了學生的藝術表現興趣,教學效果良好。其次,對于藝術創作者而言,如果在繪畫中僅是刻板地描摹客觀物象或描畫照片,滿足于這種客觀性的記敘,這與藝術的創新特質是相悖的。正如黑格爾所言:“純然外在的客觀性不能揭示內容的完滿實體性,藝術家就不應致力于此。”或是承襲一家之藝,或外在簡單地拼湊藝術形式及題材內容,或粗糙地凸顯怪誕的獨創性,都易于“格俗”與“氣俗”。美學家黑格爾同樣主張藝術家應完全掌握藝術表達的客觀規律,他(她)才能在所表現對象里同時表現出自己最真實的主體性,從而創作出獨創性的藝術作品。習藝者應多讀書參名理,汲取古今中外大師的精華,內化為個人的藝術特質,方能令方寸之際,纖俗不留,從而使自我與作品溫文爾雅,表達豐富的精神及文化意涵,通過心靈的活動,把自在自為的情感或精神品性從內在世界中揭發出來,使它真實地外化為形象,運用內在的生性灌注作品,從而產生真正的藝術美。
總之,沈氏的畫論對中國當代藝術教學與藝術創作有著積極的資鑒作用,據此去改善中國當代藝術教育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教師、學校及社會文化機構都應共同努力、各司其職。首先,教師作為藝術教育的主導者,應博學多才、見多識廣,盡可能引導學生向古人先輩及杰出的當代藝術家學習,使學生通達而自出精意。其次,社會及學校的博物館、展覽館及美術館作為文化服務機構,應增加藏品或展品質量與數量,并加強管理,為習藝者與大師之間的交流創造機會,激勵藝術愛好者的創作熱情。其三,習藝者應當虛靜讀書并潛心研習畫理與畫道,提高品格,去俗就雅。唯有如此,中國畫界才能清新怡人,使觀者如沐春風,復興中國悠久而獨特的藝術精神。
【參考文獻】
[1]〔清〕沈宗騫.芥舟學畫編[M].潘耀昌編著.中國歷代繪畫理論評注,清代卷(下).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9:72,89-90,94,100.
[2] 〔德〕歌德.論文學藝術[M].范大燦,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65.
[3]〔德〕黑格爾.美學(第一卷)[M].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366-368,372.
[4]〔英〕Julian Stallabrass.當代藝術,王端慶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199-200.
[5]〔宋〕郭熙,郭思.林泉高致[M]//自俞劍華編,中國畫論類編[G],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57:633.
[6] 〔清〕石濤.石濤畫語錄,俞劍華注釋,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7.
[7]〔西班牙〕吉瑪·嘉絲奇,瓊瑟·阿什辛. 形、線、色彩、空間(西班牙現代繪畫教程)[M].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