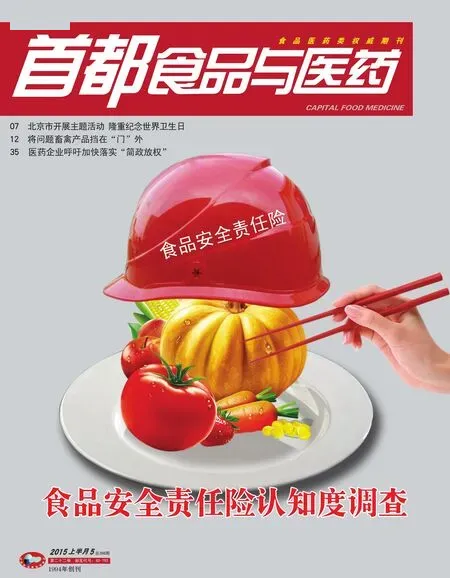堅守西藏三十余載的妙手大師
——訪解放軍第八醫院疼痛科主任張德鵬
◆本刊記者 許方霄


正是由于高寒、缺氧的高原環境,才使西藏成為肩周炎、頸椎炎、坐骨神經痛等病癥的高發區,這些病癥令當地軍民痛苦不已。除了疾病帶來的痛苦外,他們甚至感到絕望——靠先進的藥物目前尚無法根治。就在他們似乎已經習慣了默默忍受折磨之時,高原上來了一位妙手仁醫,帶著他精湛的醫術,穿梭于這片圣潔的雪域高原,用銀針和嫻熟的手法點亮患者心中那盞即將熄滅的希望之燈。他,就是張德鵬,一位幾乎走遍高原每一個角落,堅持在西藏駐守31年的倔強軍醫。
減輕患者痛苦是行醫初衷
張德鵬出生在甘肅酒泉臨水鄉的一個小村莊。由于氣候原因,冬季長時間的寒冷令張德鵬所在的村子里很多人都遭受關節疼痛的困擾,看著熟悉的臉龐上泛著痛苦的表情,張德鵬的心像被人狠狠地扎了一下,心里產生莫名的難過,一個“我要學習醫術,為患者減輕痛苦”的念頭跳進他的腦海。那一年,張德鵬還是個初中生,剛剛15歲。
在治病救人的責任和對醫學的無限憧憬下,張德鵬四處搜集醫書,并就此走上了漫漫自學之路。張德鵬說,自己有個“啟蒙老師”——當地一位有名的老中醫。這位老中醫祖上四代行醫,是個不折不扣的中醫世家,為了能學到更多的醫術,張德鵬每天放學后都會到老中醫家里去,看他如何為病人把脈、扎針,跟他學習怎么開藥。
談起自己診治的第一位病人,張德鵬至今印象深刻:那還是1974年的一個冬天,村里有一個13歲的女孩兒犯了風濕性關節炎,但由于女孩兒的父母都是“走資派”,即使四處苦苦哀求,也無人敢替“走資派”的女兒診治。無法言喻的病痛使女孩兒疼得哇哇直哭,女孩兒的父母看著是既著急又心疼,但現實很無奈,他們當前能做的也只是不停地流淚。也許實在是別無選擇了,女孩兒的父母最后找到了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張德鵬。女孩兒痛苦的哀號聲使張德鵬的悲憫之心瞬間涌上心頭,雖然緊張,但他還是從容地拿起銀針。銀針刺進女孩兒皮膚的那一刻,意味著張德鵬真正走出了行醫生涯的第一步。張德鵬連續一個星期幫女孩兒針灸治療,女孩兒的疼痛感逐漸消失。看到女孩兒一家人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張德鵬才放心地舒了口氣。
隨著治療的病人越來越多,張德鵬的名氣也越來越大,鄉間鄰里只要有點不舒服,都會來找張德鵬給瞧瞧。由于擁有醫術上的特長,張德鵬在高中時就被當地醫療合作站招去,當起了赤腳醫生。在張德鵬眼中,自己是個幸運的人。“那個時候,大城市的醫生們都會組織醫療隊到農村來,對農村的合作醫療站的醫療骨干進行培訓。”張德鵬說,在這為期3個月的醫療培訓中,他的醫學知識和醫療技術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提高,這也使他更加堅定也更加勤奮地學習傳統醫學。

▲年輕時期的張德鵬夫婦
不能放棄“老本行”
憑著醫術上的好口碑,1976年2月,張德鵬被特招入伍,并被分配到重慶某工程團衛生隊,專門從事針灸推拿工作。1977年,張德鵬來到重慶的解放軍163醫院進修放射專業知識,但對于自己的“老本行”,張德鵬舍不得就此丟下。他將點點滴滴的休息時間充分利用起來,刻苦鉆研針灸、按摩、正骨等知識。
張德鵬所在的工程團長年挖深井、打隧道,長期要彎腰低頭,加之受風寒影響,很多戰士們患上頸椎病、肩周炎、腰背病等病癥。雖然張德鵬在家鄉名聲在外,但他深知醫學就像一片廣闊天地,自己目前所掌握的猶如滄海一粟,等待他去學習和研究的東西還有很多。為了能使戰士們盡快擺脫腰背病折磨,張德鵬可謂是使盡全力,為了更精準地找到人體相關穴位,準確地把握力道,張德鵬不惜以自己為“靶子”,用銀針在自己身上進行反復試驗。
此外,張德鵬還多次利用休假機會,向行業內諸多知名專家教授和民間醫生請教。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多年的艱辛摸索,急性腰扭傷、小關節紊亂、椎體錯位等不同類型的腰背病,都被張德鵬一一攻克。當年的赤腳醫生,此時已成為部隊人人皆知的“妙手神醫”。因工作成績突出,1982年12月,張德鵬被破格提升為干部,不久又被調到解放軍163醫院放射理療科專門從事針灸推拿按摩工作。
1984年,張德鵬在重慶的部隊已經生活了8年,這8年的部隊生活雖然艱苦,但在張德鵬看來,為無數戰士們解除痛苦給他帶來了別人無法體會的快樂,而且在這期間,張德鵬也與一位善良而美麗的湖南姑娘結成連理。就在張德鵬以為一切就這么按部就班地生活下去的時候,部隊傳來援藏的號召。由于西藏缺醫少藥,成都軍區打算派出100名醫務干部前往西藏進行援助,張德鵬沒有經過太多考慮就申請進藏,但很“不幸運”地被分在全軍海拔最高的解放軍第八醫院工作。
再難也要堅守下去
離開重慶,前赴高寒缺氧、環境艱苦的西藏,留下新婚妻子獨自一人,張德鵬心里也不好受,覺得對不住她,但為了邊遠地區更多病患的福祉,他強忍心中的留戀與不舍,毅然遠行。張德鵬說,西藏是坐骨神經痛、肩周炎、肱二頭肌腱炎等世界性疑難雜癥的高發區,來到這種特殊環境也是對他提出了新的挑戰。
張德鵬坦言,剛去西藏的時候確實存在不適。氣候不好,海拔3900米,缺氧,高原反應產生的生理反應讓張德鵬極度難受。“當時的西藏生活條件特別艱苦,天天就是自己煮些面條,偶爾蒸些米飯。那時候沒有新鮮豬肉賣,更別說新鮮蔬菜了。饞肉了,就托人買上點凍豬肉。”張德鵬笑著回憶道。海拔5300多米的查果拉山,四季都覆蓋著厚重的白雪。長年駐守在查果拉哨所的官兵們在此嚴重缺氧的高原上,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心臟腫大、造血功能異常、風濕性關節炎等高原疾病。張德鵬不知道已經多少次避過雪崩、塌方來到這里,為駐守的戰士們診治。提及此事,張德鵬不禁紅了眼眶,他說,為守邊防,戰士們幾乎是用生命在戰斗,只要能讓他們擁有健康體魄,即使路途險阻又有何妨?“我能做的就是盡自己最大的能力,為他們服務好”。縱然經歷萬種艱險,張德鵬都沒有萌生逃離西藏的心思,他時刻提醒自己:“我是名軍人,同時也是名救死扶傷的醫生,當地軍民需要我!我必須堅守在這個需要我的地方!”這個信念像一座巍峨的高山,始終屹立在張德鵬的心中。多年來,張德鵬多次深入邊防一線,為邊防戰士和地方群眾巡診達上萬人次。
按規定,援藏工作3~5年的援藏軍醫就可以申請回內地工作。為了能一家團圓,張德鵬的妻子及家人多次提議讓張德鵬轉業。一邊是無時無刻不掛念的家人,一邊是飽受病痛折磨的西藏軍民,張德鵬該做如何抉擇?“既然已經來了,就要好好地干一番事業!”倔強的張德鵬最終說服家人,堅持要留在這個讓他放心不下的高原,用他手中的銀針和自己摸索出來的獨特手法為患坐骨神經痛、面癱等疾病的西藏軍民送去希望。今年是張德鵬堅守西藏的第三十一個年頭,當年百名援藏軍醫如今只剩下他一人依然留在西藏。
大師是從“創造”中出來的
除了父母起的名字以外,張德鵬還有一個代號——大師。張德鵬笑著說,這個稱呼是部隊的戰友們給起的,從年輕時就一直被這么叫著。對于這個稱號的由來,張德鵬解釋道:“大師的意思不單是專家,還有創造者的意思。”張德鵬認為,一名真正的醫者,不能一味地照搬書本,必須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創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思想與手法。如今,大師張德鵬的很多治療手法和方法在書上是找不著的,因為那是他在治療過程中不斷摸索出來的經驗總結。張德鵬說,與中醫的辨證論治說法相似,針灸、正骨也得根據掌握的病情情況來具體對待。“同一個病在同一個患者身上,治療方法可能都不一樣,而且扎針的手法、角度也要根據自己的想法去扎,這不是找書就能夠學會的。”
治療面癱是張德鵬的擅長領域之一。憑借自己的獨特手法和創造性想法,在某些病例治療中,張德鵬會將兩個穴位串起來,他說,雖然病人當時會感覺特別疼,但經過多次治療驗證,效果都特別好。其實,張德鵬的“自學成才”與其多年從事放射科工作有很大關系,因為放射科對人體解剖方面的知識要求很高,所以患者在得了腰背病以后,只要把拍的片子放到張德鵬的面前,張德鵬立刻就能知道此病的原因所在。“在哪個位置有問題,扎針和正骨的時候我就能想到,因此,只要按照相應的手法或針灸的配置去治療就沒什么問題了。”但嚴格來說,張德鵬不能被稱之為“純針灸人”,因為純粹學針灸的人,只是按照中醫理論,如奇經八脈、十二經絡等來下針,而張德鵬所運用的針灸、正骨等手法卻是從解剖的角度出發,是西醫基礎上的中醫。為了更直觀地表達,張德鵬舉例說:“比如關節脫臼,或者在腰椎檢查之后,雖然感覺很疼,卻沒發現有骨折跡象,但用解剖的知識,我則認為,這種疼痛是由小關節的錯位引起的,而這種錯位,儀器是檢查不出來的。”此時,張德鵬則憑借自己的豐富經驗,將中西醫結合,為患者正骨、按摩、針灸,無需打針吃藥,患者很快就恢復了健康。
基于張德鵬不斷創造新技術的精神和取得的優異成績,西藏軍區還授予他“自學成才先進個人”的稱號。但張德鵬卻沒有將他的獨創手法編寫成書,對此,他雖然感到很遺憾,但卻表示“沒辦法編”。“同一個面癱,針灸的方法都不一樣。根據面癱的具體情況,哪一根經絡上來以后,再根據面部的幾種表情來配穴,包括面部本身和背、腿、手的穴位。在治療坐骨神經痛、肩周炎、腰椎間盤突出等病癥上也是同樣的道理。”張德鵬說,“即使編成書也是不行的,因為很多都是我自己經驗的總結,如果編成書了,別人在看過之后很可能會按照同樣方法去實施,但因為情況不一樣,比如患者的舌苔、脈象等存在差異,即使在同一個人身上,治療方法也可能是不一樣的。像開中藥一樣,特別是針灸,配穴特別重要,書是死的,但是扎針、按摩是活的,必須得根據具體情況來操作。”

▲張德鵬在厄瓜多爾為病人診治

▲在中厄兩國建交紀念會上,張德鵬(右二)與厄方領導合影
神醫美名傳播國際
2004年的一個夏日,正在休假的張德鵬突然接到成都軍區外事辦的電話。“不是有什么緊急情況吧?”張德鵬接聽電話后,才知道有一個援外醫療任務,成都軍區外事辦打電話的目的就是問其是否參加。“這個任務很光榮,得去!”張德鵬再一次“先斬后奏”,沒有和家人商量就立馬答應下來了。
援外醫療,顧名思義,就是前往國外進行援助醫療工作。與駐扎西藏不同,張德鵬這次必須得遠渡重洋,在一個既遙遠又陌生的國家——厄瓜多爾待上一年半時間。得知消息后,張德鵬的妻子是又氣又擔心,但張德鵬的性格她又怎會不了解?她知道,當前她能做的,就是偷偷擦掉眼角的淚水,好好珍惜寶貴的相聚時間,不斷囑咐丈夫多注意身體、照顧好自己……去厄瓜多爾的前幾天,孝順的張德鵬夫婦來到甘肅酒泉,看望年邁的父母。張德鵬說,當時也和父母“聊了聊”。得知兒子即將前去國外,張德鵬的父母并沒有阻攔,而是讓兒子到國外放心工作,不用擔心他們。父母的深明大義讓張德鵬無比感動。
“當地醫療設備十分欠缺,走的時候我們從國內買了一些醫療器械帶過去。”張德鵬回憶道。2014年8月,張德鵬作為醫療隊隊長帶領醫療隊到達厄瓜多爾的三軍總醫院。雖說中國醫療隊員的醫療水平遠遠高于當地醫生,但若想很快在異國打開局面亦是不易之事,但張德鵬及中國醫療隊卻很快獲得厄瓜多爾及國際上的贊譽。到厄瓜多爾沒多久,張德鵬就接手一個病人——一個患了面癱的大學生,這個大學生在當地醫院做了四個月的治療,結果卻越來越糟糕。“嘴角得掛鉤子,不然受不了,當地已經治不好了。”張德鵬說。最后,這個大學生懷揣最后的希望來到三軍總醫院,并被安排給張德鵬。從接診的第一天起,張德鵬每天都會耐心地為其針灸,半個月后的一天,該患者突然氣急敗壞地質問張德鵬:“整張臉繃得太緊了,還使勁跳,感覺特別難受”。“這說明神經馬上就要恢復了。”張德鵬興奮地說,并讓翻譯及時告訴患者,讓他放心。就在患者將信將疑,并焦急等待之中,“整張臉一下子就全都恢復過來”。這個消息像插上翅膀,在厄瓜多爾的首都基多市瞬間傳開了,張德鵬更被當地人視為神醫,每天來找他看病的患者都是排著長長的隊伍,他根本就沒有坐下的時間。雖然援外任務重,工作強度大,但張德鵬誠懇地說,看到親手治好的病人臉上洋溢著笑容,自己心里也會很開心,這種幸福感超越了其他,也就忘卻了疲憊。
由于張德鵬盛名在外,厄瓜多爾唯一一所培養研究生的重點大學——玻利瓦爾大學研究生院隨即邀請張德鵬為醫學系學針灸和按摩專業的20多名研究生上課。只要有張德鵬的課,不必打聽他在哪間教室,順著掌聲最熱烈的地方走去,準能找到。教室里的張德鵬認真講解,仔細示范,還不時過來糾正學生的錯誤手法,一幕幕專注而溫馨的場景,讓所有人感動于中國傳統醫學的強大力量,它讓國籍的差異和語言的障礙不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正氣源于原則
見到張德鵬的第一眼,就會感受到他由內而外散發的正氣。張德鵬說,自己的性格隨父親。張德鵬的父親自小就在農村生活,是苦孩子出身,解放以后,18歲就當了村支部書記。張德鵬說,身為老共產黨員的父親原則性非常強,也是個非常正直的人。“現在80多歲的人了,還經常教導我們要做個正直的人。”也正是在這股正氣的作用下,雖然張德鵬診治了難以計數的病例,卻從未出現過一例收受錢物的事。
張德鵬說:“雖然年輕的時候日子過得很清貧,家里還有老人,但是我從來不接受別人的一分錢,這是我的原則。”張德鵬也毫不避諱地說,也許是為了感謝自己的幫助,也或許是受當前“送紅包”的風氣影響,他確實也遇到很多病人給自己“塞錢”的情況。每當這時候,張德鵬都會收起平日和藹的笑容,嚴肅地說:“你要給我錢,可以啊,那你明天不要來了。”看到張德鵬“變臉”了,患者們都會略感尷尬地拿走錢。說起自己的“不近人情”,張德鵬哈哈地笑著說:“這是我的原則,不能壞。”
即使尚在休假期,在醫院的病房里也會經常看到張德鵬的身影。只要病人找到他,張德鵬都會給他們治療。在來北京參加“最美援外醫生”頒獎典禮的前一天,張德鵬還在為一位得類風濕關節炎的病患做治療。該病患已經去過廣東省好多大醫院,在某大醫院打一針就要開銷8000元錢,十多萬元花出去了,但病痛卻仍然沒有好轉的跡象。面對頑疾,該病患的目光中浮現出絲絲絕望。也許是上天眷顧,該患者無意中得知張德鵬在這方面具有極高造詣,幾經周轉之后終于找到張德鵬。“剛開始的時候,他的手都蜷不起來,但畢竟才一年,骨頭還沒變形,還沒發展到骨節增生。”對于這位絕望的病人,張德鵬耐心地勸他放寬心,并表示很有信心治好他的病。果然,在接受張德鵬7天的治療后,該病患的癥狀就得到了緩解。問及這種情況要花費多少錢后,張德鵬樂呵呵地說:“看到別人痛苦,我就給他治一下嘛,不要錢。”
“年輕的時候,要好好地把手藝學好,飯后休息半個小時,其余時間全部看書,醫學方面的書都要看。有了知識的積淀,工作以后再積累經驗,技術才能提高,才能成為有用的人。”這是張德鵬經常對學生們說的話,這是他對學生們的要求,更是他自己一路走來的寫照。“既然選擇了醫生這一行,要做就要做好,如果半途而廢,劃不來。”
人物小傳

張德鵬,1957年12月出生于甘肅酒泉,解放軍第八醫院疼痛科主任,技術五級。1976年入伍,在解放軍基建工程兵00282部隊衛生隊任班長,曾多次被評為學習雷峰先進個人;1982年調入成都軍區163野戰醫院放射理療科;1984年調西藏軍區解放軍第八醫院放射理療科;1995年任放射理療科主任。2004年8月至2006年2月在厄瓜多爾執行援外醫療任務,被厄瓜多爾國防部授予“部隊之星”榮譽勛章。2006年被西藏軍區樹為先進典型,評為“自學成才先進個人”,并榮立三等功。2015年3月被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授予“最美援外醫生”提名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