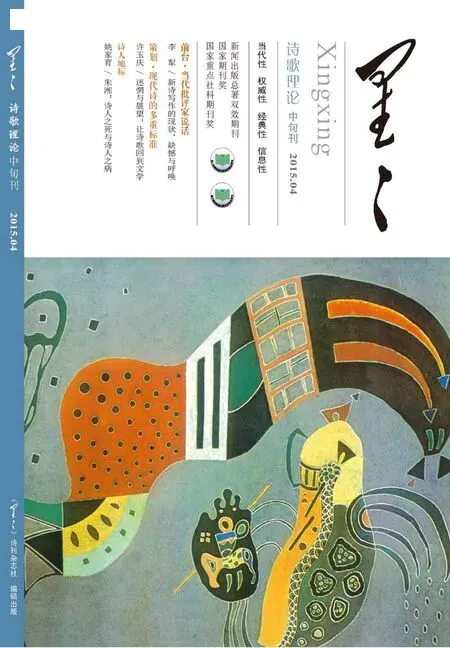迷惘與展望:讓詩歌回到文學
——談當下詩歌創作評價的標準問題
許玉慶
迷惘與展望:讓詩歌回到文學
——談當下詩歌創作評價的標準問題
許玉慶
中國現當代詩歌已經走了上百年的歷史,期間有過輝煌有過低谷,自然也出現了諸多燦爛的詩篇。但是在當下詩壇,從詩人、評論家到普通讀者爭議最多的莫過于“什么樣的詩歌才是好詩?”一方面,大批詩人在自己的藝術世界中默默耕耘,舉辦大量的大獎賽、出版各式各樣的民刊,在歲月的時光中書寫著自己的詩章;另一方面,詩歌從來都不寂寞,各種現象、各種爭議讓詩歌界熱鬧非凡。很多人會追問:今天為什么再也寫不出好詩?無論是詩人還是詩歌評論家,不管是表現出極度關注的神態,還是一副無所謂的態度,都無法回避這一問題。特別是近年來接連發生的所謂“梨花體”、“烏青體”事件,更是將當下詩歌創作推向風頭浪尖。詩人們憤怒了,認為這是一些不懂詩歌的人在亂嚷嚷,或者認為詩人是走在時代前列的先鋒,自古至今大詩人都是在當時被貶低和不為理解的,或者說:你看不懂,是你不懂詩歌。那么,好詩的標準究竟是什么?當然,這也是個莫衷一是的問題,但我們總還是能探討一下。我認為,最好的答案就是將詩歌本身放逐到文學世界中去,讓她自己找到屬于自己的方向。
一、明白易懂是不是就是好詩
在對詩歌評判的標準上,歷來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標準:一種認為詩歌越難懂越好,通俗易懂的詩歌不是好詩,持這種觀點者很容易陷入神秘主義的誤區;另一種觀點認為,通俗易懂的詩歌才是好詩。自古至今,這兩種爭論從無休止。直至近年來,中國詩歌界出現了所謂的“口水詩”、“白話詩”的命名和倡導,如趙麗華、烏青等詩人的力挺。應該說,無論是詩人還是評論家在一段時間內太過關注那些和詩歌毫無關聯的表象,太迷信一些所謂大師、所謂先鋒領軍人物所發出的驚世駭俗的言論。其實,真正好的詩歌從來不是因這些表象而得以傳承的,而是基于詩歌中所蘊含的詩人對所生活世界的一種發自內心的原創性價值。
在人類藝術的原初時代,詩歌是如何產生的呢?或許,追根索源會給我們更多的啟發。“斷竹,續竹,飛土,逐鹿”可以算得上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詩歌之一,到了春秋末年才出現了詩集《詩經》。那么,詩歌源自何處?它們并非完全由文人創作,更多的是源自于民間的歌謠;即所謂的“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是個人思想情感的外露,是人類社會初期對思想情感表達方式的原創。后人之所以將《詩經》視為“經”而不斷學習和模仿,成為中國文學的緣起,是因為這些詩歌體現了先民對中國文化和中國藝術的原創性努力。《詩經》中那些對愛情的贊美、對強權的控訴、對親情的向往等詩篇,開啟了中國文學傳統的大門。
后來的好詩歌同樣如此,以原創性價值為文學史所接納。北朝民歌《木蘭詩》為歷代人們喜愛,不是因為這首詩明白曉暢、朗朗上口,而是因為其蘊含了人們對超越男女差異而追求個體價值的精神;蘇軾的《題西林壁》短短四句,內涵了對同一事物從不同視角出發所看到結果的差異。到了今天,詩歌史上依然延續著這種對原創性價值的尊重。有的詩歌在形式表達上確實非常簡單明了,但是這種通俗易懂的背后隱藏著作家對所處時代生活的切入,體現了對社會和時代的獨特把握。例如北島的《生活》:“網”,以及顧城的《一代人》:“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
因此,僅僅是藝術形式上“明白易懂”不是決定詩歌好不好的標準。真正的標準是詩歌所體現的原創性價值,是對人生和世界的獨特的洞見。單單以藝術形式的難易作為衡量好詩的標準,實際上是對詩歌做了一種十分膚淺的理解。
二、反傳統的是不是好詩
“可以說,這樣的詩歌是對以往過度修辭、故作高深、拗口詰牙的詩歌方式的一種反撥,是對宏大敘事和假大空的主流話語體系的一種顛覆,是對一切所謂所指、能指、詩意、寓意以及強加給白云的陳詞濫調的比喻的徹底剔除。這樣用全新角度和方式寫白云、用稚拙原初的語言進行探索、讓詩歌回歸本源和本質的作品,我們如何不歡迎呢?”[1]趙麗華的言說本身看似沒有任何問題,顛覆傳統是很多詩人熱衷的話題和創作姿態。那么,這種言說的問題出在哪里呢?一個詩人在醉心于顛覆的時候,把建構
意識給弄丟了。“自由詩的無序和放縱,恰是對這種秩序焚之于燭后,那些歡快的火焰舞蹈的姿態。”[2]叛逆應該是在打破既有的詩歌格局的同時,從而探索其背后所擁有的更多可能。作為一種藝術樣式,叛逆和建構往往是異質同構的。沒有建構的叛逆是毫無意義的,叛逆的目的就是為了建構起一種新的藝術樣式。
我們不妨從藝術符號視角來看一下為趙麗華所稱道的《對白云的贊美》。所謂藝術符號,特別是藝術價值較高的,都是體現為存在性的符號。這種符號都是不可重復的,具有能夠返回存在潛能的作用。換句話說,就是藝術符號必須是創新性符號,對其更高的要求就是要具備原創性。那么,《對白云的贊美》中的藝術價值究竟體現為怎樣的藝術價值呢?擁有怎樣的創新性發現呢?“天上的白云真白啊”:如果是人類社會原初時期,有一個人突然發出這樣的感嘆,那就肯定具有原創意味,就像魯迅所講的“杭吁杭吁”派。但是任何意象一旦被后人不斷重復后,已經從審美質素轉化為文化構成。“很白,很白,非常白,特別白,賊白”,等等,這些話語就表述而言,并沒有體現出什么獨特意蘊,只不過是一種語義上的重復而已。寫白云是白的,是不是一種全新的角度?創新應該是有著自己獨特發現作為根基的語言實驗,語言游戲是不足以構成詩歌創新的。
百年來,現代性焦慮讓人們爭先恐后去嘗試源自西方的各種文學新理論新方法。故而,創新顛覆的思潮也是一浪高過一浪。人們往往是對一種思潮僅僅做了簡單的模仿,還沒有來得及創作出屬于自己的作品,還沒有真正內化為自己內在的東西,就快速將其趕下舞臺。以新為榮,以新為好,而不是以心靈之悟、以心之原創作為創作之本,導致了中國百年詩歌問題重重。詩人和詩
歌界不能將眼下的尷尬虛擬成為將來的繁榮,也不能將眼下讀者的批評視為“因循守舊、固步自封、如井底之蛙般見識淺薄的文學觀念”。[3]趙麗華和一些當下詩人的部分創作,不過是在自娛自樂罷了。他們一旦無法忍受寂寞,就拿出這些東西來,以詩人的姿態俯視廣大讀者,實在是毫無意義。
三、引起轟動的是不是好詩
在很多人眼中,趙麗華或烏青的詩歌出現在網絡上,純粹就是一種炒作行為。當各種攻擊和謾罵的帖子紛紛呈現于網絡,當各種批評的文章呈現于報端,事件已經遠遠超出了詩歌本身,而演化成為當下頗為流行的媒介事件。于是趙麗華奮起反擊,在博客中嚴重聲明:烏青是“躺著中槍的”。其實,趙麗華、烏青是否進行炒作對于當下的詩歌創作、對于整個文學發展,都沒有直接的影響。因為詩歌作為一門藝術有著自己的審美標準。
詩歌史、文學史的發展證明,那些在特定歷史時期曾引起巨大轟動效應的詩未必就是好的詩歌,而在某一時期不為人們所認可的詩歌未必不是好詩。非非主義、下半身寫作、女性寫作、第三條道路等,在當時出現之際大噪一時,但是很快就被分化、淹沒。在今天這個網絡時代里,詩人或對詩歌的某些炒作行為的確能夠吸引大眾的眼球,如詩人的驚人之語、詩歌的詭異形式、不同流派相互攻訐等。但這些現象本身只不過是一種網絡文化,或者說是一種文化現象,與能否創作出好詩沒有多大關系。在這樣一個時代里,趙麗華、烏青等詩人們有權利將自己書寫的文字拿到網上去發布,打工者也有權利將自己的業余創作拿到網上去展
示,甚至通過紙媒、座談會來傳達自己的聲音。但是這些都與詩歌本身的好不好沒有任何關系,那些滿懷情緒的讀者也大可不必為此當真。
詩歌是公認的在文學各文體中創作難度最大的一種。作為一名致力于漢語詩歌創作的詩人,或者業余愛好者,都應當致力于中國現代新詩藝術的建構,創作出更好的詩歌。好的詩歌應該是詩人對現實生活獨特體驗的產物,因此能夠拓展人生內涵,促進現代漢語的豐富性和藝術美,而不是僅僅為了創作的快意,或者在媒體上妄自菲薄,創造一些文化現象,達到吸引眼球的目的。
綜上所述,好的詩歌應該是詩人對現實生活獨特理解的產物,是詩人對人生的特有感悟通過現代漢語語言藝術的獨特建構來營造的藝術世界,應該讓詩歌回到文學本身。
注釋
[1][3] 參見趙麗華新浪博客,《烏青的白云是不是詩?》, http:// blog.sina.com.cn/s/blog_4aca2fbd0102e3xw.html?tj=1 。
[2] 葉延濱:《 中國當下詩歌十四題》,《西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