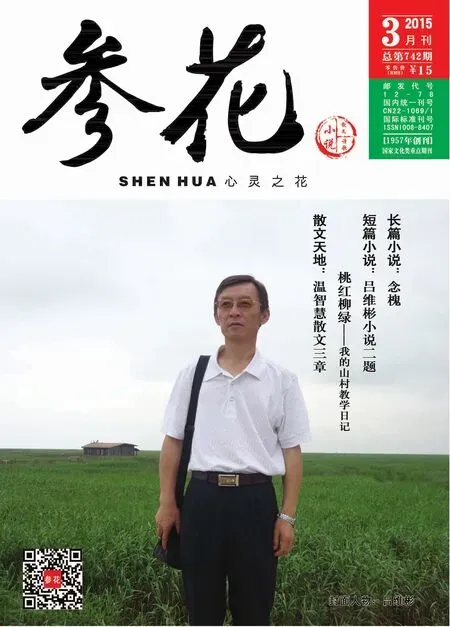蓬勃發展的云南抗日救亡歌詠運動
◎柏戰
蓬勃發展的云南抗日救亡歌詠運動
◎柏戰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的炮聲再一次地震憾了中國大地,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展開了全面的侵華戰爭,中華民族一時危在旦夕。隨著戰事的發展,中國東、中部地區很快淪陷,內地的眾多機關學校被迫紛紛陸續向西部、西南地區轉移。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地區成為了抗戰時期重要的后方基地。各種為抗戰服務的藝術形式在云南都異常活躍,如戲劇、音樂、電影等蓬勃發展。在當時的云南社會,民眾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為了喚醒民眾的抗戰意識,凝聚民心,就必須采取一種廣大群眾可以接受,容易理解,傳播迅速的藝術形式。而在這眾多的藝術形式之中,音樂恰恰符合這種需要。這就注定了音樂這種藝術形式在當時成為了敵后抗戰文藝活動中最為普遍,最為“時尚”的形式。縱觀云南的整個抗戰音樂文化,我們不難發現,具有群眾性質的歌詠運動,充斥了整個云南的抗戰音樂文化。這些群眾性質的救亡歌詠運動為推動云南的抗日救亡運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也成為了云南抗戰文化上的一大特色。
在抗戰初期(1937.8),云南昆華民眾教育館推廣部主任趙國徽(中共地下黨員)和李家鼎便組建了昆華民眾教育館民眾歌詠團。李家鼎同志任歌詠團的指揮。這可以算得上是抗戰以來云南昆明第一個組織規模較大的歌詠團體。其建立的宗旨也很明確“用救亡歌曲訓練和團結民眾,為爭取民族解放而奮勇抗戰”。民眾歌詠團的成員大多以老師、學生、工人為主,并且以歌詠團為中心,還組織發展了婦女歌詠團、兒童歌詠團等附屬之下的歌詠團體。為了深入地推廣民眾歌詠工作,昆華民眾教育館還多次舉辦歌詠干部訓練班,為其他團體組織的歌詠團提供相對專業的干部骨干。1939年初,在中共云南省工委書記馬子卿的直接領導下,以民眾歌詠團為中心,在李家鼎同志的帶領下,歌詠團每天至少有一、二百人去大唱抗戰歌曲,如《義勇軍進行曲》《黃河大合唱》等。在各中共黨支部(小組)的直接帶領下,各種群眾性質的歌詠活動有條不絮地進行著。通過歌詠進行抗戰宣傳普遍走向深入,這樣的局面一直堅持到1941年的“皖南事變”。
1939年暑期,云南省立昆華藝術師范學校戲劇電影科的第一屆同學畢業了,恰逢云南省教育廳鑒于戲劇歌詠教育的重要性,在廣大縣城、農村推行戲劇歌詠教育,隨即組織藝師的畢業生與民眾歌詠團下的“金馬劇社”,分別成立了云武瀘區戲劇樂歌巡教隊(劇教一隊)和楚姚大區戲劇樂歌巡教隊(劇教二隊)。兩個劇教隊奔赴三迤大地,組織大字不識的民眾高唱抗戰歌曲,他們為大山深處的民眾表演抗戰話劇,放映自制抗戰幻燈及抗戰電影,讓身處與世隔絕的紅土高原的民眾知曉祖國正處在生死存亡的時期,必須要全體中國人民的拼死一搏才能挽救危局,重整山河!1941年,兩隊因經費拮據,兩隊并為一隊。1945年5月再加調整,并與省立昆華教育館合作,在昆明民眾劇場公開演出。1946年以后巡教隊繼續在一些縣演唱,主要仍以演唱、教唱通俗進步歌曲。
提起抗戰時期的云南,就不得不提抗戰時期的“民主堡壘”——西南聯合大學。聯大在戰火中誕生,并存在了9年的時間。在聯大這塊“民主”的沃土上,聯大的同學、學者、愛國民主人士與云南社會各階層愛國民主力量相結合,使得聯大校園的文化抗戰活動迅速興起。聯大校園抗戰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當屬聯大校內的各種社團,其中音樂社團以其獨有的靈活方式在歷次抗戰愛國運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8年底,西南聯大成立了學生團體“群社”,這是西南聯大社團中成立較早,規模組織最大的,群社下設多個組織,其中的一個分支組織就是群聲歌詠隊,由徐樹仁擔任指揮,演唱各種抗戰歌曲。1940年,在群聲歌詠隊基礎上,聯大歌詠團成立,歌詠隊指揮還由徐樹仁同學指揮,經常演唱《五月的鮮花》等抗戰歌曲。1940年7月,聯大歌詠團應邀前往昆明廣播電臺播出抗戰歌曲。1940年8月31日,為給抗日將士募集寒衣,該歌詠團再次到昆明電臺演播。當晚,令人振奮的鋼琴聲響起。雄壯激昂的抗戰歌聲隨著電波傳遍云嶺高原、海外南洋。其中《黃河大合唱》是首次在云南演出。1941年3月、4月,該團再次到電臺演播。
抗戰時期云南抗日救亡歌詠運動,是云南抗戰音樂運動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云南抗戰文化運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共產黨和云南各界音樂人士的正確有力領導下,群眾性質的歌詠運動得以健康蓬勃的發展。在努力配合抗戰事業的同時也呼喚出了云南人民抗戰的熱情與積極性,為實現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責任編輯 劉月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