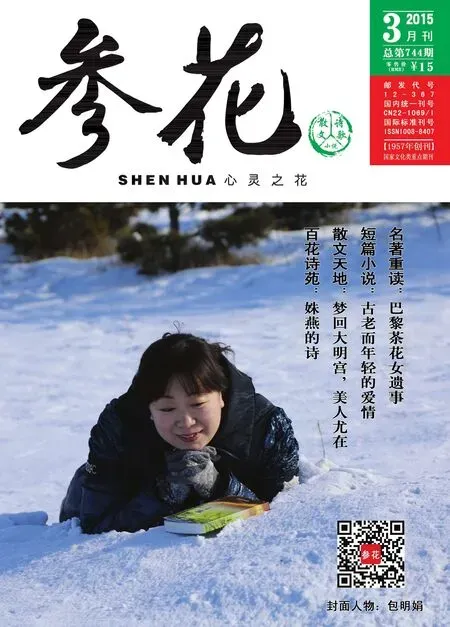媽媽,等我回家
◎錢立新
媽媽,等我回家
◎錢立新
寂寥荒蕪依然如舊,這個已接近沙漠的團場,我越走越近,都能看到母親的身影,還有妻女,在路口遙遙站著。我向他們跑去,可是發現身子卻是一直向后退,親人的身影也越來越模糊,越來越遠……
當我從夢中驚醒時,才發現我是睡在一個小板床上,一個小小的房間,窗外的月光就那么清涼的灑了進來。包圍著我的,是我的牢籠,我無法走出去的牢籠。此時此刻,思緒萬千,我再一次睡不著了。我從口袋摸出了煙,點燃,淡淡的火光,映著我無限悵然的臉。
我出生于杭州,一個溫暖的家庭,有疼愛我,呵護我的父母。那個物質并不豐富的時代,我度過了并無太多憂慮的童年。后來,隨著父母支援邊疆建設,到了新疆,一望無際的戈壁,在我眼里,是不變的顏色。人生最美的時光,莫過于無憂無慮的少年時代,面龐稚嫩,想法單純,朋友若干,打發時光。現在想來,一切都是難再來的過往。
每次置身夢境,孤獨、無措就會迎面襲來。人生之路就這樣,越走越窄,仿佛路的盡頭只有沉默的灰墻,我只能用視線與其對峙,可卻無法穿透。未來是什么?何去何從?
不知曾經的我,是不是因為,不清楚遠方有什么,才會選擇執意遠行?
窗外的月光是那么的涼,雖然是春天了,可是那月光還是那么的冷。
當法院宣判的那一刻,我知道很多東西都回不去了,包括我自己。這些年的時間讓我明白了很多,明白了人活一世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家庭,是親人,是那些平淡中最容易忽略的點點滴滴。
我曾無數次想著,年邁的母親在屋里佝僂著背慢慢往前走著的模樣,或是有時獨坐客廳默不作聲的落淚,每每此時,我總是無比悔恨無奈而心痛。
這些年的時光,烈日不憐憫我的悲傷,耀我致盲。我仿佛聽見命運的大門緩緩關上的吱嘎聲……我一度以為,真切的以為,人生的所有可能都已跌落無可挽回,我反復咀嚼著那些悔恨失落的味道,幾近一蹶不振,為這個錯誤賠上了后半生定會荒涼的時光。
直到后來,母親拖著瘦弱的身體來看我的時候,對我說:兒子,我等著你回家!
當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痛徹心扉的哭了,眼淚噴涌,卻沒有發出一絲聲音。媽媽,兒子這么的讓你失望,可你并沒有過多的指責,依然交待我在里面要好好改造,在家等著我回家。
母親離開后,我一個人枯坐房里,打開沉沉的包裹,里面是我喜歡吃的東西,熱乎乎的捂在包里,外加她精挑細選的水果,我由此越發明白什么叫可憐天下父母心。就這么默默坐著,直到天色暗了下來,月色輝映的夜里,頭頂著寂靜的星辰,前方的漫漫人生讓我有了一絲溫暖的依靠。在我的夢境中,一望無際的茫茫荒原上,開滿了紫色的花朵,落雨如塵,陰寒如秋。暗色調的天幕下,孤獨的鳥兒久久盤旋。我在狹小的空間里,向外眺望著,身邊坐著母親。
夢醒時分,我才明白,溫暖和點亮人生的,從來都是溶于血水的骨肉親情。
現在想來,人生往往是這樣,希望、堅持等富有支撐力的東西總是在臨界流產的艱難孕育中,好像稍不注意,一切支撐我走下去的幻想就將消失殆盡。
后來,我總在心里想著,如果母親不能在有生之年讓我再盡孝床頭,那我的余生如何能夠原諒自己?因此,我不知道除了早日與她團聚,還有什么能報答她的一片苦心。這也是我這么久以來無法擺脫自責和內疚的原因,我覺得我對不起她。她寄予我的,不過是這樣一個簡簡單單的期望,期望我能安然度過一生,希望我爭氣。為著這樣的一個簡單的愿望,她數年如一日地付出無微不至的關愛。歷經半載人生風雨,淺嘗過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維系何等脆弱,我才驚覺母親給與我的這種愛意,深情至不可說,無怨無悔,默默相伴。我不得不承認,唯有出自母愛的天性,才可以理解這一種無私。
兵團之夜,溫差頗大,我不再是將諸多讀本奉作命運的旨意。書里說,“生命中很多事情,沉重婉轉至不可說”,我相信,人生有此次酷烈的鍛煉才讓我成為了現在的我,讓我在現實中感受再造,即便是如此荒涼的站點,而正是它,最貼近人生。
已深的夜,風里送來了春天的氣息,我丟了煙頭,抬起頭看了看那依然冰涼的月光。心里有一句話在不停的說:媽媽,等著我回家!
(責任編輯 劉冬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