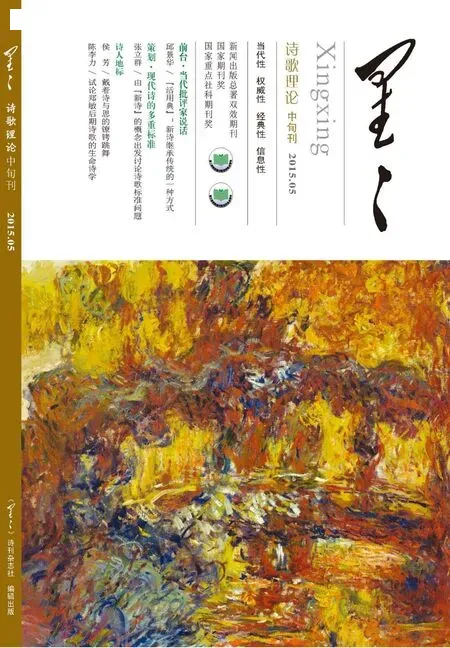我相信詩歌對人性的滋潤……
——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訪談錄之伊甸篇
詩人訪談
我相信詩歌對人性的滋潤……
——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訪談錄之伊甸篇
訪問者:姜紅偉
受訪人:伊 甸
姜紅偉:有人說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大學生詩歌的黃金時代,您認同這個觀點嗎?
伊 甸:20世紀80年代確實是中國大學生詩歌的黃金時代。1986年,當時我已從大學畢業,在一個浙江省作家協會組織的文學活動中,與杭州大學的在校大學生交流,記得當時杭大幾乎每個系都有詩社,每個班都有癡迷于詩歌的狂熱分子。整個80年代,中國所有大學里都有無數熱愛詩歌的學生。舒婷、北島、顧城1986年在四川跟大學生見面,被幾千個狂熱的大學生包圍著索取簽名,以至于舒婷恨恨地說:“這些大學生全是暴徒!”一批詩歌的狂熱暴徒啊!這一切在1989年戛然而止……90年代的中國大學生,以逃避虎狼般的速度逃離詩歌。此后,舒婷、北島、顧城們再無可能遇到大學生的狂熱包圍,代替他們的是一夜暴富的企業家和一夜竄紅的影視明星。
姜紅偉:請您簡要介紹一下您投身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的過程?
伊 甸:很慚愧,在某種意義上,我是“混進”大學生詩人隊伍的。我比當時“正宗”大學生詩人年長10歲左右。我是做了中學老師后再考入湖州師專(現湖州師范學院)中文系的。在進入湖州師專之前,我只發表過十幾首詩。1983年我進入湖州師專后,跟各地大學生詩人交流甚多,受到當時大學生詩風的影響,創作上口語化、生活化的現象特別明顯。1984年在邵燕祥老師、王燕生老師的支持下,6月號《詩刊》以《詩二組》的形式發表了我的十幾首寫工人生活的詩(文革中我在海寧化肥廠做過多年司爐工)。緊接著在《飛天》、《星星》、《青年文學》、《萌芽》、《青春》、《詩歌報》等全國各種報刊上發表詩歌。曾經獲得《飛天》大學生詩歌獎、《萌芽》文學獎、《綠風》詩歌獎以及各種詩賽的一二三等獎。當時自然是十分興奮的,但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些詩大部分都很表面化、概念化,是膚淺和幼稚的。
姜紅偉:在大學期間,您參加或者創辦過詩歌社團或文學社團嗎?擔任什么角色?參加或舉辦過哪些詩歌活動啊?
伊 甸:1984年,高校的氣氛比以前寬松了一些(此前由全國十三個最好的大學中文系、新聞系學生聯合創辦的文學雜志《這一代》被禁。大學生自發成立文學社和詩社往往被認為不合法),我的一位朋友,當年留校做了湖州師專團委書記的楊柳先生告訴我,上面支持學生組織文學社團了,于是我們馬上成立了
一個詩社,取名“遠方”。我擔任了第一任社長。蔣維揚、喬延鳳編的《詩歌報》、洋滔編的《拉薩河》曾發表過“遠方”詩社的詩歌專輯。整整三十前過去了,“遠方”詩社仍存在,今年5月在遠方詩社一直以來的指導老師沈澤宜先生(詩人、評論家,1957年在北大中文系被打成右派)的倡導下,由湖州師范學院出面舉辦了遠方詩社成立三十周年的紀念活動。
姜紅偉:您參與創辦過詩歌刊物嗎?
伊 甸:“遠方”詩社剛創辦時,我們每學期編印一本油印的《遠方詩刊》,主編沈健(現在是湖州職業技術學院教授、詩歌評論家)。第一、二、三期《遠方詩刊》油印本我至今仍珍藏著。幾年前,在沈澤宜老師一些熱愛詩歌的弟子的資助下,出版了新的《遠方詩刊》,最近出了第四期。第一、二期由我和鄒漢明任責任編輯,第三、四期由我一個人任責任編輯。現在的《遠方詩刊》是一本面向全國詩壇的民間詩刊。
姜紅偉:上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人們最熱衷的一件事是詩歌大串聯,您去過哪些高校?和哪些高校的大學生詩人來往比較密切最后成為好兄弟啊?
伊 甸:當年囊中羞澀,很少出去串聯。只有一次,劉波在湖南株州要舉辦一個全國青年文學社團聯絡會議,1985年四月底,我和柯平來到株洲,才知道這個會議已在團中央的干涉下被取消。據劉波說,他已經向所有被邀請的人發去會議停辦的通知。但一些人沒收到這個通知,仍然趕到了株洲,除了我和柯平外,還有廖亦武、潘洗塵、馮晏等。意想不到的是,這一場年輕
詩友的自由聚會,比正兒八經的會議更讓人難忘。
潘洗塵是我第一個見到的外地大學生詩友,這幾年聯系不少,他編的雜志好幾次發表了我的作品,他編的EMS周刊出了一本《伊甸新作快遞·陽光總是走得很慢》。很感謝他的熱情。但株洲見面以后,29年未曾見過面,去年夏天我在大理也沒找到他的人影,今年夏天我還去大理避暑,他的讀詩吧可能會是我常去的地方。1987年我在北京魯迅文學院見到了蘇歷銘和華海慶,匆匆相見,未及深談。這幾年通過微博、微信和蘇歷銘聯系較多,常有共鳴之處,他的文章《安靜寫作——一個詩人不應喪失的優秀品質》我十分喜歡,他說:“詩人是人群中特殊的群體,他們應該具有特有的批判精神和悲憫情懷”,說出了我最想說的話。程寶林也27年不見了,1987年10月,我旅行結婚去成都,程寶林把他宿舍里一米寬的小床讓給我們住,留下了永遠難忘的深刻印象。此后二十年——彼此相忘于江湖,一直到幾年前在博客上重新有了聯系。從他的文章來看,他一如大學時代那么純粹、正直、悲憫、嫉惡如仇。最有戲劇性的見面是和許德民的相見。1986年夏天,我和沈健去新疆,居然在天山山脈的尼勒克縣意外地撞見了許德民夫婦。當時,許德民剛從馬上摔下來,身上有好幾處傷。后來我們四人結伴去天山深處。天山出來告別之后,也是20多年相忘于江湖,這幾年才有了聯系。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近幾年參加詩會,動不動我就會喊出:哎呀,我們30年不見了吧!唉,我們二十多年不見了吧!
姜紅偉:當年的大學生詩人們最喜歡書信往來,形成一種很深的“信關系”,您和哪些詩人書信比較頻繁啊?
伊 甸:當年和我通過信的大學生詩友有:蘇歷銘、潘洗塵、程寶林、朱凌波、華海慶、楊川慶、包臨軒、楊榴紅、呂貴品、燕曉冬、尚仲敏、許德民、卓松盛、張小波、陳鳴華、傅亮、沈國清、張洪海、黃燦然……他們分別來自人民大學、吉林大學、黑龍江大學、哈爾濱師范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大、湘潭大學、南京師大、暨南大學等全國各地的大學。當年通過信的大學生詩友起碼有50位以上,這些詩友中我只見過一小部分,但即使很多詩友從未見過面,80年代的通信讓我們彼此有了了解,有了友情,一見面就會像碰到熟悉的老朋友那樣親切。
80年代的所有信件我全都保存著,如果哪位詩友懷舊時想看看自己當年的筆跡,我可以復印了寄過來。如果哪位詩友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有了他的紀念館,我愿意把他寫給我的信全部捐獻出來。
姜紅偉:在您印象中,您認為當年影響比較大、成就比較突出的大學生詩人有哪些?哪些詩人的詩歌給您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
伊 甸:實際上,現在詩壇上影響最大的詩人,除以北島為代表的今天派詩人之外,大多是80年代的大學生詩人,只不過有的是80年代初期和中期畢業的,有的是80年代末畢業的。80年代是一個風云變幻的時代,80年代畢業的大學生和90年代以及本世紀畢業的大學生在理想、責任感、憂患意識、人生境界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80年代的大學生詩人是王家新。當年我從一本好不容易借到的《這一代》上看到了王家新的一首詩,盡管沒抄下來,但記憶非常深刻。這首詩寫鳥兒可以從
某座橋上飛過,但普通人卻不可以從那座橋上走過。王家新寫這首詩的時候,還是武漢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他的詩里所呈現的批判意識和懷疑精神,即使放到三十多年以后也還是非常寶貴的。還有呂貴品的詩,雖然也有著口語化、生活化的大學生詩歌的痕跡,但他的詩是深沉的,他通過對一些細節的描述呈現出思想的力量。但呂貴呂的這些詩歌,很可能是大學畢業以后寫出來的。
姜紅偉:當年,大學生詩人們喜歡交換各種學生詩歌刊物、詩歌報紙、油印詩集,對此,您還有印象嗎?
伊 甸:印象較深的有華東師大的《夏雨島》,復旦大學的《詩耕地》、燕曉冬、尚仲敏的《大學生詩報》。應該還有湘潭大學的《旋梯詩刊》,吉林大學的《北極星》、黃燦然的《紅土詩抄》、浙師大的《黃金時代》等等,等等,可惜我記性太差,大多不記得了。當年大學畢業時把那些沒有任何價值的教材、一些隨時可以買到的書搬了回來,卻沒把這些越來越顯得珍貴的大學生詩歌報刊搬回來,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我實在太愚蠢。
姜紅偉:在20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詩友中,聽說您和程寶林交往比較密切,能說說和他的一些故事嗎?
伊 甸:1983年到1985年,我在浙江湖州師專中文系讀書,擔任學校“遠方”詩社社長,與全國許多大學生詩人有過頻繁的聯系,比如許德民、傅亮、卓松盛、黃燦然、蘇歷銘、潘洗塵、包臨軒、朱凌波、呂貴品、楊川慶、楊榴紅、尚仲敏等等,其中還有北京人民大學紅葉詩社社長程寶林。1984年年底,我收到紅葉詩社寄來的一封為程寶林出版詩集籌款的信:
伊甸及浙江詩友們:很冒昧,但為了詩,為了一種愿望,我們不得不這樣冒昧。本來,我們只打算將程寶林的詩集《雨季來臨》印刷少許分贈詩友們。但謝冕老師卻鼓勵我們,為這本詩集寫序,外地的一些詩友建議我們增加印數。我們何嘗不這樣想呢?僅靠程寶林賣掉錄音機和漂亮的皮夾克,僅靠紅葉詩社顯然不夠,于是,我們決定向詩友們借款集資,使這本詩集得以順利出版,待詩集銷售后,立即奉還……
信末的署名是“北京紅葉詩社”。落款日期為1984年12月1日。
我當即寄了錢去,寄多少錢現在已想不起來,后來程寶林賣掉了他的詩集,就把錢寄了回來。
我的書架上至今還并排站立著兩本《雨季來臨》,扉頁下方分別寫著:“送給詩兄伊甸——寶林于1985年3月29日”,“送給老伊和他的女友甸小姐——寶林85年4月23日于人民大學”。詩集由謝冕作序,后面還有李小雨的評論。
那幾年里,我和寶林大約有十幾次在同一期刊物同一個欄目發表詩作,彼此都很熟悉對方的作品。雖然都一樣地口語化一樣地快節奏一樣地充滿激情充滿幻想,但今天回過頭來看,寶林的詩更清新更有情趣,而我當年的詩則明顯地暴露出一種膚淺的樂觀主義。
1985年夏天,寶林從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他本來被分配在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能夠留在首都工作,是很多大學畢業生夢寐以求的事。但寶林當時愛上了一位川妹子,為了愛情,他放棄了這個留在北京的機會,不遠萬里奔赴成都,在《四川日報》做了一名編輯。1987年,我和妻子到九寨溝旅行結婚經過成
都,第一次見到了寶林和他又美麗又溫柔的女朋友。
當年的寶林清瘦、樸素,雖然已工作兩年,仍然是一副大學生模樣,正如李小雨文章中對他的描繪:“黑瘦而單薄,眼睛遮不住一臉的孩子氣,口中訥訥的,似乎話不多,但似乎又有許多話要講,因為拘謹,而終于沒有講成……”我和寶林的性格比較相似,我們都出身底層,都有一種從底層社會帶來的拘謹、木訥和敦厚。但由于彼此一見如故,雙方的女伴又都是一樣的善良和謙卑,所以我們的相處和交談非常愉快。他和我講了他對女友的深深的愛,他在報社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比如報社對他請假參加青春詩會一事的阻撓),他對湖北老家親人的牽掛等等,我們像老朋友一樣互相信任,無話不談。他把報社給他的那間單人宿舍讓給我們住,又帶我們去見了龍郁、孫建軍等一些詩友。
然后,然后……二十二年天各一方,再無見面機會。這幾年在報刊和網絡上陸陸續續讀到他的一些散文,發現寶林還是當年那個率真、耿直、胸懷坦蕩、見義勇為的寶林,當然更成熟,更有力量。他寫故鄉和親人的那些散文,字里行間有一種悲憫和反思的沉重,比如他的《歸國紀事——歸葬》,雖然寫的是他親身經歷的事,實際上是對苦難的中國農村社會的深刻解剖,讀后讓我感慨良久。另外,他在自己的博客上直言不諱地譴責某些缺乏良知的御用學者,體現了他思想的敏銳和信念的堅定——這是我特別贊賞和敬重的地方。
但愿有一天,能與寶林在世界的某個角落突然相遇,我相信我們一定會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覺。在我認識的詩友中,寶林是讓我感覺到可以徹夜長談的寥寥無幾的幾個人中的一個。
姜紅偉:在您寫詩的過程中,聽說甘肅的《飛天》文學月刊給予您很大幫助,能具體談談您和《飛天》的淵源嗎?
伊 甸:八十年代,甘肅的文學雜志《飛天》開辟一個專門發表大學生詩歌的欄目“大學生詩苑”,這是《飛天》雜志的一個招牌欄目。這個欄目為全國大學生詩人所熱愛,凡是有點影響的大學生詩人,當時都在“大學生詩苑”上發過詩,很多人發的是處女作。“大學生詩苑”在他們成為詩人的道路上所起到的作用十分巨大。
“大學生詩苑”的編輯是張書紳老師。可想而知:在八十年代幾乎所有的大學生都愛上詩歌的年代里,做“大學生詩苑”的編輯是何等地繁忙。張書紳老師每天要面對從全國四面八方雪片般飛來的詩稿。那時還沒有打印的稿件,所有詩稿都是抄寫的,許多作者的字很潦草,張老師得花多大的耐心去讀這些稿件。他還得給作者寫信,提修改意見,有的詩可以發表,但有瑕疵,張老師得絞盡腦汁地幫作者修改。
1984年1月和7月的《飛天·大學生詩苑》中,張老師各發表了我一組詩,給了我極大的鼓勵,至今想起來都是一件非常快樂和幸福的事。1986年,我和詩友沈健去西藏新疆時路過蘭州,我們特地去拜訪了張書紳老師。7月14 日上午,我們找到了《飛天》編輯部,正好張老師和《飛天》的另一位詩歌編輯李老鄉都在,李老鄉也是我們非常喜歡的詩人。兩位老師都非常親切、溫和,把我們當作小弟弟一樣關照。聊了一會后,兩位老師請我們到飯館里吃蘭州特產——牛肉拉面。那時,我們很不懂事,作為作者,只有內心深處對編輯老師的感恩,卻不懂人情世故,沒從家鄉帶點土特產給老師,也不懂由我們出面請客……現在想起來
感到十分愧疚。
那天,我們和兩位老師還有蘭州的女詩人李述合了影,用的是我相機中的彩色膠卷,當時彩色膠卷剛剛開始使用,十幾元一卷的價格,是當時我月工資的四分之一,因此一路上我只用這個膠卷拍我認為最重要的照片。一直到十天后到達德令哈時,我才用了膠卷的一半,其中最重要的照片就是和張書紳李老鄉兩位老師以及李述的合影,以及在西寧和昌耀的合影等。結果在德令哈遇到了一個利用暑假出來作音樂演出的團隊,其中一個陜西音樂學院姓萬的人跟我們借剩下的半卷膠卷,我們“豪爽”地借給了他,再三叮嚀要他沖好膠卷后掛號寄嘉興市文聯,誰知我從大西北回來后等了好久不見寄來,寫了兩封信去催,又托西安的朋友專門去找陜西音樂學院找到他索要膠卷,他居然說早就寄給我了,當時我真恨不得專程跑到西安去狠狠揍他一頓。沒留下和張書紳李老鄉兩位老師以及和昌耀的合影,這件事成為我永久的遺憾。
27年不見張書紳老師了,心里常常惦記著他,我從內心深處至誠地祝愿他平安、健康、長壽。張老師的“大學生詩苑”培養了整整一代大學生詩人,那些大學生詩人現在都人到中年,很多還活躍在詩壇上,我想他們都會記得這個讓他們永遠感到親切的名字——張書紳。
姜紅偉:您如何看待上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的意義和價值?
伊 甸:80年代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時代,大學生詩歌運動正是跟整個社會的理想主義密切呼應的。它的激情、它的純粹、它
的天真——都是非常珍貴的,但是它就像一個美麗卻脆弱的瓷器,在八十年代末嚴峻的現實面前砰的一下碎掉了。九十年代,大學生的整體精神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實主義、功利主義成為大學生中占主導地位的精神狀態和生活方式。要讓大學生重新回到80年代那種激情、純粹、天真的狀態,看來是不可能了。它成為我們這一代人懷舊的風景。但它仍是有意義的,它的意義就是:80年代的大學生詩人現在雖然已進入中年甚至老年,但他們的靈魂深處,那種理想主義的東西、那種詩意的東西仍在發出光芒,使他們多多少少避開了勢利、狡獪、邪惡。雖然不能一概而論,人是這個世界上最復雜的東西,這個時代,純粹和天真越來越成為稀罕之物,勢利和狡獪越來越大行其道,80年代的大學生詩人也難免有一些人漸漸學會了見風使舵,學會了唯利是圖,學會了爾虞我詐,但這肯定是少數,這樣的人當初對詩歌的熱愛不會是出自內心的,不會是一種別無選擇的生命需要。總體上,我相信詩歌對人性的滋潤,我相信詩歌對熱愛它的人帶來的對邪惡和虛偽的免疫力。
姜紅偉:回顧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您最大的收獲是什么?最美好的回憶是什么?
伊 甸: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讓我發現,中國有那么多熱愛詩歌的人,有那么多純粹和天真的人,有那么多靈魂在發出光芒的人。即使在對現實和未來感到絕望和沮喪時,我還是能透過大片霧霾和黑暗看到這些光芒。我最大的收獲是,當我沉浸在詩歌中、當我沉浸在和詩友們的靈魂交流中,我對世界之美,對人性之美就有了信心。我感到了生命中詩性的存在——那是活著的
唯一意義。我最美好的回憶就是那些詩歌,那些像詩歌一樣的信,那些像詩歌一樣的靈魂。
姜紅偉:投身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您的得失是什么?有什么感想嗎?
伊 甸:投身于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對我來說是有利有弊的。因為大學生詩歌運動的鼓動和激勵,我更熱烈地投身于詩歌寫作,更堅定了自己對于詩歌的信念;但這場大學生詩歌運動像潮水一樣裹著我向前的時候,我來不及抖掉自己身上的泥沙。我在詩藝和精神上的準備不足,因為發表量太大而帶來的虛榮和幻覺,暴露了我的粗糙、淺薄和單調。我必須警告自己:當你被一種潮流裹挾向前的時候,你要設法脫身而出,讓自己保持獨立、清醒、自省。寫作永遠是一個人的事情,它跟任何運動無關。寫作是一種永恒的自我訓練,它與名聲無關,與榮譽無關。雖然榮譽看起來是一頂非常美麗的帽子,但它畢竟是一頂帽子,它不是詩歌本身,也不是生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