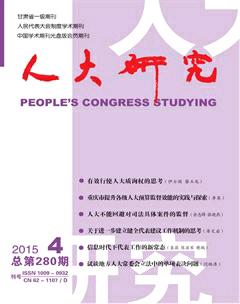有效行使人大質(zhì)詢權(quán)的思考
伊士國++蔡玉龍
人大質(zhì)詢權(quán)作為人大監(jiān)督權(quán)的重要內(nèi)容和表現(xiàn)形式,具有重要的價值和作用。但是由于各種原因,人大質(zhì)詢權(quán)長期處于“休眠”狀態(tài),致使人大監(jiān)督的功效尚未完全發(fā)揮。因而,我們應(yīng)采取有效措施,“激活”人大質(zhì)詢權(quán),保證人大質(zhì)詢權(quán)的有效行使。
一、人大質(zhì)詢權(quán)行使現(xiàn)狀及其原因分析
季衛(wèi)東教授曾指出:“歷史的經(jīng)驗已經(jīng)反復(fù)地證明,理論上很完美的制度并不一定可以付諸實施,而行之有效的制度卻未必是事先設(shè)計好的。”[1]我國人大質(zhì)詢權(quán)正是陷入了這樣一種“名歸而實不至”的尷尬境地。雖然我國憲法和法律明確規(guī)定了人大質(zhì)詢制度,明確賦予了人大及其常委會質(zhì)詢權(quán),且越來越規(guī)范化、程序化,然而,與此不相適應(yīng)的是,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質(zhì)詢權(quán)的次數(shù)卻越來越少。據(jù)有關(guān)媒體統(tǒng)計,近 30 年來有不少于 80%的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從沒有行使過一次質(zhì)詢權(quán)。如果說我們過去還能列舉幾個經(jīng)典的質(zhì)詢案例的話,如“1989 年 5 月,在湖南省七屆人大二次會議上,代表們就中央要求清理整頓公司提出質(zhì)詢案,最后以副省長楊匯泉被罷免而告終;2000 年 1 月,廣東省九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代表們提起質(zhì)詢案,導(dǎo)致省環(huán)保局局長易人;2009 年,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對省政府部分直屬機(jī)構(gòu)違法收費(fèi)和挪用財政資金行為提出質(zhì)詢案……”。那么,近幾年來,無論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還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都很少行使質(zhì)詢權(quán),質(zhì)詢案例自然鮮有談起。2010年,吳邦國委員長在其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依法開展專題詢問和質(zhì)詢”,曾燃起了人們無數(shù)希望。然而,由于缺乏相應(yīng)的跟進(jìn)措施,到目前為止,人大質(zhì)詢權(quán)行使的次數(shù)依然非常少。對于這種情況,學(xué)者們將其稱為質(zhì)詢權(quán)的“閑置”“虛置”“休眠”等。正如曹眾教授指出:“‘質(zhì)詢被寫入憲法和法律文本已經(jīng)有30余年的歷史。如果把1954年憲法第三十六條規(guī)定的‘質(zhì)問也算在內(nèi),那么這項權(quán)力在中國的憲法和法律中已存在50多年的歷史。當(dāng)前,又距離2010年委員長的‘提起兩年多過去了,像詢問那般,中央層面本應(yīng)起到示范效應(yīng)的質(zhì)詢案,至今卻悄無聲息。質(zhì)詢權(quán)依舊休眠……”[2]那么,是什么原因?qū)е氯舜筚|(zhì)詢權(quán)出現(xiàn)了上述狀況呢?是不是“一府兩院”的工作中沒有什么值得質(zhì)詢的問題呢?顯然不是。正如王鴻任代表指出:“質(zhì)詢權(quán)的長期閑置,并不是各地‘一府兩院的工作中沒有值得質(zhì)詢的問題,而是規(guī)避剛性監(jiān)督措施的惰性。”[3]
筆者認(rèn)為,人大質(zhì)詢權(quán)被“虛置”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認(rèn)識上的誤區(qū)。由于質(zhì)詢是人大通過一定的法律程序,強(qiáng)制被監(jiān)督對象回答代表或委員提出的問題,且代表或委員可以根據(jù)回答的情況采取必要的措施,因而,質(zhì)詢權(quán)具有較強(qiáng)的“剛性”,與詢問、審議、視察、檢查等監(jiān)督方式相比,“問責(zé)性”更濃一些。因而,許多對人大質(zhì)詢權(quán)不了解的人,特別是“一府兩院”的領(lǐng)導(dǎo)人員,誤認(rèn)為人大從事質(zhì)詢工作,就是給自己“唱對臺戲”,就是給自己找“麻煩”,甚至就是“沒事找事”“無事生非”。一些官員還誤認(rèn)為,一旦被人大質(zhì)詢,就要被罷官,即使不罷官,也會影響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一府兩院”一般不愿積極主動地配合人大的質(zhì)詢工作。而從事人大工作的同志,基于上述理由,也怕得罪人,也不敢積極主動地行使人大質(zhì)詢權(quán)。第二,法律機(jī)制不健全。雖然我國憲法和法律已經(jīng)建立了比較完善的人大質(zhì)詢制度,但該制度仍然存有不少缺陷,特別是規(guī)定比較原則、抽象,缺乏具體的程序性規(guī)定,如人大質(zhì)詢會如何組織、如何開展、如何處理等都無具體的細(xì)則規(guī)定,這樣使得人大開展質(zhì)詢工作往往于法無據(jù),無從下手,實踐中操作難度也比較大。第三,實施門檻高。考慮到人大質(zhì)詢具有較強(qiáng)的問責(zé)意味,因而,我國法律規(guī)定了較高的實施門檻。這雖然有一定的合理之處,有利于避免質(zhì)詢權(quán)的濫用,但實施門檻偏高,也會阻礙人大質(zhì)詢權(quán)的正常行使。如根據(jù)我國法律規(guī)定,只有一定數(shù)量的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書面聯(lián)名,才有權(quán)提出質(zhì)詢案。這就無形中增加了人大質(zhì)詢權(quán)行使的難度,因為如果某一質(zhì)詢案得不到法定人數(shù)的贊同,就根本無法提出。又如根據(jù)我國法律規(guī)定,各級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只能在各級人大會議或人大常委會會議期間提出質(zhì)詢案,其他時間則無權(quán)提出。因為各級人大會議一般每年才舉行一次會議,各級人大常委會一般兩個月舉行一次會議,且各級人大會議或人大常委會會議議程本來就非常多,這就導(dǎo)致人大質(zhì)詢工作無法經(jīng)常性開展,難以做到常態(tài)化,等等。
二、“激活”人大質(zhì)詢權(quán)的對策
“嚴(yán)密監(jiān)督政府的每項工作,并對所見到的一切進(jìn)行議論,乃是代議機(jī)構(gòu)的天職。”[4]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強(qiáng)調(diào),要加強(qiáng)人大監(jiān)督,要“健全‘一府兩院由人大產(chǎn)生、對人大負(fù)責(zé)、受人大監(jiān)督制度”。要“通過詢問、質(zhì)詢、特定問題調(diào)查、備案審查等積極回應(yīng)社會關(guān)切”[5]。因而,我們必須要采取措施,“激活”人大質(zhì)詢權(quán),以增強(qiáng)人大監(jiān)督實效。具體說來:
第一,提高對人大質(zhì)詢權(quán)的認(rèn)識。要排除妨礙人大質(zhì)詢權(quán)行使的錯誤認(rèn)識,就必須對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lǐng)導(dǎo)干部進(jìn)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知識的教育和培訓(xùn)。要使他們充分認(rèn)識到人大質(zhì)詢權(quán)是憲法賦予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重要職權(quán)之一,妨礙人大質(zhì)詢權(quán)的落實,將會損害我國人大的地位和權(quán)威;要使他們充分認(rèn)識到人大質(zhì)詢權(quán)是人民當(dāng)家作主權(quán)利的重要體現(xiàn),妨礙人大質(zhì)詢權(quán)的落實,就會妨礙人民當(dāng)家作主權(quán)利的實現(xiàn);要使他們充分認(rèn)識到人大質(zhì)詢權(quán)是加強(qiáng)權(quán)力監(jiān)督和制約的必然要求,妨礙人大質(zhì)詢權(quán)的落實,就會導(dǎo)致權(quán)力的濫用和腐敗。可見,人大質(zhì)詢權(quán)的行使,決不是給某些機(jī)關(guān)或人員“唱對臺戲”“沒事找事”“找麻煩”,而是人大制度和人民當(dāng)家作主的必然要求。當(dāng)然,也要提高人大代表或委員對人大質(zhì)詢權(quán)的認(rèn)識,并要加強(qiáng)對他們的專業(yè)知識培訓(xùn),使他們不僅要敢于質(zhì)詢,還要善于質(zhì)詢,提高人大質(zhì)詢工作的質(zhì)量和水平。
第二,實現(xiàn)憲法和法律的有效銜接。雖然我國憲法和法律都規(guī)定了人大質(zhì)詢權(quán),但是兩者的規(guī)定卻存在一些矛盾之處,最突出的就是我國憲法沒有賦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質(zhì)詢權(quán),也沒有賦予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質(zhì)詢“兩院”的權(quán)力。如我國憲法第七十三條規(guī)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期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組成人員在常務(wù)委員會開會期間,有權(quán)依照法律規(guī)定的程序提出對國務(wù)院或者國務(wù)院各部、各委員會的質(zhì)詢案。受質(zhì)詢的機(jī)關(guān)必須負(fù)責(zé)答復(fù)。”而我國的監(jiān)督法、地方組織法等卻規(guī)定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質(zhì)詢權(quán)。這樣,就使得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質(zhì)詢權(quán),以及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質(zhì)詢“兩院”都缺乏憲法依據(jù),都存在“違憲”的嫌疑。因而,我們應(yīng)對憲法的有關(guān)規(guī)定進(jìn)行修改,以實現(xiàn)憲法和法律的有效銜接,為人大質(zhì)詢權(quán)的行使提供憲法保障。具體言之,可以將憲法第七十三條修改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組成人員有權(quán)提出對國務(wù)院或者國務(wù)院各部、各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質(zhì)詢案,具體程序由法律規(guī)定。”此外,可以在憲法第三章第五節(jié)中增加關(guān)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質(zhì)詢權(quán)的規(guī)定,即“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及其常委會組成人員有權(quán)提出對同級人民政府及其所屬工作部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質(zhì)詢案,質(zhì)詢案的具體程序由法律規(guī)定”。
第三,進(jìn)一步完善人大質(zhì)詢制度。雖然我國質(zhì)詢制度不斷發(fā)展,但仍然存有不少問題,有待進(jìn)一步完善。具體言之,一是關(guān)于質(zhì)詢主體。我國法律規(guī)定只有一定數(shù)量的人大代表或委員聯(lián)名才能提出質(zhì)詢案,這無形中增加了質(zhì)詢權(quán)行使的難度。可以考慮修改相關(guān)法律,降低數(shù)量上的要求,以方便人大代表或委員提出質(zhì)詢案。二是關(guān)于質(zhì)詢對象。目前我國法律規(guī)定的質(zhì)詢對象范圍仍然有點(diǎn)窄,不夠全面,可以考慮將其擴(kuò)大。“質(zhì)詢對象除同級人民政府及其所屬工作部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外,在人代會期間,還應(yīng)增加同級人大常委會及‘一府兩院領(lǐng)導(dǎo)人,以實現(xiàn)對國家權(quán)力運(yùn)行的全方位監(jiān)督。同時明確規(guī)定司法質(zhì)詢的對象是‘作出生效行政行為的人民政府及其所屬工作部門,作出生效判決、裁定、調(diào)解書、決定書等終局法律文書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6]三是關(guān)于質(zhì)詢時間。由于各級人大及常委會會議次數(shù)少、時間短、議程多,因而,如果只在會議期間才允許人大代表或委員進(jìn)行質(zhì)詢的話,顯然難以保證質(zhì)詢的效果,也達(dá)不到人大質(zhì)詢的目的。因此,可以考慮地方組織法的相關(guān)條文,規(guī)定人大代表或委員在閉會期間也可以行使質(zhì)詢的權(quán)利,以做到人大質(zhì)詢工作的經(jīng)常化。四是關(guān)于質(zhì)詢程序。目前人大質(zhì)詢工作尚缺乏一套具體細(xì)致的程序規(guī)定,使得人大質(zhì)詢權(quán)的行使缺乏程序保障。因此,應(yīng)通過立法增加有關(guān)人大質(zhì)詢程序的內(nèi)容,包括質(zhì)詢案的提交、質(zhì)詢案的審議、質(zhì)詢?nèi)说奶釂枴⒈毁|(zhì)詢?nèi)说拇饛?fù)、質(zhì)詢的后果等。特別是應(yīng)明確規(guī)定質(zhì)詢不滿意的法律后果,否則,人大質(zhì)詢權(quán)就會形同虛設(shè)。可以考慮規(guī)定,如果“代表或委員對質(zhì)詢不滿意時,可以要求代表大會主席團(tuán)或常委會將被質(zhì)詢問題提交代表大會或常委會全體會議討論。若質(zhì)詢案根據(jù)一定程序被提交大會或常委會會議討論后,下一步的結(jié)果可以是:或表示滿意通過;或需進(jìn)一步組織特定調(diào)查;或提出罷免、撤職案等,都由會議來決定”[7]。
注釋:
[1]季衛(wèi)東:《法律程序的意義》,載《法治秩序的構(gòu)建》,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頁。
[2]曹眾:《設(shè)計對實施的向往——對詢問權(quán)、質(zhì)詢權(quán)的審視與反思》,載《法治與社會》2012年第7期。
[3]王鴻任:《從代表角度談質(zhì)詢權(quán)的閑置》,載《人民代表報》2012年3月24日。
[4]【美】威爾遜著:《國會政體》,熊希齡、呂德本譯,商務(wù)印書館1986年版,第167頁。
[5]《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http://www.sn.xinhuanet.com/2013-11/16/c_118166672. ht
m,2014-6-20.
[6]柯蘭:《激活地方人大質(zhì)詢權(quán)需要頂層設(shè)計》,載《檢察日報》2013年9月9日。
[7]蔡定劍著:《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91頁。
(作者分別系河北大學(xué)人大制度與地方立法研究中心秘書長、副教授,河北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