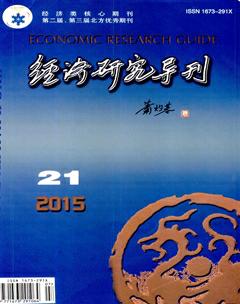對公共產(chǎn)品供給問題的經(jīng)典解讀——以我國和英國的燈塔為例
楊 昭
(西藏大學(xué)財經(jīng)學(xué)院,拉薩 850000)
自從薩繆爾森在其《經(jīng)濟學(xué)》(第6版)教科書中首創(chuàng)“公共產(chǎn)品”(public goods)的概念,并對其性質(zhì)進行闡述后,公共產(chǎn)品理論逐漸成為現(xiàn)代財政體系的核心。但是,公共產(chǎn)品該如何更有效地被生產(chǎn),或者進一步說,在公共產(chǎn)品的提供中政府和市場該如何確定各自的邊界和責(zé)任,仍然是現(xiàn)代公共產(chǎn)品理論的熱點和難點。燈塔作為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產(chǎn)品,成為了人們論證公共產(chǎn)品供給理論的典型物品。
一、我國與英國燈塔提供的歷史演變
1.我國的燈塔
晚清之前,我國的燈塔發(fā)展建設(shè)較為緩慢。早期的燈塔多為私人籌集,甚至由一些僧侶進行籌劃,還有少數(shù)燈塔是與地方官府合資建造。我國最早的燈塔市位于福建的崇武燈塔,該塔實在明代洪武年間(1387)年由當(dāng)?shù)貪O民集資建設(shè)的。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的燈塔事業(yè)蒸蒸日上,燈塔建設(shè)有了跨越式發(fā)展。首先是一批有識之士認識到燈塔的重要性,自發(fā)組織建設(shè),從1848—1968年的二十年間,以民間為主,先后修建了數(shù)十座燈塔,其中最著名的西鶴嘴燈塔,則由邑人金品山以一己之力建造。1868年后,中國的燈塔由海關(guān)統(tǒng)一管理,但也有國人自行建造的燈塔出現(xiàn),但終因經(jīng)費不足,由官府接管。自此,中國的燈塔實現(xiàn)了從民間自發(fā)籌建到政府統(tǒng)一規(guī)劃建設(shè)管理的演變。
2.英國的燈塔
在燈塔的提供機制沒有被法定之前,英國的燈塔主要是由私人提供的。17世紀(jì)之前,燈塔在英國是默默無聞的。17世紀(jì)初,管理航海事宜的領(lǐng)港公會建造了兩座燈塔,私人也在建造,并且數(shù)量更多,效率更高。1610—1675年間,私人至少建設(shè)了10座燈塔,而領(lǐng)港公會并未建設(shè),此時私人主要是通過向國王申請獲得籌建權(quán)利,并通過向過往船只收費維持運營。之后,領(lǐng)港公會申請到專利權(quán),并向愿意籌建燈塔的私人出租,私人獲得承租權(quán)并建造燈塔,并向港口的所有者收取費用。之后,英國政府認為私人收費太高而逐漸收回?zé)羲搅?820年,英國私營燈塔只剩22個,而政府所有的,即由領(lǐng)港公會進行經(jīng)營的達24個。1842年后,私營燈塔徹底退出了英國歷史舞臺。
二、對燈塔供給問題的經(jīng)典解讀
1.福利經(jīng)濟學(xué)理論
以庇古為代表的福利經(jīng)濟學(xué)理論,論證了市場失靈的存在,提出了“外部性”的概念,并且認為正是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使邊際社會收益(成本)與邊際私人收益(成本)產(chǎn)生偏差,從而惡化了整個社會的福利狀況。所以,對于這些會產(chǎn)生外部性的產(chǎn)品或服務(wù),需要政府進行投資以“鼓勵”或“限制”其發(fā)展。庇古認為,由于燈塔有很強的外部性,私人提供難以獲益,所以必須由政府進行經(jīng)營。之后,新福利經(jīng)濟學(xué)拓展了有關(guān)經(jīng)濟生活中價值判斷的理論,引入經(jīng)濟倫理及公平正義的觀點。該理論主張,公共產(chǎn)品本身就包含著倫理和道德的成分,對公共產(chǎn)品的提供面臨著好與不好、該與不該的價值判斷問題。該理論將公平正義作為包括經(jīng)濟制度在內(nèi)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首要目標(biāo)。那么,公共產(chǎn)品和服務(wù)作為人們可以更好地生產(chǎn)或生活的基礎(chǔ),較之一般的私人產(chǎn)品承擔(dān)著更為廣泛的社會職能,理應(yīng)由政府以收入公平分配為基礎(chǔ)進行生產(chǎn)安排,從而實現(xiàn)經(jīng)濟發(fā)展的社會道德價值。
考察我國和英國燈塔,最終都由政府統(tǒng)一進行籌劃管理,根據(jù)福利經(jīng)濟學(xué)的理論,一個合理的解釋則是: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進步,附于燈塔之上的經(jīng)濟意義越來越高,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也愈加明顯。也即,燈塔所體現(xiàn)出來的外部性得到強化,所以需要以公共產(chǎn)權(quán)的方式加以保障。在英國,政府對燈塔進行回購的原因是“燈塔的收費太高”,可見,在那時,私人只有通過高收費的方式才可以使燈塔的外部收益內(nèi)化到過往船主的成本,而這又違背了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造成社會總福利的損失。在我國,晚清燈塔的建設(shè)更是伴隨著國人海洋意識和人權(quán)意識的蘇醒,承載著發(fā)展航運和對外貿(mào)易,加強軍事防御和維護海泉等重責(zé)大任,已經(jīng)遠遠超越了其原始意義,故而私人是不可能再繼續(xù)承擔(dān)燈塔的建造和管理。
2.俱樂部理論
該理論認為,判斷一種物品是否為公共產(chǎn)品,關(guān)鍵取決于該物品的消費容量和潛在消費者,當(dāng)消費容量和消費者都趨于無限時,為典型的純公共產(chǎn)品;當(dāng)消費容量和消費者具有一一對等的關(guān)系,則為標(biāo)準(zhǔn)的私人產(chǎn)品;消費容量有限,而潛在的消費者卻無限時,就屬于俱樂部產(chǎn)品。俱樂部產(chǎn)品由俱樂部成員共同消費,而對俱樂部外的其他成員是排他的。此時,個人的行為選擇最終會導(dǎo)致一致同意的集體決策。原因在于,在俱樂部之類小團體中,成員之間的信息是完全的,達成一致協(xié)議的成本較低,對成員的激勵、監(jiān)督、懲戒也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實現(xiàn)。而且,對于俱樂部不滿意的成員也可以用以腳投票的方式離開,這就保障了每個成員在維護自身利益的驅(qū)動下,達成集體的一致決策并加以維護。而對于純公共產(chǎn)品來說,由于集體的規(guī)模無限大,要使所有人達成一致同意的決策成本、談判成本、監(jiān)督成本都會高到讓人卻步,因此,理性的人將會放棄這種努力,而對純公共產(chǎn)品消費的共同性又會使他很容易隱藏自己的實際需求而產(chǎn)生“搭便車”的現(xiàn)象,最終導(dǎo)致純公共產(chǎn)品的供給不足。
燈塔也可以認為是符合該種理論的俱樂部產(chǎn)品。早期,我國和英國的燈塔都是以民間建造為主,并通過收費的方式進行運營。尤其是在英國,燈塔建造的第一步是:“船主將愿意支付使用費的簽名請愿書交給樞密院……”燈塔建成之后,對于沒有“燈光通行證”的船主將會被禁止進入燈塔的輻射范圍,而且對于違反規(guī)定的船只,會有嚴厲的懲罰。通過這些方式,很好地維護了燈塔這一俱樂部產(chǎn)品的穩(wěn)定性。船主擁有燈塔的使用權(quán),燈塔的建造者擁有燈塔的所有權(quán),他們共同構(gòu)成了燈塔的集體產(chǎn)權(quán)。總之,根據(jù)俱樂部產(chǎn)品理論,燈塔可以由私人通過集體產(chǎn)權(quán)的方式進行提供。
3.交易成本和產(chǎn)權(quán)理論
該理論以交易成本作為出發(fā)點,論證了公共產(chǎn)品通過私有產(chǎn)權(quán)的方式進行提供是完全可行的。以該學(xué)派代表人物科斯的三個著名定理為基礎(chǔ),可以認為,若不存在交易成本,公共產(chǎn)品的提供無論是交給政府還是市場,都是有效率的,而最終由哪一方提供取決于兩者的談判和競爭;但若存在交易成本,公共產(chǎn)品由誰提供將取決于市場安排和政府制度安排中成本較低的那一方。在這里,交易成本又可分為內(nèi)生交易成本和外生交易成本。在燈塔的例子中,外生成本主要是指維護燈塔運營所耗費的一切成本,比如人工成本、信息采集成本等;內(nèi)生成本則是指由于收費所造成的效率的損失。最終,該一種公共產(chǎn)品的提供機制是否應(yīng)該被采納,應(yīng)唯一地取決于該方式是否最小化了公共產(chǎn)品提供過程的所有成本。例如英國燈塔的所有者向港口所有者收費而不直接面向船只收費,這種將燈塔捆綁于港口所有者的行為,既最小化了燈塔的收費成本,又使港口的所有者借助于燈塔的服務(wù)實現(xiàn)更多的營利,在這一過程中,燈塔所有者和港口所有者的產(chǎn)權(quán)利益都得到了實現(xiàn)。
根據(jù)這一理論,燈塔提供機制的歷史演變最終也是由其不同時期的交易成本所決定的。在早期,資本主義英國和封建末期中國政府的財政規(guī)模有限,若要建造燈塔,必然要以征稅的方式加以實現(xiàn),加之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這勢必會造成很大的內(nèi)生交易成本。而相對來說,私人由于其天生的信息優(yōu)勢和對過往船只收費的便利性,使其相較于政府提供有著更明顯的成本優(yōu)勢。但是,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私人提供不能滿足燈塔的多樣功能,只能以高收費的方式進行維持,而這其中產(chǎn)生的交易成本又會導(dǎo)致社會總福利的較大損失,而此時,技術(shù)的進步和政府管理能力的提升,使得政府進行安排的成本低于私人提供的成本,所以,市場選擇的最終結(jié)果是由政府來對燈塔進行生產(chǎn)經(jīng)營。
三、啟示
我國和英國燈塔的歷史演變縱然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沿著由私人供給為主到政府統(tǒng)一安排的路徑來發(fā)展。這一過程背后,必然有其經(jīng)濟原因。福利經(jīng)濟學(xué)從公共產(chǎn)品的外部性以及社會公共正義的角度,提出了通過公有產(chǎn)權(quán)提供公共產(chǎn)品的合理性;俱樂部產(chǎn)品理論重新定義了燈塔的屬性,認為集體產(chǎn)權(quán)可以實現(xiàn)特殊公共產(chǎn)品的充分提供;交易成本和產(chǎn)權(quán)理論,通過對不同時期燈塔提供機制的考察,認為公共產(chǎn)品供給邊界的決定因素是交易成本的高低,而這最終會外顯為不同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安排。
結(jié)合我國的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現(xiàn)狀,一直以來,政府對經(jīng)濟的干預(yù)力度都比較強,對于龐雜的公共產(chǎn)品的供給,政府的手伸的越來越長,財政支出壓力也越來越大,而效果卻不盡如人意。要想改變這一情況,可以從許多方面入手。結(jié)合上文的分析,筆者認為,首先應(yīng)該轉(zhuǎn)變政府職能,構(gòu)建服務(wù)型政府和現(xiàn)代公共財政體系。同時應(yīng)該加強政府在產(chǎn)權(quán)保護方面的制度保障和法律建設(shè),從根本上說,就是要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在充分考量促進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和實現(xiàn)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礎(chǔ)上,尊重各市場主體參與公共產(chǎn)品生產(chǎn)、經(jīng)營、分配的各種方式。唯有如此,才可以真正提高我國公共產(chǎn)品提供的質(zhì)量和效率。
[1]駱永民.交易成本視角下的公共產(chǎn)品提供機制[J].山西財經(jīng)大學(xué)學(xué)報,2007,(7):5-9.
[2]王瑤.科斯燈塔私人供給之謎的重新解讀[J].經(jīng)濟學(xué)動態(tài),2014,(8):117-125.
[3]李芳.晚清燈塔的建設(shè)與管理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xué)碩士學(xué)位論文,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