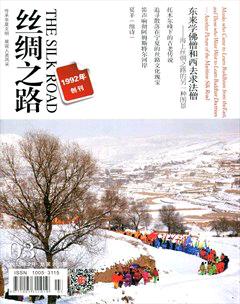東來學佛僧和西去求法僧
梁二平



忽然出來個“絲綢之路東起點”
中國南方沿海省份在談論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之時,不經意間,又有渤海圈的學者提出了宋代“海上絲綢之路北起點”之說。時間與空間,在研究海上絲綢之路這一課題時,出現了多個“第一”。正當國內沿海省份為了各自的出發點,紛紛重新定位自己省份的文化份量之際,我們又在與韓國學者的交流中,得知韓國以慶尚北道為首倡的“絲綢之路東起點”研究,正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我不知道,日本學界未來會不會加入到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熱”研究中來,若他們以九州的“漢委奴王印”為漢代中日交往之證物,完全會弄出又一個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更占優勢的“絲綢之路東起點”——博多灣(今日本福岡)。1990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海上絲綢之路活動,西邊從馬可·波羅的故鄉意大利威尼斯起程,東邊最后到達的是日本長崎。
多年來,中國人一直將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定位于南海的廣東和廣西,最西端一般定位于今天的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和東非肯尼亞、西北非摩洛哥。韓國則認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東起點應定為朝鮮半島東南方的慶尚北道港口。
海是開放的,海上絲綢之路是開放的,海上絲綢之路學術研究也是開放的,如果用這樣的立場來看,它本來也沒有什么起點和終點,交流是流動的。今天,大家來共同編織東方的海上交流之路,回顧對話與交流的歷史,構建“大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框架,進行更寬廣的學術研究,它于東方學、于絲綢之路學都不是壞事。
當然,話還要說回來,韓國的東起點是由何而來的呢?這就不能不提到唐代新羅僧人慧超到中國學佛的故事,和他后來由中國去印度取經的千年壯舉。
新羅僧人西航求法
許多人都知道敦煌藏經洞曾經藏有大量的中國佛教經典,但這些經典不僅僅是中國僧侶抄寫的,還有外國僧侶的貢獻。這之中最為韓國學者所樂道的即《慧超往五天竺國傳》,這部西游取經,游歷印度、波斯、阿拉伯的紀行,即是韓國僧侶慧超為大唐留下的寶貴財富。
應當說,中國學界在很早就注意到了這部典籍,它是法國人伯希和于20世紀初從我國竊走的大量唐代佛教文獻中的一部行紀殘卷,現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伯希和首先指出編號“伯希和3532”敦煌寫本殘卷就是慧琳《一切經音義》中的《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后經羅振玉對照敦煌寫本與《一切經音義》,證明敦煌殘卷“伯希和3532”確是《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日本學者藤田豐八曾于1911年參照法顯、玄奘等人的西行游記及歷代正史,對此作了考證和箋注,撰有《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一卷。1931年,錢稻孫曾把此書譯成漢語,線裝出版。1938年,德國東方學者福克司將此傳的漢文重新整編,并譯成德語,是為此殘卷在歐洲的第一個譯本。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朝鮮半島的學者高炳翊于1959年寫了《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史略》一文,鄭烈模將此傳譯成現代朝鮮語。近年來,由于慧超是新羅人,韓國對他的研究非常熱鬧:他被韓國稱為“古代韓國第一位世界人”,即韓國走向世界的第一人;2001年,韓國佛學界在西安市周至縣宣御寺慧超曾辦祈雨祭的地方,豎立了“新羅國高僧慧超紀念碑”,當時的韓國總統金大中題寫牌匾;2010年,韓國慶尚北道成立了“韓國絲綢之路項目本部”,準備為《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申請世界記憶遺產;2013年和2014年,韓國慶尚北道兩次組織上百人的絲綢之路探險隊,從陸路和海路重走了慧超西行取經之路。
據中華書局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往五天竺國傳箋釋經行記箋注》所載,中國佛教高僧傳記中并無慧超的生平記載(有人認為他出生于長安)。顯然,他還算不上大唐當時的高僧。中國的文獻中只稱他是新羅僧人,并沒有慧超入唐的記載。
2014年9月22日,在廣州召開的中韓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學術大會上,我有幸見到了韓國海洋史專家鄭守一先生,向他請教了近年韓國關于慧超的研究情況。鄭守一先生說,韓國方面的研究證明,慧超大約是704年生于新羅雞林,719年,大約16歲時,從半島的東海岸雞林走到西海岸華城唐恩浦,由此登船赴大唐學佛(也有一說是從半島最西南的黑山島渡海入唐)。在大唐,他師從密教大師金剛智,于玄宗開元七年(719)抵廣州,大約在開元十一年(723)由海路往天竺。西游四年后,由陸路返回大唐,寫成了此書。后來,他繼續跟隨金剛智和不空大師學佛,兩位大師先后圓寂后,780年,慧超來到五臺山。同年,在這里的乾元菩提寺圓寂。
存世三卷本《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是它的節錄,這部分文字記述了慧超從中國去古印度探求圣跡所經歷的數十個國家、地區、城邦以及中國西北的地理、宗教信仰、佛教流傳情況及風土習俗等。所記拘尸那國以前及最后部分已缺。依據本書殘留的記事,可知慧超在中國由海路進入古印度,曾經歷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而后進入北天竺諸國;最后,歷波斯、蔥嶺、疏勒、龜茲安西都護府,從陸路返回大唐。
此傳記錄了北方游牧部族突厥人進入西域后對“胡人”社會帶來變化的相關記載,為人們認識當時西域地區社會族群分布格局變動提供了一幅真實圖景。傳中曾談到:“毗耶離城庵羅園中,有塔見在,其寺荒廢無僧。”“迦毗耶羅國,即佛本生城。無憂樹見在,彼城已廢。有塔無僧,亦無百姓。”這些記載說明當時印度佛教已趨衰落。如書中記載:“龜茲國,又從疏勒東行一月,至龜茲國。即是安西大都護府。漢國兵馬大都集處。”“焉耆國,又從安西東行至焉耆國,是漢軍兵領押。有王。百姓是胡……”上述關于唐朝、突厥、大食和吐蕃在西域和蔥嶺以西諸地的逐鹿活動和治理情況的記錄應系原始材料,盡管細碎,卻是對其他相關文獻資料的有力補充,故彌足珍貴。
那么,慧超是怎樣經海路來中國,又是怎樣由海路去印度的?
慧超沒有留下這方面的記錄,唐代也沒有留下任何海洋地圖。關于東洋與西洋的海路,我們僅有宋代的地圖可作參考。現在,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的西行海岸圖,即《華夷圖》。它與同刻一石的《禹跡圖》不同。《禹跡圖》是華夏的國圖,《華夷圖》更近于世界圖景,是以華對夷來繪圖的,突顯了國家和國防意識,同時也描繪了西亞的海岸線。
不知道為什么,《華夷圖》沒有采用《禹跡圖》所用的“計里畫方”法,所以,其海岸線、島嶼和半島等海疆元素表達得都很不精確,特別是山東半島與雷州半島幾乎被畫“丟”了……但此圖周邊的大量文字注記,多少補充了“番夷”方面的不足,并透露出濃重的海防味道。
關于此圖的出處,圖上刻有這樣的文字:“其四方番夷之地,唐賈魏公圖所載,凡數百余國,今取其著文者載之,又參考傳記以敘其盛衰本末。”這段重要的文字告訴我們《華夷圖》是以唐代賈耽的《海內華夷圖》為基礎經過選擇后重新編繪刻石的。所以,它是唐、宋兩代地圖的混合體。
關于“番夷”,注記中有大量文字標注了中國周邊“番夷”國家和地區的名稱及其變遷。
東邊:《華夷圖》比《禹跡圖》有進步,清楚地繪出了遼水及入海口,并在遼水東岸標注“唐安東府”。再向東又比《禹跡圖》多畫出了朝鮮半島。半島上標有百濟、新羅、高句麗、平壤等名,并注記:“在遼東之東千里,東晉以后,居平壤世受中國討爵稟正朔。”或許,受地圖尺幅所限,朝鮮半島之東,沒有接著畫出日本。但在“東夷海中之國”的注記中,注記了日本、蝦夷(今日本北海道一帶)、女國、琉球……和“宋至者日本”等文字。
南邊:南海之疆與海南島畫得基本準確。海南島上面標有朱崖、昌化、瓊、萬、黎母山等字。在海南島的旁邊注記:“五嶺自衡山之南一山,東盡于海,其南漲海之北,古荒服秦置五郡,漢分九郡,曰南朱崖皆其地。”再向南,“海南之國”,已出圖外,沒有畫出。但注記有扶南(今柬埔寨、老撾、越南)等幾十個國名。
西南邊:《華夷圖》比《禹跡圖》所畫范圍大了許多。雖然筆調約略,但還是勾畫出了孟加拉灣和印度半島的基本輪廓,并標注了“五天竺(印度)”和“真臘(柬埔寨)”,是宋代地圖西南方向標注最遠的地方。這些描繪,對于我們了解大唐和大宋去天竺的海上認識與海岸描繪多有裨益。我們不能要求1000年前的古人做得更多和更好了。當年,西行路之辛苦,恰如慧超在他的紀行中所說:
我國天岸北,他邦地角西;
日南無有雁,誰為向林飛。
日僧白云慧曉與最早繪出海上航線的《輿地圖》
說完大唐的新羅僧侶,接下來再說說大宋的日本僧侶,他們都是從海上而來,又都為中國古代的航海史和海上絲綢之路留下了重要史料和線索。
唐代中國僧人東渡日本傳播佛教后,各種佛教學派在日本落地生根。1255年,源自中國的臨濟宗,在京都建成了當地最大的寺院——東福寺。曾經在大宋學佛的日僧圓爾辨圓被敬為開山之師。圓爾于1235~1243年跨海來大宋求學,曾在江浙一帶學佛八年。圓爾回國后,聲名大噪,曾為當時的天皇授菩薩戒,禪法由此進入日本皇室。
圓爾在大宋學佛后,其弟子也紛紛渡海求學,其中即有被寫入佛學史的日僧白云慧曉(即佛照禪師)。其著作,凡二卷,全稱《佛照禪師住慧日山東福禪寺語錄》,又作《白云慧曉禪師語錄》,收于《大正藏》第80冊。卷上包括慧日山東福禪寺之進山、上堂、小參、舉古、拈香,卷下包括小佛事、法語、雜篇、佛祖贊等,卷末附錄摘自虎關師煉所撰《元亨釋書·佛照禪師傳》。
史載,白云慧曉于1266年渡海入宋,在明州(今浙江寧波)的端巖寺學法。1279年,白云慧曉返回京都時,除了帶上一些佛學書籍外,還從大宋帶回一張拓印地圖《輿地圖》。日本僧人為何要帶回一張中國地圖?歷史沒留下任何記載,我想,這張地圖或許能透露一點線索。
白云慧曉拓印的《輿地圖》,原是一塊石刻地圖。其圖巨大,縱207厘米,橫196厘米。由左右兩幅拼合為一。此圖正上方刻“輿地圖”三字,左上方刻“諸路州府解額”(即科舉人數),圖中府、州、軍的名稱及數量大體與左上方刻記一致。原圖未記作者年代,后人根據圖上的政區改制內容,推定其大約繪于南宋度宗咸淳元年至二年(1265~1266)的明州,繪圖人不詳。此圖誕生之時,剛好白云慧曉來明州端巖寺學習,所以,他有機會見到此圖原刻,并將《輿地圖》拓片帶回日本。中國的這個石碑早已亡佚,白云慧曉的拓本成為僅存的地圖,現藏于日本京都栗棘庵,成為中日佛教交流的見證。
《輿地圖》是一幅包括宋代疆域及其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大型地圖。其地理范圍東及日本,西到蔥嶺(今帕米爾),南涉印度及印度尼西亞一些島嶼,北達蒙古高原。包括宋朝疆域內的政區名稱,東北部的女真、契丹、蒙兀、室韋,西北部的高昌、龜茲、烏孫、于闐、疏勒、焉耆、碎葉。東部及南部涉及到海外諸國,西南有印度、閣婆、三佛裘,以及南海上的一些島嶼,東邊繪出了日本等國。
圖中山脈用寫景法表示,并繪有森林。河流用單曲線表示,湖泊用水波紋表示,地名均括以方框。在許多州、縣間繪有道路。西南地區繪有少數民族分布情況。北和東北兩處,有數百字的注記,主要說明其歷史與地理情況。
從海圖的角度講,此圖最突出的特點是首次繪出了多條海上航線。在長江口方向,繪有一條沿海岸北上的陰刻水路,并以方框標注“過沙路”;另一條向東延伸到日本的陰刻水路,以方框標注“大洋路”;同時,在“東海”水域,還用方框標注出“海道舟舡路”。除了標注的海路外,在崇明島和臺灣一線,還以陰刻的白線描繪出幾條海路。在現存古代地圖中,它應為最早繪出海上交通路線的地圖。
這幅地圖的海上交通部分集中體現在東海一線。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從“崇明砂”起,有一條海路通往“蛇山”島(今崇明島以東),而后海路又通向“毛人”島,另有一條海路,向北直通“日本”島。從方位上看,位于“日本”島以南,琉球群島以北的“毛人”島,應是北九州島。而白云慧曉的師父圓爾當年回日本,就是在北九州的福岡登陸的。
這是日本僧人渡海來中國的一條重要海路。
按照這樣的分析,白云慧曉帶《輿地圖》拓本回日本,一是為讓日本人了解大宋的天下,二是帶回一張可供渡海的航海圖。另外,要特別指出的是,日本的地圖業發展很晚,基本上要靠從中國帶回的地圖來認識世界與自身。日本自主地圖測繪的歷史直到16世紀才開始。
我國海上交通在漢代就已經很發達,東去日本、朝鮮,南下印尼,西往印度、斯里蘭卡的航線都已開通。到唐、宋兩代,海上交通貿易更為發達。通往朝鮮半島與日本的航路在《新唐書》中曾有記載:“新羅梗海道,更由明、越州朝貢。”這是記載“朝貢”之路。實際上,明、越州也有大量的船在夏、秋時節利用東南季風渡海,斜向東北橫渡東海至日本,或沿黃海北上,赴朝鮮半島。但唐代沒有留下一張海圖,早期宋代涉及海洋的地圖中,也沒有關于海上交通的描繪,更沒有航線的標示。所以,《輿地圖》在這一點上顯得尤其珍貴,只是研究《輿地圖》的諸多論文中,關于海上交通與航線的文章還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