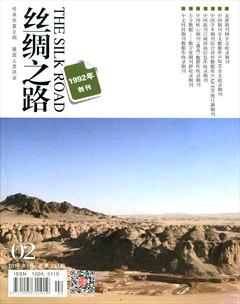絲路古道平川區境內古渡口與古城遺址考述
張明清
【摘要】白銀市平川區位在絲綢之路自陜西咸陽經六盤山通往西域的古道上。這條古道相對平緩易行,位在北武當山下的鹯陰口是古代條件相對較好的黃河渡口,其西岸車道溝較為平坦且直通今景泰川而徑往西域。漢武帝曾跨過六盤山從蕭關一帶西行,由平川區打拉赤經楊稍溝“西臨祖厲河而還”。境內自東向西分布著秦、漢、晉(十六國、北朝)、隋、唐、宋、明共10余座古城遺址。
【關鍵詞】平川區;絲路古道;古渡口;古城遺址
白銀市平川區位在絲綢之路北線古道上。絲綢之路從長安、寶雞經平涼、固原,一支線沿六盤山北麓過海原到平川境內打拉池后,又分為三條古道通往黃河邊:一條由打拉池經楊稍溝到靖遠縣城,從祖厲渡口西渡黃河;一條經打拉池入旱平川,到鹯陰渡口過黃河,經景泰縣西番窯,直達河西諸州;還有一條自旱平川北行經水泉、石門西渡黃河入景泰境往河西。
一、古老的東西大道
早在秦漢時期,已經有一條中原通往西域的主干道自東向西橫貫平川區境。這條古道自陜西至寧夏段古稱回中道,公元前220年,秦始皇曾沿此道翻越六盤山,巡行到今寧夏境內號稱“襟帶西涼,咽喉靈武”的蕭關一帶。漢武帝時張騫、霍去病都是抵蕭關再往西進入今平川區境,從鹯陰古渡直去西域。北逐匈奴,大面積開拓西北疆域之后,公元前114年,漢武帝分北地郡河西、置安定郡,置祖厲、鶉陰二縣屬安定郡轄(祖厲縣治在今靖遠縣西北的紅嘴子,鶉陰縣治在今平川區水泉鎮的黃灣)。之后,漢武帝數次經回中道西巡,公元前112年十月進入今平川區境,從打拉池沿楊稍溝到靖遠,“西臨祖厲河而還”。
這條古道在《讀史方輿紀要·迭烈孫堡》中也有記載:“明初元將賀宗哲攻鳳翔不克,自固原之六盤山遁去,明師追之,復由迭烈孫渡河遁。”又《明會要》:“(宣德)七年(1432)五月,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遜道路。”并解釋說,云此前“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蝎蜥嶺。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經迭烈遜黃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余里”。強調指出,迭烈孫黃河渡口在朱元璋時曾“官置渡船,平涼撥軍造濟,人以為便。”這一次是“如舊開通,以利民”。
二、黃灣古渡口
平川區黃灣古渡口即漢時的鹯陰口,宋、明時稱為迭烈孫渡口,清時為黃沙灣渡口,民國后稱之為安寧渡口。
黃灣古渡口位在紅山峽上口,渡口兩岸山勢深邃、溝豁叢生。渡口西岸車道溝,直通今景泰境內中泉鄉西番窯。西漢置縣之前,黃灣渡口名為漠口,這一帶流傳著霍去病西征匈奴渡河時的傳奇故事。《后漢書》記載,護羌校尉趙沖率騎追擊叛羌,戰歿于鹯陰口。《三國志》記載,涼州盧水胡反,魏文帝曹丕派張既前去平定,盧水胡在鹯陰口埋伏了7000多騎兵,張既另選別處暗渡黃河,大破盧水胡。西晉亡后,北方進入十六國時期,鹯陰口烽煙不斷,當地流傳著前秦滅前涼時,大軍渡河時的種種傳說。隋唐時期,會州是朝廷屯軍養馬之地,唐朝在鹯陰口設有管理機構。唐代名臣名將如李靖西征吐谷渾、尉遲敬德西征突厥、薛仁貴西征吐蕃,都曾從鹯陰口渡河西出。渡口西岸的塔兒山上有數處古塔遺址,據說是武則天派人修造的七星塔。北宋末年,在渡口修造索橋,西夏占據后,在渡口筑城防守,名為“迭烈遜(孫)”。
明洪武三年(1370),“建置船只索橋,通涼莊路”,“設巡檢司于此,每歲冬增兵戍守”。宣德年間(1426—1435),“此時,復開此路,命陜西布政司造船八艘,每艘十一人持之,隸迭烈孫巡檢司”。黃灣古渡口是明代黃河上游一座規模很大的官方渡口。但有明一代,游牧于黃河西面的蒙元遺兵不時乘冰從渡口過河東掠,靖遠、會寧直至定西、固原一帶發生十多次較大規模的戰事,都與迭烈遜渡口有關。清朝數次西征,部分大軍往來是從這里渡過黃河的。此時渡口的主要功能是商貿要津,不再有防守職能。
1944年,應抗日急需,甘肅省政府將蘭寧公路改道從黃灣渡口渡河,稱之為為安寧渡,初置四艘單車渡船,后置四艘機器拖輪。從此,安寧渡進入現代機器輪渡。解放戰爭時期,安寧渡為人民解放軍快速進軍寧夏發揮了關鍵作用。1958年,為了方便靖遠縣城的交通,渡口移至縣城西北漢代祖厲渡口舊址,名為紅嘴子渡口。黃灣渡口現在為民渡,國家投資架設了滑輪索道和渡船,以水力為動力。
三、古城遺址
數千年古道,數千年古渡,從秦漢至明代,沿著這條古道在平川區境內留下了很多古城遺址。
平川境內最早的古城是西漢武帝時的鶉陰縣治。有學者研究認為,西漢鶉陰縣城在平川區水泉鎮黃灣的北武當山上,而且提出了保護鶉陰城的中肯建議,其實山上的古城是西夏的迭烈遜城。鶉陰故城遺址位在山下原黃灣學校及李家堡子一帶,東漢年間縣城被一場大洪水沖毀,洪水的痕跡至今可辨。位在黃灣古城遺址東山上有一處規模很大的古墓葬群,西漢墓葬特征明顯。近五六十年來,人們在修田建房時挖出的古墓就有300座以上,被平川區確定為文物保護單位。20世紀70年代,文物部門發掘了一座古墓,內外兩室,四周和墓頂全是方木圍封,經考證認定為漢墓,出土文物保存在靖遠縣博物館。2013年,又發掘一座規模更大的西漢墓,經專家們認定黃灣古城遺址就是西漢的鶉陰縣城遺址。鶉陰縣城東漢年間被洪水沖毀后,移置于旱平川,史書記其名為鹯陰。祖厲縣城也應是毀于這場洪水而移置于今會寧縣境的。學者們普遍認為,鶉陰縣城是秦將蒙恬沿河所筑抗御匈奴的古城。蒙恬“城河上為塞”阻擊匈奴,而漢武帝以秦城置縣,河西諸郡與朝廷的交通也是考慮的主要因素。
旱平川新墩有東、西兩座土筑古城,民間稱東城為“纏州”,西城為“柳州”。據《甘肅通志》載:“鹯陰古城,在靖遠縣北。東漢作鹯陰縣,屬武威郡。晉廢。”旱平川新墩東城即東漢的鹯陰縣城。鹯陰城原是一處匈奴部落聚居地,西漢政府在黃灣渡口設置鶉陰縣后,慢慢形成了集鎮“廛里”,東漢時在集鎮的基礎上擴筑為鹯陰縣城。根據《魏書》記載,鹯陰縣南北朝時又復名鶉陰縣,也就是說,這座古城史書上先后使用過鹯陰、鶉陰兩名。宋時,此地曾長時間為西夏占據。西夏人在占領地“以堡鎮號州”,或因城名之聲韻變化,或因“廛里”之名一直在民間流傳,鹯陰城名成了“纏州”。
新墩西城是前秦平涼郡郡治和唐代涼川縣治。晉太元元年(376),前秦滅前涼,為彰顯其功績而置平涼郡,《魏書·地形志》:“平涼郡,領縣二。鶉陰,郡治。前漢屬安定,后漢屬武威,……”云明確記載了鶉陰縣的履歷,魏晉賢先生《甘肅省沿革地理論稿》據此認定此處的鶉陰就是旱平川的漢城鹯陰。平涼郡治筑在鹯(鶉)陰縣城邊,就是今新墩西城,距鹯陰城僅300余米。平涼郡自設置至隋末,有200年郡治不在平涼縣,從《魏書》、《隋書》中即可求證。唐時復置會州,以會寧縣為州治,在恢復隋涼川縣名時,將涼川縣“別置”于平涼郡治古城。涼川縣城被稱為“柳州”,可能是音轉,也可能是西夏留下的城名。
西秦麥田城。東晉咸和四年(329),羯族后趙石勒滅匈奴前趙劉曜,嚇壞了鮮卑乞伏氏首領傉大寒,乞伏氏自榆中苑川“懼而遷于麥田元孤山”,在麥田駐36年后,因氐族前秦進逼,又由麥田遷于度堅山。
古籍記載麥田城地理環境的只有《水經注》。酈道元《水經注》在記述完祖厲川水之后說:“河水又東北徑麥田城西,又北與麥田泉水合,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北徑麥田山西谷,山在安定(固原)西北六百四十里。”依此,麥田古城在靖遠城以北的黃河下游,而且瀕臨黃河。《大清一統志·蘭州府·古跡》載:“麥田城,在靖遠縣東北。”考察靖遠縣東北黃河沿岸,只有距新墩兩古城西南約5公里處、位在旱平川南沿月河的古城遺址的地理特點,符合《水經注》對麥田城地理環境的記述,也符合《大清一統志》的記載。仔細考察即可看出,此故城初筑在古沙河南面的平臺上,后來不知是西夏引水掘城,還是自然突發洪水,致使沙河改道從城中穿出,大部城墻被沖毀,僅留一面城墻被分割在沙河的南北兩邊。30年前,月河河口、沙河南北兩側各有一段雄偉的古城墻,可惜近幾十年毀墻平地,使古城墻現在僅存一段。古城墻北面沙河故道的痕跡現在還很明顯,西北故沙河口汩汩涌淌的泉水,泉水流出故城西北后西南方向流入黃河的痕跡,與《水經注》所記麥田泉水完全吻合。
200年后,宇文泰為西魏丞相時,于公元548年奉西魏太子率兵西巡,會師于鶉陰,當地人張信拿出全部家產慰勞六軍,宇文泰非常高興,就以“會”為名置會州。唐人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記述了這段歷史,并清楚地記載:“會寧,本漢鶉陰縣地。”學者們根據史籍中記載的會州與蘭州、鹽池、固原等地的距離推算,確定故會州在旱平川。但旱平川有四處古城遺址分布在方圓三五公里的范圍內,到底哪一座才是故會州城呢?《元和郡縣圖志·會州》記載:?“開元七年(719),河流漸逼州城,刺史安敬忠率團練兵起作,拔河水向西北流,遂免淹沒。”《新唐書》也有此記載,說明會州城在黃河邊沿。
另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述,宋朝收復古會州地后,地方軍政官員因選擇新筑會州地址而發生爭議,對原會州地理位置和地形作了較清楚的描述:“會州西地名巴寧會,地形高爽,土脈堅潤,比之古會州更險要。”最終在“會州川口”即今靖遠縣城“初筑會州”即宋會州。結合諸史籍可以看出,宋代以前故會州的地理特點:臨河,城西有一高地也可筑城。平川月河與今靖遠城之間的河川,宋人叫“會州川”,而《舊唐書》稱之為“會寧川”,說明宋筑新會州之前故會州也在這一河川上。如此,只有河川最北的月河古城遺址具備這些條件。因此,西魏時宇文泰初置會州是以麥田故城為州治的。
宇文泰置會州,北周武帝于保定二年(562)廢會州,改為會寧防,隋初又改為會寧鎮,后撤鎮置會寧縣,屬平涼郡轄,此時平涼郡治在今固原。隋大業二年(606)置會寧郡,改會寧縣為涼川縣,以為會寧郡郡治。唐初,在涼川縣置西會州,復會寧縣名,作為西會州州治。貞觀八年(634),改為粟州,后又復為會州。“開元四年(716)別置涼川縣”,即恢復了涼川縣名,而置縣于平涼郡治故城。涼川縣名應該來源于平涼川,說明位在月河北面的旱平川當時叫作平涼川。
北宋末期,在今靖遠縣城筑的新會州,后被金兵攻占,又被西夏攻占。金朝在今會寧郭城僑治會州,之后,會州便落戶于今會寧境。
另外,從會州州治城名的變化也可看出唐及以前會州城地理位置的特點:西魏所置會州,北周改為會寧防,這是“會寧”名稱第一次出現;隋朝撤防設鎮又改為會寧縣,又置會寧郡,將郡治會寧縣改名為涼川縣,這是“涼川縣”名的第一次出現;唐在涼川縣置西會州時,恢復州治名為會寧縣,后恢復會州建制時仍以會寧縣為州治,但“別置涼川縣”。從會州州治在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圍繞“會寧”、“涼川”兩名的交替使用來看,唐及以前的會州城就在“會寧川”和“平涼川”的交界處,也就是在今靖遠城東一彎河川和旱平川的交界處,而月河的麥田古城遺址正好位于此處。這一特點和前述對唐及以前會州城址的推斷相吻合。
北宋在會州川口新筑會州時,于今平川區共和鎮打拉池筑懷戎堡,在其西20里的毛河洛筑水泉堡,在其東楊崖灣筑通會堡,通會堡當時屬今寧夏海原境內的西安州轄。西夏占據此地后,在鹯陰渡口筑迭烈孫堡。明代先后筑有水泉堡、陡城堡。而這10座古城,除打拉池及其東的通會堡和其西的水泉堡外,其他7座古城都在旱平川及其周邊方圓20公里范圍內。
四、遺址現狀
平川區沿絲綢之路古道兩邊,分布著從秦漢至明代共9座古城遺址,而且至少還有三五處古城遺址尚未查清其朝代和古名。鶉陰古城已毀于黃河洪水,會州古城城墻現僅存一墩,迭烈孫古城址就在北武當道觀,懷戎堡內有民居農田,城墻已不完整。水泉堡城南墻不存,陡城堡內為民居。
鹯陰古城城址清晰,1970年后被平整為農田。古城只有一座南門,東、北城墻今尚存數段,南城墻上已改為水渠。城墻東西、南北各長325米,面積約158畝。城周有城壕,挖出過漢代箭簇等兵器。城東北部曾挖出過古窨洞,內有兵器、尸骨,但未深探便填埋了。城中遍布磚瓦碎片,有專家鑒定是漢瓦無疑。
唐涼川縣古城也已變為農田,但城墻基本保存完好。20世紀70年代平地時村民就勢鏟成塊田,沒有深挖,在城東北部鏟出直徑約1米的兩塊柱砥石,估計是衙門所在。東城門處挖出直徑約50厘米的城門梁,上有大火燒灼痕跡。城中有一直徑1米多的井口,與北山下沙河一暗洞相對應,或為取水設施。涼川城有東、西兩城門,城門有甕城,甕城口皆面南。東、南、西三面城墻下有城壕,城墻最高處頂端距地面16.4米。墻頂寬3~5米,城面積約180畝。城四面城墻各有向外突出的墩臺,是為“馬面”。涼川城北臨陡坡,水路隱蔽且近,從坡下水頭村莊仰望城墻,陡峭險峻。其規格要遠遠高于鹯陰縣城,說明前秦筑平涼郡治時的軍事防御目的非常明顯。
五、保護和開發
1976年定西地區文物普查時認定新墩西城為唐代古城。1980年,靖遠縣政府將新墩兩古城遺址列為文物保護單位。白銀市恢復建制后此地歸平川區轄,1994年1月,平川區政府于兩城遺址建立縣級文物保護碑。
白銀市平川區處在“蘭白都市經濟圈”的中心區域,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文化發展勢頭良好的一個新興城區。,這座現代新興城區可以說是絲綢古道上的一株文化奇葩,境域古遺址密布,文化堆積深厚,考察這些古遺址,就好像打開中國西北數千年歷史畫卷,對民族文化的傳承,對絲綢之路歷史文化和旅游文化開發有著很重要的現實意義。為此,提出以下建議:
其一,建立健全古文物保護機制,明確區級文化部門、鄉鎮政府直至村民委員會的保護責任,管理制度化常規化。
其二,繼續查明那些史跡還不清楚的遺址。平川區博物館加大文物搜集力度,盡可能阻止文物的遺失和散落。
其三,在加強保護的同時,積極開發利用。鹯陰古渡口、迭烈遜古堡城、北武當古道觀、西漢墓群都集中在黃灣,和明水泉堡城以及野馬巖畫、元屯石林等文化古跡及太和島在同一片區,列為北武當景區,得黃河之優勢,開發前景無限。
鹯陰城、涼川城、會州城屬水泉鎮牙溝水村轄,連同陡城堡可建立一個文化景區,其中鹯陰城距離黃河不過四五公里,會州古城遺址在黃河邊的月河,月河社的農家樂已名享遠近,東依國道,西臨黃河,開發條件十分優越。打拉池的宋代懷戎堡、宋水泉堡、宋通會堡以及清奮威將軍王進寶墓和故居可組建為一個文化旅游景區,打拉池臨近屈吳山,開發條件非常優越。平川區有很多紅色遺址,明水泉堡是紅軍游擊隊成立并戰斗過的地方,打拉池是紅軍會師地,20世紀三四十年代黨的地下組織在陡城、水泉、黃灣一帶活動活躍,溯昔追今,是進行歷史文化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的優秀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