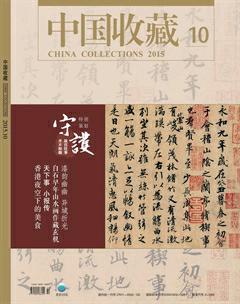那些你所不知的故宮往事
王菁菁

政治與政權會以人的立場和意向為轉移,真正的藝術與文化卻永遠直指最原始的人心與人性。這也是為何文物會被承載賦予某種政治價值與政治認同感的原因。
“紅墻綠瓦、宮鎖珠簾”,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故宮最“致命”的吸引力,莫過于它的神秘莫測。即便已經建立博物院90年,依然如此。
相信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心態:越是好奇,越想走近它。然而長期以來,對于故宮與民眾之間的距離,輿論卻總會有著這樣那樣的詬病,比如太封閉、傳統、不接地氣,甚至在最后,大家往往都會將質疑的原因歸結為兩個字:體制。
那么,事實究竟如何?
祝勇,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2011年走進這座“深宮大院”,既是學者出身,又帶著散文作家浪漫氣質的他曾因《故宮的風花雪月》一書被不少“同好”于此的讀者所知。而在“慶院90周年”之際,他將再次推出新作《故宮的隱秘角落》。“客觀地說,這90年走得很不容易。任何事物的發展都需要經過累積的過程,今天我們眼中這個表現得越來越開放的故宮,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代代人長期不懈努力的結果。當然,故宮要更貼近民眾,還有許多不足之處需要完善,但回顧以往,用‘封閉’二字來評價故宮,有失公允。”在專訪的一開始,祝勇就如此對《中國收藏》記者說道。
一直在堅持開放
1925年10月10日,紫禁城終于變成了一座博物院,這一名稱概念源自西方。皇帝生活的地方竟然變成了博物院?這在當時無疑是個石破天驚的消息。特別是自晚清以來,慈禧、光緒、珍妃之間的關系、恩怨等等,已經通過各種畫報、民間筆記小說廣為流傳,老百姓特別關注。祝勇曾經研究過故宮開放當天北平的很多報道,“人們蜂擁而至,很多觀眾甚至趴著窗,就是為看一眼后宮到底是什么樣。”
采訪中,他以1925年為起點,給故宮博物院的90年做了一個粗略的分期——第一個時期是1925年到1937年,日本占領北平之前的12年,這是故宮博物院建立、草創、奠基、開放的12年,這期間不僅實現了紫禁城后宮對民眾的開放,而且相關文物的整理工作也馬上開始進行;第二個時期是1937年到1949年,當時日本占領了北平,同時也占領了故宮博物院,抗戰8年被稱為“日偽故宮時期”;第三個時期是1949年到1979年,在祝勇看來,這30年有點兒像1925年故宮草創后,因為歷史又回到了新的起點;第四個時期則是1979年至今,這個大發展與大轉型的時期也是現在的人們相對更加熟悉的。
“之所以說故宮不封閉,一直開放、堅持辦展覽就是很好的證明,我可以給大家舉幾個例子。”祝勇說。
比如人們熟知的故宮文物南遷與西遷,這在世界博物館發展史上,都是文物保護值得濃墨重彩的獨特一筆。但即便是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之下,一路上,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還在堅持辦移動展覽,目的很明確——激發國人的愛國熱情。據說,展覽反響非常熱烈,更加堅定了當時全民抗戰勝利的信心。
而且,彼時的故宮不僅在國內辦展覽,還走出了國門。比如在1935年,故宮文物赴英國倫敦展覽;上世紀40年代初,故宮文物赴蘇聯,參加了在莫斯科、列寧格勒舉辦的中國藝術展覽會。其中在英國倫敦舉辦的故宮文物大展,為了體現對展覽的重視,當時英國專派軍艦負責文物來回的接收,以確保安全。展品則上至商周青銅器,下至宋元名畫,活脫脫呈現出一部較為完整中國的文明史。“倫敦的這個展覽,去了很多國民黨政府官員和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把大展辦到歐洲就是要宣傳中華文明,讓全世界不要小看中華民族,同時讓世界知道中華文明的淵源流長,絕不能毀在日本的鐵蹄之下,以爭取國際對中國抗戰的支援。轟動的效應是可想而知的。”
另一個特殊的例子是在“日偽故宮時期”。事實上現在很多人不清楚,從故宮遷徙的文物只占了一部分,還有很多都留在原地。根據當時的統計,留在北平故宮的文物多達118.9萬件。時任院長馬衡已經隨文物西遷,留守的負責人是總務處長張庭濟。這是后來學術界中一個比較有爭議性的人物,因為在日軍占領故宮后,依然采用張庭濟來負責故宮的日常管理工作,這意味著其任了偽職,要從日偽政府領取薪水。不過祝勇還是認為,僅從守護文物、維護故宮運營的角度而言,不能完全抹殺張庭濟的功勞——8年間,故宮還在堅持對外開放。尤其是1945年10月10日,恰恰是故宮建院20周年當天,太和殿中舉行了華北日軍的受降儀式,故宮終于又回到了北平政府手中。而除了一些銅缸被日軍在戰事后期拿去造子彈外,文物幾乎沒有損失。
資料顯示,除了“文革”最亂的三年中,周恩來總理為保護故宮文物不被“破四舊”而下令關閉以外,無論時局如何變化,故宮的展覽、對外開放一直未曾間斷過。
眾星云集之地
身為中國最負盛名的博物院,90年來,故宮的“誘惑”絕不只是存在于平民百姓間。
據祝勇介紹,在故宮博物院成立、初創的第一個時期,北平已是文化和學術之都,特別是“五四”以后,很多的學術巨匠都聚集在此,這為故宮博物館利用人才資源開展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機。隨著宮殿文物、檔案、資料的逐一公開,大量的知識分子都介入了對故宮的研究,助力故宮作為博物院的功能全面展開。 值得一提的是,這期間還成立了故宮理事會,很多文化大師包括蔡元培等人紛紛加入其中。理事會成員甚至還包括不少當時的政界“大佬”級人物——蔣介石、汪精衛、于右任、張學良……可謂群星熠熠。而從政府的層面來看,不管是北伐之前的段祺瑞,還是北伐之后的蔣介石,在撥款資金等方面對故宮博物院的重視程度都不曾減低過,甚至可以說是不遺余力。
當時針指向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1979年的這30年間,故宮再一次迎來“新生”。之前因為戰亂而分離的文物,比如南遷西遷的、還有溥儀帶到“偽滿洲國”的,終于為多年漂泊劃上了句號,與留在故宮的文物完整重聚。而從1948年開始,古物陳列所這個原屬“前朝”的范圍被劃給了故宮,前后打通,形成了今天完整故宮的面貌。由此,其他各種展覽、研究、出版也更加熱熱鬧鬧地開展了起來。 這當中有個很有意思的“小插曲”,就是學術界關于沈從文先生究竟有沒有在故宮工作過的疑惑。祝勇說,1956年、1957這兩年,時任院長吳仲超開始為“重生”的故宮四處搜羅人才。而在新中國成立后,沈從文先生工作于歷史博物館,工作地點就在今天的午門,由于當時的午門是歷史博物館,并不屬于故宮博物院,這讓很多人誤以為沈先生是在故宮工作。據說,這段時期是沈從文人生中的“低落期”,就連自己的學生、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來歷史博物館視察,他都避而不見。后來,吳仲超想調沈從文到故宮工作,猶豫再三的沈從文沒有應允,但接受了特聘研究員的身份。于是,故宮博物院在其北面給沈從文安排了一間辦公室,他每周過來一兩次,重點是幫助織繡組工作、進行專家指導。
有歷史研究學者認為,從“五四”運動到“文革”前這段時期,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在學術研究上的激情、迸發力與思想自由的程度是遠勝于之后的。顯見此時的故宮,在充實實力,整理、展覽上都得到了長遠發展,種種因素促使這里的一切比較順利地走上了正軌。據悉,當時大學的美術史、藝術史等教材,很多都是出自故宮。隨后,受“文革”影響,故宮關閉三年后于1971年重新開放,由此進入了比較平靜的研究展覽時期。
文化“國脈”
通過上述回顧,很容易讓人產生這樣的聯想,雖然中國的文物不是僅留存于一座故宮,但一直以來,它儼然成為了中華文明象征的一個難以取代的“符號”,鑒于此,在某些特殊的背景之下,文物會超脫本身的文化意味,被用于、以至帶來其他更廣泛的效應,比如政治、比如精神。
“我認為故宮的文物,是文化‘國脈’的象征。今天故宮文物的最大一筆遺產來自清朝的皇家收藏,從‘康雍乾’開始。在那個時代,天下的文物基本上都集中在皇家手里,流落在民間的特別少,特別是經典文物。所以故宮的文物是流傳有序的,歷朝歷代,一代代這么傳承下來,這就絕不僅僅是文物值多少錢的問題。”祝勇回答道。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在當年戰火紛飛的狀況下,國民黨政府還要將文物運往臺灣。不僅是因為其珍貴、值錢,而是在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看來,有了文物在,臺灣就不再是只偏居一隅的“小朝廷”,而是順承了文化“國脈”,會顯得“名正言順”。
提到流入臺灣的故宮文物,現在很多人都認為占了當年故宮文物的大部分以及優質部分,實際并非如此。“當時運走的是極小一部分,因為條件所限,只有三艘軍艦。據統計,南遷文物匯集在南京的13491箱,運到臺灣的是2972箱,不夠一個零頭。”
由于戰況緊急,文物運臺的時候,并沒有經過仔細挑選,而挑選的標準當年也與今日有所不同。“當時的標準基本是集中在書畫瓷器和青銅器,而其余的很多是不入當時人的“法眼”的,比如說家具。另外,像清代的皇帝、后妃的巨幅畫像,每一幅都有一間屋子那么大,由于國民政府是反清的,所以也不拿走;還有一些大型玉器,太占地方于是也留了下來。再說匆忙也讓他們有些措手不及,比如有些皇帝自用的東西,進貢的也好,或者是江南織造、內務府打造的也好,原本都有精美包裝。走的時候擱不下,他們就留下了盒子,而盒子本身也是文物,當年造成的分家讓現在兩岸故宮必須合作來研究。”祝勇告訴記者。
無論是抗戰時赴外辦展,還是部分文物被運往臺灣,抑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舉辦“偉大的祖國”展覽用以振奮人心,再到“文革”時期帶有意識形態和階級斗爭色彩的泥塑《收租院》走進故宮公之于眾……政治與政權會以人的立場和意向為轉移,真正的藝術與文化卻永遠直指最原始的人心與人性。這也是為何文物會被承載賦予某種政治價值與政治認同感的原因,特別是對于故宮,這樣一座被濃縮為中華文化符號的院落來說更是如此。或許,故宮給世人留下封閉、被體制所左右的印象,與此也有一定關系。
當然客觀地說,只要不是在某些特殊時期的“過于政治化意味”,我們在看待文物、文化、交流的時候仍然應該試著讓眼光“開放一些”。以近年來兩岸故宮的合作為例,據祝勇介紹,2002年鄭欣淼就任故宮院長,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訪問臺北故宮,當時對方的院長是“綠營”的杜正勝,兩岸關系正處于“冰點”的臨界處。這種情況下,鄭欣淼的到訪無疑被輿論視為非常大膽的舉動,引起了很大轟動,建立兩岸故宮正常的交流從那時起開始在摸索中一步步前行。后來,著名文物專家朱家溍先生到臺北故宮做報告,座無虛席,他的開場白即為“我的故宮同事們”,全場頓時掌聲雷動……
“因為兩岸有著共同的文化血脈,我反而認為現在的我們沒必要為當年文物去了臺灣而感到心痛,因為有它們在,至少證明了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祝勇感慨道。
也許,一方面是博物館應有的公眾教育功能,另一方面是文物保護,當兩者碰撞,必然會有矛盾之處。公眾希望故宮打消神秘感,別那么被“左右”,開放得越多越好的迫切愿望在情理之中;但從守護的角度而言,文物保護總是置之首位的,“這不是圖一時之快的事,我們的后代子孫也有看文物的權利。”采訪臨了,對于守護二字的總結,祝勇表現得很堅定。
寫到此,回過頭再看文章開頭的疑問,故宮封閉嗎?或許未必。90年來,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體制,其實沒有必要太糾結于當中的那些“不得已”。只不過,民眾與文物的距離只隔著一所故宮時,能不能向著彼此的了解之路再邁一步?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