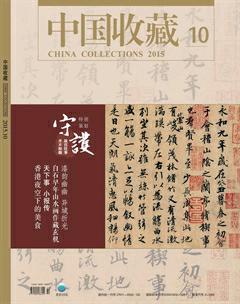龐薰琹VS王濟遠
理智

王濟遠與龐薰琹,亦師亦友,他們共同在上世紀30年代的大上海文藝界,掀起了繪畫革命的浪潮。隨著運動的深入,他們的人生之路也開始變得不同,一個深入西南,一個遠走他鄉。而今,80年之后,在新一輪老油畫熱潮來臨之時,他們的市場表現又如何呢?
龐薰琹:遠走重洋 義結畫社
1925年,19歲的龐薰琹棄醫從藝,遠涉重洋來到法國巴黎,入敘利恩繪畫研究所(又譯作朱麗安學院)學習。兩年后,他又接受了常玉等朋友的勸告而進入了藝術氣氛活躍的大茅屋畫院研習繪畫,并結交了很多藝友。
作為一位多才多藝、開拓型的藝術家,1932年9月,龐薰琹在上海舉辦了回國后的第一次個人畫展,讓人們大開眼界。人們在驚異興奮中發現:“他的作風,并沒有一定的傾向,卻顯出各式各樣的面目,從平涂的到線條的,從寫實的到裝飾的,從變形到抽象的形……許多現在巴黎流行的畫派,他似乎都在做新奇的嘗試。”(倪貽德《藝苑交游記》)尤其是他的“純粹素描”,與作為油畫底稿的素描所不同,有些中國的淡墨畫的意味。
1931年9月23日,在上海梅園酒家,龐薰琹、倪貽德、陳澄波、周多和曾志良等5人召開了一次私密的會議。他們因痛感“中國藝術界精神之頹廢與中國文化之日趨墮落”,于是集合了起來,懷著挽狂瀾于既倒的決心,“不避艱辛,不問兇吉,更不計成敗,向前不息勇猛的進。”就這樣,一個在中國近代美術史上影響深遠的藝術社團——“決瀾社”應運而生了。
縱觀決瀾社主要成員的創作傾向,他們大膽地借鑒和吸收了印象派以后現代派繪畫的各種藝術風格和手法,在自己的創作中體現了出來,對于當時的中國藝壇,無疑是吹進了一股新鮮的美術之風。
在整個決瀾社時期,龐薰琹的藝術創作大約可劃分為兩個階段。前期,龐薰琹創作作品的題材大多是靜物、風景,以及憂郁煩悶的青春女性形象、畫室里的女性、跳西班牙舞蹈的女郎等。他沉醉于純粹的形、色、線的“藝術世界”中,他作品中的形象大多安逸、優雅,秩序感強。然而,從第三次決瀾社畫展之后,他的藝術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轉變。
他在藝術上不再只是追求純粹形式的審美趣味,而是在形式創造中揉合特定的思想意識,他努力地將巴黎的藝術趣味與中國的現實生活內容結合起來。用具有象征和隱喻的藝術表現手法,畫面運用立體主義的幾何造型方式,同時以一種“超現實”的手法將多種形象內容組合在一張畫面中,各種并置的形象表達出作品的內涵。
決瀾社的成員除了龐薰琹之外,還有倪貽德、陳澄波、周多、曾志良、王濟遠、傅雷等人。他們都是當時不甘于被時風所困而隨波逐流的新進畫家,他們雖然藝術觀念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卻以狂飆運動來沖破庸俗陳腐的畫壇沉寂的局面,掀起一個新興藝術運動。
王濟遠:自學成才 旅居歐美
王濟遠原籍安徽,生于江蘇武進。自幼鐘情繪事,天賦極高,所作花鳥人物無一不佳,于1912年從江蘇第二高等師范學校畢業,之后到鄉間小學教書,兼以繪事排遣時日。他以水彩聞名,兼善書法,一時間在江南畫壇聲名大噪。
1918年,王濟遠經友人介紹正式進入劉海粟等人在上海創辦的上海圖畫美術院專業學習西畫。在系統學習了一年之后,王濟遠即從學校畢業。在美院學習的一年對王濟遠至為重要,他受了西洋油畫的影響,后來的畫風大多在此基礎上衍生。
1919年,王濟遠從學校畢業之后即留校任教。同年秋,他和劉海粟等人一起創建繪畫團體天馬會并擔任要職,爾后擔任上海美專教授和教務長長達12年,被視為美專派健將之一。1926年,王濟遠辭去上海美專教職,并于1926年赴巴黎考察美術,在當地舉辦了畫展。1927年創辦“藝苑繪畫研究所”,數次赴日考察。
1932年,王濟遠加入決瀾社。其時,決瀾社幾乎都是小青年,惟獨他是40開外的中年人,他被稱為“我們社的大叔”,是決瀾社不少成員的師長。
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畫壇上,王濟遠看似寡言少語,但實則勇猛沉著。他與同仁盟友們頻繁地從事各種藝術活動,為現代藝術吶喊,做了許多推進現代藝術的實事,且“不問什么收獲不收獲”,因而聲譽十分響亮。他的作品更受邀參加過日本的國家級油畫展,作為重要的民國畫家被推出。
王濟遠身邊的朋友決瀾社中的龐熏琹、倪貽德、陳澄波、傅雷等固然是人杰,其他與他往來的人也十分耀眼。1916年他與顧淑娛結婚時,胡適曾出席他的婚禮。晚年在美國還與張大千共同舉辦過畫展。還有與他或為盟友或為師生的蔡元培、劉海粟、張善孖、黃賓虹、朱屺瞻、林風眠、關良、潘玉良等,這幾乎就可勾勒出民國時期文化藝術生態的一個基本形貌。王濟遠于其中的貢獻不盡然只有賴于繪畫這一件事,他本人更是中國早期現代藝術的重要推進者,這個成績大概比他的繪畫更得肯定,因之他享有現代藝術史中的一席之地,是毫無疑問的。
1941年起,王濟遠開始定居美國,并創辦華美畫學院,傳授中國畫藝及書法。在移居海外數十年間,他志在追求中西畫藝之調和,其作品以水彩畫見長,多取材于風景,油畫風格受塞尚影響,又蘊含東方文人氣質。今有臺北歷史博物館及故宮博物院、北京中國美術館都永久收藏了他的作品。
龐薰琹:起步較早 漸入佳境
相較于王濟遠盛名之下的毅然出走,龐薰琹選擇了繼續在國內任教,并且深入西南省份考察搜集中國古代裝飾紋樣和云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1948年,他拒絕赴美國執教之聘,由粵返滬,迎接解放。
基于以上原因,龐薰琹在國內的知名度要遠遠大于年長他—在當年享有盛名的王濟遠,因此龐薰琹的作品被市場認可度高。據統計,他的作品最早出現在內地拍場是在1997年的朵云軒秋拍中,他的一幅1957年作《繁》以6600元成交。而從1998年開始,龐薰琹的作品價位就有所提高,在1998年中國嘉德春拍中,一幅上世紀70年代創作的《靜物》油畫拍得25.30萬元的價位。這一方面反映出收藏界對于龐薰琹的一個再認識,另一方面也表明市場對其精品畫的價值認可。
從2002年開始,龐薰琹畫作的市場價格開始逐步走高,從20萬元到30萬元再到50萬元。值得一提的是,佳士得和蘇富比對這位在中國近現代繪畫領域有重要影響的人物青睞有加,如2003年秋拍,龐薰琹的《杜鵑花》在香港佳士得以53.78萬港元成交。2005年北京翰海的秋季拍賣會上,一幅龐薰琹創作于上世紀60年代末的靜物作品《雞冠花》拍出了66萬元的高價,這幅作品的整體畫面體現了他固有的藝術主張,強調色彩的運用、參差錯落的構圖與執著的生活追求,均一一在這幅靜物中充分體現出來。而2007年在香港蘇富比,龐薰琹的《鳶尾花》更是拍出了180萬元的佳績,這也使得龐薰琹作品正式進入100萬元的行列。2011年中國嘉德春拍中,龐薰琹1983年作《路是人走出來的》以322萬元成交;2012年春拍,榮寶齋(上海)推出龐薰琹作于1974年的《瓶》,其以345萬元的成交價創下了目前龐薰琹作品的成交最高記錄。
1985年,龐薰琹逝世。家屬將龐氏遺作479幅捐贈給桑梓常熟。在目前市場上,龐薰琹的作品流通的并不多,相信隨著其精品在市場上的不斷出現,其價位還將有一定幅度的上升。
王濟遠:價值重現 市場可期
對不少人來說,王濟遠是個陌生的名字,即便對美術有一定了解的人,王濟遠也是個相對生疏的名字。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個名字常常是和劉海粟的名字寫在一起出現在報刊上的。但隨著王濟遠旅歐游美,在上世紀40年代以后的美國華人藝術家中,王濟遠卻是被人稱道不已的。這個被內地市場遺忘的畫家,進入新世紀之后,王濟遠才再一次在中國內地收藏界被人們提起。
在內地拍賣場上,王濟遠的作品第一次出現是在2002年秋拍的中國嘉德書畫專場中,當時一幅王濟遠創作于1932年的名為《蘊澡浜之殘痕》的絹上水彩畫,但遺憾的是,這幅作品最終因無人應價而流拍。而這也反映出當年收藏界對于王濟遠及其作品的陌生。
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時隔一年之后,同樣是在中國嘉德的秋拍中,王濟遠的13幅1930年游歐時期所作的《人體速寫白描集》卻拍出了38.5萬元的價錢,并且這一價格在此后的10年間都再沒有被超越。如果說這次高價成交是王濟遠作品在內地拍賣場中的一次意外的話,那么也正是這次拍賣使不少人真正開始重新審視王濟遠和他的油畫。
從2008年開始,王濟遠的作品價格急劇上漲。而這一波行情更多地體現在了香港佳士得和蘇富比的拍賣中。在2008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中,一幅《女人像》拍得54.75萬港元,而他的另外一幅作品《桌上的景物》則拍出了108.75萬港元的高價。而到了當年的秋拍,一幅王濟遠《自畫像》在佳士得以338萬港元成交,再次刷新了他的市場記錄。而這也是迄今為止,王濟遠畫作在拍場中的最高價。
相較于香港市場中不斷走高的王濟遠作品,在內地各大拍賣場上,王濟遠的作品市場行情雖然也有所表現,但大多數作品的成交價仍然徘徊在100萬元以內。2015中國嘉德春拍“王濟遠藝術專場”中,他的《讀書少女》木板油畫以全場最高價,也是迄今為止內地市場的最高價80.5萬元成交。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隨著人們對王濟遠藝術認識的提高,他的作品將會受到越來越多藏家的關注,市場價格也將進一步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