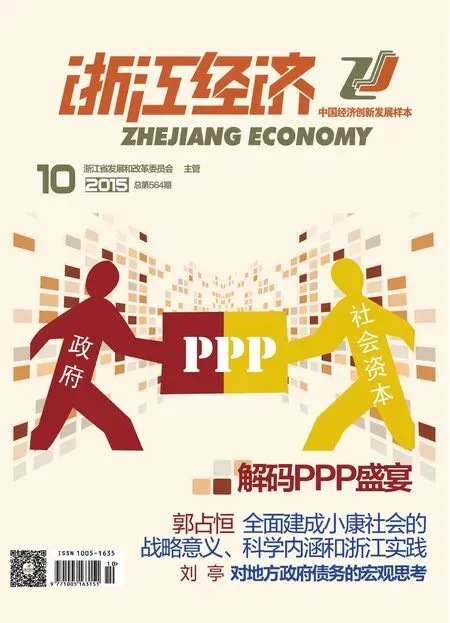對地方政府債務的宏觀思考
劉亭
對地方政府債務的宏觀思考
劉亭
*本文系劉亭同志2015年4月25日在“第22屆全球金融年會”財富管理分論壇上的報告,編發時有刪節。
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是全國性的普遍問題。一定意義上,它是一個體制性、模式性的問題。未來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要解決,單靠地方政府的努力也是無解的,必須依靠全國深化改革和轉型發展的新突破

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怎么看都是你地方政府的事情。但中國是單一制政體的國家,問題出在地方,根子恐怕還是在“頂層設計”。所以,講這個宏觀思考的話題,也不能算是“貨不對路”。
從現狀來看,中國的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不是一兩個、十幾個少數地方的問題,而是全國性的普遍問題。從成因來看,中國的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不是哪一位地方領導管理不當才引發的問題。一定意義上,它是一個體制性、模式性的問題。從對策來看,未來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要解決,單靠地方政府的努力也是無解的。解鈴還須系鈴人,必須依靠全國深化改革和轉型發展的新突破。
債務知多少?
根據2013年12月30日審計署發布的《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截止到2013年6月底,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總規模為人民幣17.9萬億元。其中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為10.9萬億元,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為2.7萬億元,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為4.3萬億元。從總量上來看,尤其和中央債務合在一起后,總負債率低于國際標準,還屬于安全區間。因此,審計署的總體評價也是“債務風險總體可控。”但是,對于地方債務,有幾個呈現的特征卻是讓人非常不安:
一是增長速度非常快。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從2010年到2013年,同口徑年均增長接近20%,其中縣級年均增長在26%以上。
二是有些地區很嚴重。2012年底就有近200個縣、3400多個鄉鎮債務率超過100%,償還壓力很大。
三是債務投資低回報。地方政府債務投資的去向主要是市政建設、土地收儲、保障性住房等基礎性、公益性項目,收益水平低、回收期長。甚至不少的項目不僅不產生回報,后續的運行維護還需持續投入。
四是高度依賴土地出讓。當前中國地方債務的主要償付來源是政府性基金收入,而政府性基金收入中75%的資金源自土地出讓金。
當然,以上還是2013年年中的數據,如今已到了2015年。財政部原本規定各地于今年1月5日前上報至2014年底的地方存量債務余額,然而地方上都有個“小九九”。因為在存量確定、債務劃分后,負有擔保責任和救助責任的債務,今后的大趨勢是歸于項目或融資平臺自身的問題(或通過出讓股權以及變現國有資產抵補解決),很難再“搭車”,算是真正的地方政府債務(這也就是說中央不會給予托底解決)。而且未來地方發債規模,要與存量債務規模掛鉤,因此地方上報數據時便傾向于做大債務盤子。
究竟之前是審計署摸底時,地方政府怕追責而存在瞞報漏報,還是如今甄別時為了做大盤子,地方政府又錯報虛報?恐怕弄不好就是一筆“馬馬虎虎”的糊涂賬。譬如,多地城投公司索性上報了兩套債務數據,據悉之間最大相差的落差竟然達到30%!
一些研究機構也給出了獨立的推算。如中金公司日前在發布的最新研究報告中對地方政府債務規模作了測算,參考社會融資總量增速、城投債發行量和地方政府債券發行量,預計2014年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為15萬億元,這是比較保守的說法。法國興業銀行估計,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總規模甚至已達人民幣25萬億-30萬億元。瑞銀亞洲區首席分析師陶冬則一口咬定“地方債(包括地方融資平臺債務)起碼有20萬億元”。
在地方調研過程中,縣級政府負債百億元的不在少數,一些地方甚至在200億元以上。每年的利息償付就已是沉重的包袱,而且規模還在如同雪球般越滾越大。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以至于此呢?
病根在哪里?
如果追溯一下地方政府債務急劇膨脹的時間線,可以發現2007年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總量還不足5萬億元。然而至2013年中,就飆升至18萬億元。而這個時間點,正是我國為抵御全球金融危機、出臺大規模經濟刺激措施之后。
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后,中國經濟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現負增長,2000多萬農民工返鄉,宏觀經濟面臨硬著陸的風險。為了應對這種危局,中國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十項措施。初步匡算,實施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約需在往年正常的投資規模以外,再追加擴張性投資4萬億元,用以對沖危機引發的經濟下行壓力。此后,“四萬億”便成了一些媒體和專家詬病當時宏觀調控“過度反應”的代名詞。
“馬后炮”沒有多大意思,像許小年那樣的“事前諸葛亮”,或許還有點說“風涼話”的資格。記得當年中央推出“四萬億”肇始,甚至有專家質疑,藥量還下得不夠大的。我早就說過,“四萬億”本不算多,但是到了金字塔形權力架構的特色中國,“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地方政府早就積蓄了滿滿的投資沖動,如今中央一聲令下,豈有不“乘勢而上”之理,又哪能不釀成“潰壩噴涌”之勢?
很多市縣的財政收入僅夠用于保工資、保運轉、保起碼的民生,政府投資只能依賴于土地出讓金。危機來襲后,這一塊也大幅銳減了。預算法規定地方政府不得發債,這就逼得官員們掉頭翻身去找銀行貸款、BT融資或發行企業債券,好在當時的金融監管當局眼開眼閉,不但不加追究,反而開閘放水,兩會上信誓旦旦的5萬億元新增貸款規模,到年底一下子幾乎翻了一番。有專家推算,2009年的貸款有40%流向了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城投債、地方債、信托、銀行理財,轉來轉去錢其實還是給了地方政府”。
說到底,政府項目投資是地方政府債務的主要成因。沒有這么強勢的政府,沒有如此眾多的項目,沒有“不借白不借”的機制,地方政府的債務何以至此!而最近地方政府的日子難過,還在于風暴潮“三碰頭”:一是實體經濟不景氣導致稅收下滑;二是房地產的不景氣導致土地出讓金減少(土地出讓金作為政府性基金收入,雖不納入公共財政收入統計,但實質上已占地方財政總收入的三成以上,很多地區已超過稅收收入);三是政府項目和民生支出負擔越來越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今年一季度經濟數據出臺,GDP增速為7%,比去年同期回落0.4個百分點。和2008年二季度14.9%的增速相比,早已跌去了一半多。另外,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3.5%,為新世紀以來的最低增速,更成了GDP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趨勢下,在央行加快降息降準節奏的同時,政府主導的投資拉動這一“法寶”依然又會被祭出。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公布的各地政府安排的投資計劃總規模已達20萬億元。前賬未了,后債又生,地方政府如何才能擴大有效投資、穩定經濟增長,且不給已然高企的地方政府債務雪上加霜呢?
出路向何方?
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著力防控債務風險。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作為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但地方政府的債務“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對此,或許也用得上王岐山書記對反腐說過的一句名言:“堅持標本兼治,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
從近期中央密集出臺的相關政策來看,系統性風險的控制和化解工作已經大舉展開。譬如:
2014年9月,《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國發201443號)印發,旨在建立規范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主要內容包括建立“借、用、還”相統一的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機制;賦予地方政府依法適度舉債融資權限;推廣使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PP);剝離融資平臺公司政府融資職能等。
2014年10月,財政部《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清理甄別辦法》(財預2014351號)印發。對2014年底尚未清償完畢的債務進行清理甄別,要求認真甄別篩選融資平臺公司存量項目,大力推廣PPP模式。
2015年1月1日,施行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新版《預算法》明確立法宗旨,細化全口徑預算管理和預算公開制度,賦予地方政府有限發債權,以及對完善預算審查、監督、強化預算責任等方面,都作出了更加詳細的規定。
2015年1月,財政部《關于開展地方政府存量債務初步清理甄別結果自查工作的通知》印發。要求各地對初步清理甄別結果組織開展自查,并于2015年3月8日前上報存量債務清理甄別結果。
2015年3月,財政部《地方政府一般債券發行管理暫行辦法》印發。文中對地方政府一般債券的定義、資金用途、償債來源、承銷發行、信用評級、信息披露等方面進行了明確和規范。
2015年3月,財政部《2015年地方政府專項債券預算管理辦法》印發。針對地方政府政府專項債券的特殊性,在發行要求、預算編制和調整、預算科目設置以及預算執行等多個方面提出了具體要求。還明確了地方政府專項債券預算制定主體為省級財政部門,專項債券所有收支必須納入政府性基金收支預算管理,明確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全部納入政府性基金預算管理,可在銀行間或交易所市場發行,明確提出債券兌付主體為省級財政部門。
2015年4月,財政部《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管理暫行辦法》印發。文中對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的定義、資金用途、償債來源、承銷發行、信用評級、信息披露等方面進行了明確和規范。
大而化之、籠而統之,以上文件內容,可解析為三招:
一是控新增。明確地方政府今后舉債不得通過企業融資,只能通過發行地方債券。對債務規模實行限額管理,并分門別類納入全口徑預算管理。部分市縣因存量政府債務較大,按照財政部下達的各項風險指標測算已被列入風險預警地區,今后將不得新增債務限額。
二是化庫存。那些沒有收益、難以吸引社會資本參與的公益性項目,可由政府發債融資。如財政部近期下達了地方存量債務1萬億元置換債券額度,用以部分置換截至2013年6月30日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存量債務中將于今年到期的1.86萬億元債務。這些債券將按市場化原則在銀行間和交易所債券市場發行,并鼓勵符合條件的機構投資者和個人購買。據財政部測算,置換后地方政府一年可減輕利息負擔400億—500億元;如果首批置換成功,財政部還有可能進一步擴大置換規模。
三是通新渠。對軌道交通、供水供氣、垃圾處理、教育衛生等可以吸引社會資本參與的公益性項目,積極推廣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合作模式,其債務由項目公司按照市場化原則舉借和償還。
大家最近都非常關注股市,說中國股市熊了七八年,如今終于牛了一把。但是,中國股市最近為什么這么牛?為什么中央高層也樂見其牛?其實背后的邏輯,是和我們用PPP解決地方政府債務的道理相通的。
中國的企業一方面負債非常高,另一方面,大量有成長性的中小企業又很難獲得銀行貸款。如何解決這一難題,解藥就是大力拓展直接融資,借助市場的手,讓資金流到最需要、也最能產生回報的企業去。所以,就有了官方對“資金流入股市也是支持實體經濟”的強調;有了鼓勵做大中國股市,以一輪牛市來集聚社會資金,并在年內加快推行企業上市注冊制,讓大量的創業創新中小企業能快捷上市的種種行動。
而我們在政府性項目中推廣PPP,背后的思維邏輯也是期望“以更多直接融資,替代高杠桿風險的間接融資”;以規范的股份合作,替代銀行貸款或地方債券。PPP模式還有一個更可貴的優點在于,社會資本的引入,將使得政府性項目更注重投資效益和回報。2005年我在全國投資工作會議上力推民間投資,2011年我在全省投資工作會議上首提“有效投資”,其中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投資的有效不是由政府來評價,而是市場說了算。只有引入市場嗅覺最為靈敏的社會資本,一起合作開發項目,才能幫助我們真正甄別該項目到底是否“有效”。
講到治本的辦法,一是政府要謙卑,政府要轉型。政府要盡快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政府要敬畏市場,要懂得只有在充分尊重和發揮好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才能做得到“更好的發揮作用”。二是投資要謙卑,模式要轉型。過度依賴型的投資拉動,是一劑毒品,是飲鴆止渴、剜肉補瘡;是得不償失、老道失算。要加快實行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發展模式的替代,要把更多的精力和資源,用在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供有效制度供給上。
最后,說句玩笑話。投資和創新驅動雖然是要“兩點論”,但這只是機械唯物論;在兩點論的基礎上突出創新驅動的“重點論”,才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從上世紀50年代起,陳云同志就告誡我們,“建設規模不能超過國力”。建國60多年了,我們的經濟歷經了多少個大起大落,今天的建設規模再加上一個更為緊要的“民生規模”,那就更不能大幅度成倍地超過國力了。中國政府加上企業的總負債率已然是當年GDP的200%。按吳敬璉老先生的最新說法,甚至已經是250%-300%,幾乎列位世界之最了。金融危機說到底,就是債務償付危機。難道我們還不能長點記性、長點見識?難道我們還要重蹈投資驅動發展、債務驅動投資的那條老路、那條死路嗎?
作者為浙江省咨詢委學術委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