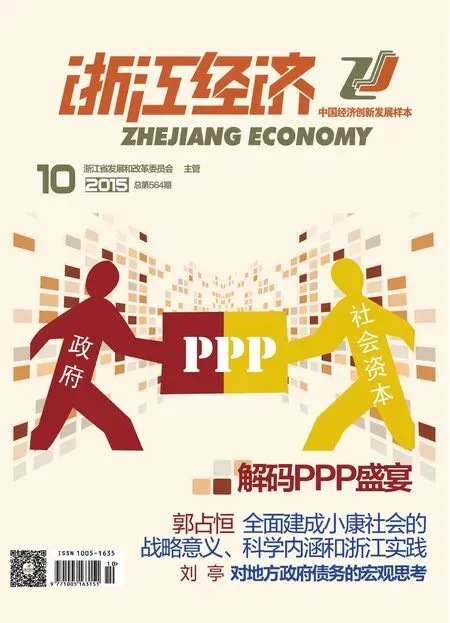推進創富大省的戰略轉變
卓勇良
推進創富大省的戰略轉變
我們早已缺乏充足的自然資源,甚至建設空間也不充裕。我們的內功增強應放在社會發展上
卓勇良

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浙江早期發展因洪水恣肆,曾大大滯后于中國北方地區。然而,一旦大規模治水展開,即后來居上,成為中國最富裕地區。根據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先生,在其成名的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中的史料,浙江在公元740年,即盛唐時期,人口逾萬縣已達56個,遙遙領先于江南諸省。
文革前經常去慈溪外婆家。這是距縣城滸山20多公里的小村,所見皆為磚瓦樓房。童年時,我在寧波城外8公里左右的一個小村莊呆過,租住在一個蠻氣派的墻門內,有一個天井和公用的廳堂,房東大伯1961年就是在天井前的廳堂磨糠充饑。墻門外有一條青石板鋪就的幽幽小巷,小巷口是一排面河樓房,幾位阿婆在落日余輝下納鞋底。
這一幅農業時代的豐裕畫面,到了改革開放前夕就有些凋敝了。慈溪縣1979年農民集體分配收入僅人均111元,浙江最低的青田縣僅37.0元。外婆家小村子,改革開放前似乎未曾蓋過新房子。
浙江改革開放以來快速崛起,既是歷史勝景回歸,更是改革開放巨大成就。浙江人均GDP于1992年超越老對手江蘇,1997年超越廣東,自此穩居全國第4位長達17年,終于在2009年被江蘇反超。浙江人均GDP按當前匯率,根據我的預測,將于2018年達到當年全球高收入國家和地區水平。
國際經驗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達到美國1/2后,經濟增速將顯著放慢。2012年,世界銀行統計的全球184個國家和地區,其中155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均生產總值,在美國一半以下。浙江往后發展,顯然將有更多不確定性。而且,創富更應理解為是一種可持續的全面發展,并不僅僅局限于經濟增長和城鄉居民收入,亦應是省委提出的物質富裕和精神富有的概念。
當前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正確看待浙江這十年。2004年以來,浙江經濟增速持續多年居于全國較低位次,一個重要原因,是未能置身于全國粗放外延增長盛宴之中。在此期間,中西部國有建設用地供給快速增長,轉移支付和地方債巨額攀高,投資超常規推進;而浙江建設用地供給增長相對較慢,地方債規模相對較小,由此并導致浙商大舉向省外投資,省內投資增速幾成全國末位。此種情形究竟禍兮福兮?我和同事最近研究表明,這十年來,這一狀況并非不利于浙江,浙江發展指數仍有所提高。
所以,目前的局面是浙江有理由沉住氣。我們早已缺乏充足的自然資源,甚至建設空間也不充裕,在全國一派粗放外延增長格局下,浙江必定成為增長“洼地”。然而,全國粗放外延增長正在走到盡頭,隨著中央卡住地方債,卡住各地濫施優惠,卡住會計賬目的靈活,再加之中西部資源環境瓶頸日益加劇,區域發展有利局面將逐漸向著有利于浙江的方向轉變。
我們的內功增強應放在社會發展上。經濟增長是牽引力,社會發展是支撐力。當前的一個目標,是在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努力推動社會發展持續居全國前列,一些地方或可明確提出把工作重心率先轉向社會建設發展。諸如增強全社會的人文氛圍,普遍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快社會事業、社會服務業發展等。
這決不等于忽視經濟發展。或許也可以將其稱為經濟發展的一種迂回戰略,也就是按照“工在詩外”思路來做好今后各項經濟工作。兩年前,我因參與小城鎮培育試點評估工作,去諸暨店口鎮調研。鎮委書記張壯雄著重談的是鎮里的社會發展工作。他說,經濟方面自有企業著力,需要政府出面的主要是征地拆遷等,而社會發展大量工作,則必須由政府來做,無人能替代政府,諸如社會保障,教育衛生,村莊和小區建設,農民工的一系列工作等,是經濟發展的保障和支撐。
當前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開始持續快于GDP增長,經濟增長正在進入消費主導格局,政府在這一時刻有一項促進居民收入增長的重要工作。面對勞資雙方,政府本質上應是中性的,即按照市場經濟客觀規律,依法維護雙方權益。但因當前特殊國情,應更多呵護勞動,推進工資三方協調機制建設,促進勞動工資合理增長。同時也要引導資本節制,增強資本社會責任,促進資本治理結構的代際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