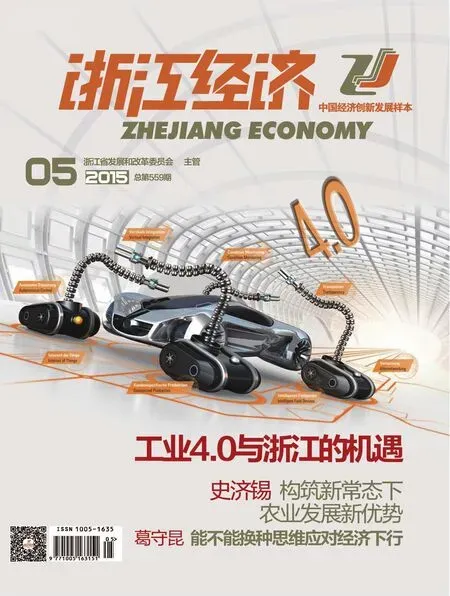提供有效制度供給
提供有效制度供給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一句話,“中國今年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面臨的困難超過去年”,已將經濟分析中喊了一年的“止跌回穩”、“見底回升”之類,徹底放了“泡了湯”——經濟還要下行、困難正在加大。
這時候,政府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當年紅、現得利”,打腫臉充胖子、瘦驢拉硬屎,死撐著那個臺面不愿意下來;還有一種選擇是“放開眼界看未來、堅定不移向前進”,既別自亂陣腳、也別高枕無憂。充分預估困難,著力制度供給的創新,打造有利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環境,成就“創新驅動發展”的新局面。
我們需要做出第二種選擇,而這個選擇的關鍵,又在于政府要為穩增長提供有效制度供給。
制度供給是就政府,尤其是現代政府而言的。說得土一點,就是一個政府,到底是干啥吃的?簡言之,政府是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但對公共產品,我們過去多理解為水電路信等基礎設施,而且認為那就是應該由政府來全盤提供的。其實,現在的情況也并非“鐵板一塊”、都是由政府來“埋單”的。當下“紅得發紫”的PPP模式,就是公私合營來建設甚至是運營公共設施的一種模式。但即便如此,PPP模式的相關制度安排,還是要由政府(如果牽扯到立法,那就包括了權力機關也即“廣義的政府”)來提供的。這也就是政府提供的最重要公共服務——制度供給。那么,新常態下的制度供給要注意哪些問題呢?
首先,要從“決定性作用”的意義上理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通常人們總是將政府和市場理解為“刀切豆腐——兩面光”,而爭論的焦點,又落在了誰多一點、誰少一點,誰強一點、誰弱一點之上。這是認識上的誤區。正確的視角,還是應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即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說的,經濟是“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這其中,經濟基礎是具有決定性的,包括政府在內的上層建筑是被決定的。當然,政府也不是只能隨波逐浪、無所作為,它還能對經濟基礎起到反作用。但反作用有好有壞,或是順勢而為,助推發展;或是逆潮而動,阻滯前進。所有這些,正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全深改《決定》中的那句經典表述“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其次,“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主要體現在有效制度供給上。經濟基礎已然市場化了,那政府就要為市場經濟規律的“決定性作用”發揮,及時提供一整套“與之相適應的”制度供給。譬如改革之初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那就是政府為市場在“三農”領域中提供的有效制度供給。這樣說,也不是過去沒有制度供給,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就是計劃經濟大的制度供給背景下,在“三農”領域中小的制度供給。當新的制度供給還沒有提供之前,舊的制度供給就是“王道”,“人隨王法草隨風”,搞“大包干”就是不合法的,起碼是違規違紀的。所以,小崗村的18戶村民要在“生死文書”上按下手印,準備承擔“坐牢殺頭”的危險。那么,現在有沒有像當年那樣失效的、甚至是負效的制度供給呢?很顯然,還有不少,諸如政府權力運行、資源要素配置、市場秩序維護、社會保障健全等很多方面,都還有待于政府盡快提供與時俱進的有效制度供給。
最后,制度供給的有效,最終要體現在出活力、穩增長上。制度供給是否有效,用得上當初的那句神邏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法規制度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涉及領域無所不包、在劫難逃,這固然是現代法治社會的理想境界。但是不要忘了,“民以食為天”。如果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制度供給不給力,發展的動力嚴重不足,最后搞到經濟和老百姓的收入都上不去,那就是舍本逐末、緣木求魚。考慮到今年甚至更長一個時期經濟下行的壓力,政府部門應集中精力、突出重點,將那些出活力、穩增長的制度供給,擺上最緊迫的工作日程——形勢變化留給我們爭取主動的時間,其實已經不多了。
政府部門應集中精力、突出重點,將那些出活力、穩增長的制度供給,擺上最緊迫的工作日程


浙江省政府咨詢委學術委副主任、研究員